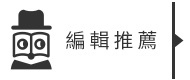導讀
愛,值得更好的回報
郭強生
能讀到一本讓人神迷忘我、欲罷不能的小說,真如同久旱逢甘霖。
整個暑假,我不停地企圖彌補經過整個學期教學後的消耗,希望能讀到幾本可以幫我充電的文學作品。先是從近期出版的小說著手,看了近兩年獲得中外文學獎的幾部小說。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比我年輕許多,我讀得到他們旺盛的企圖心,努力鋪排情節,或是挖掘歷史素材,或是揭開自身成長經驗,都顯得如此急切,甚至隱隱充滿了一種自我防衛的焦慮。
能責怪他們嗎?整個時代都被網路臉書籠罩,他們太清楚什麼是讀者反應。快速的資訊流通,各式的文學評論術語與招式,教會他們如何打造預設的護身符。一本一本我拿起又放下。
是我老了嗎?曾經深深震撼我的文學作品,都有一個大開大闔的靈魂,足以包容與理解人生所有的曖昧與不確定,難以用主題加以定論,更無法簡述屬於她/他們的那種渾然天成的文字所帶來的驚喜──除非你真的好好坐下來靜讀。
最後,我發現自己又在重讀辛波絲卡、柯慈的《屈辱》,甚至是葛林的《沉靜的美國人》。
直到出版社寄來這本努涅斯的《摯友》譯稿。
二〇一八年她獲得極負盛名的美國國家圖書獎時,我曾匆匆讀到這則新聞,當時沒特別在意,因為當年她的獲獎被視為「爆冷」。如今我終於讀到了這本精煉、優美、簡潔又深邃的小說,驚豔之餘也要為評審委員們喝采,讓這本篇幅不長的小說,從那些看似鉅作的大堆頭長篇中脫穎而出。這真是一本耐讀,更經得起慢讀、細讀的小說。
努涅斯的文筆自成一格,無過多修辭贅句,每每擊中要害,是一本真正「智慧的」小說。原因無它,獲獎時已六十八歲的作者,寫作已長達二十三年,出版過八本書,也曾獲得過一些文學獎的肯定,但是卻屬於那種「人不知而不慍」的創作者。
她一直安靜地在寫,與文學圈始終保持著距離,一直到了這本《摯友》,被媒體形容為「一夕爆紅」成為暢銷書。大家都喜歡這樣的「勵志」故事。
然而,真正勵志的部分不在於她的獲獎,而是在於她仍用一種純樸、近乎古典的態度面對寫作,寫下了她對那些正在消逝中、甚至是被年輕一代視為無用陳舊價值的哀悼。
你沒辦法解釋死亡。
而愛,值得更好的回報。──《摯友》,64頁
尤其,在MeToo運動席捲全球,女性同聲撻伐性騷的年代,努涅斯卻描寫了一位花名在外的教授與崇拜他的女學生之間,一段長達三十年的友情(或是,另類的愛情?)。
怎麼可以為這樣一個經常與女學生發生性關係的男人之死哀慟欲絕?年輕的讀者可能立刻就會未審先判。努涅斯竟然還寫得如此理直氣壯?
我想到法國國寶級女演員凱瑟琳.丹妮芙,曾因一句「我們那時男女之間的互動跟今日不同」遭到網友洗板出征。她口中的「那時」是歐洲藝術片的全盛時期,「那時」的男人指的是楚浮、布紐爾、費里尼……可惜昔日銀幕女神沒有機會將話說完,也許她需要像努涅斯的文筆才能表達得更清楚。在今昔之間,在對錯之間,每個人都在經歷著不同的痛苦,也在見證著自己的蛻變。
這是一個多麼具挑戰性的任務,努涅斯卻辦到了,難怪令評論家與讀者們讚嘆不已。她筆下那個頗具自傳色彩的敘述者,在哀慟中對著亡者「你」細訴,寫下了「你」自盡後,她陷入悲傷無以自拔過程中的點點滴滴。不是為亡者辯護,更像是一個認真活過、年屆七旬的長者在告訴下一代:
生命本就是充滿危險的,不管有多少的預防與警覺,我們仍然一不小心就會受傷。
如果我對阿波羅好,無私地為牠犧牲、愛牠──那麼有天早上我醒來牠會不見,而你會從死之國界回來取代牠?──《摯友》,182頁
全書結構看似札記手抄,零零星星卻是綿密布局不鑿斧痕。除了敘述者與亡者外,努涅斯安排了一隻名為阿波羅的大丹犬登場,成為全書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
亡者的第三任妻子約了敘述者「我」見面,遺孀不願再繼續飼養那隻亡者從街上撿回,近九十公斤的流浪狗。「我」的生活簡約單調,十五坪大的住處根本容不下阿波羅旋身的空間,更不用說,一旦被房東發現,「我」將失去這間房租低廉的住所,人狗都將流落街頭。
但是「我」卻收養了阿波羅,同病相憐的兩者命運未卜,讓這本充滿冥思與回憶片段的小說,更增添了閱讀上的期待。
阿波羅既是亡者的替身,安慰了「我」這個孤獨的靈魂,牠同時也像是敘述者「我」的分身:敏感、孤獨、憂傷。這個當年被教授啟發,大半生都奉獻寫作而習慣離群索居的單身女子,從阿波羅這個陌生的龐然生物身上又重新看到了文學的意義──你如何能跨過生存的隔閡,發現一種新的表達,讓靈魂與靈魂之間取得和解與重生的可能?
有首歌是這樣寫的:假如我們能和動物說話就好了。
意思是,假如牠們能和我們說話就好了。
但是,當然了,那會毀了一切。──《摯友》,251-2頁
所以,《摯友》不光是一部哀悼之書,更是一本關於寫作的書。
全書充滿著懇切又勇氣十足的文人風格,但是努涅斯既不尖酸也不自溺,她的一針見血總帶著某種獨特的幽默感,以及在她這個年紀所修得的智慧,對生命仍無法放手的深情。
當「我」大聲對著阿波羅朗讀起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大狗安靜享受著與新主人建立共鳴的那個場景,就連我這個從未養過寵物的讀者也深深動容。
並非阿波羅真能理解文學,「我」清楚知道這種一廂情願「擬人化」的危險。但她卻因此意識到,想必曾有摯愛之人對狗狗做過類似的事。連狗狗都知道什麼是難以放手的懷念,而總自以為理性的人類卻以各種治療之名,讓憂傷成了毒蛇猛獸。
除了寫下這日復一日的緩慢覺醒,「我」無法找到人生的出口。
校園流傳的笑話。A教授:你讀過那本書了嗎?B教授:讀?我連教都還沒開始教。──《摯友》,208頁
對文學小說的重度使用者來說,相信除了這本書中刻劃的孤獨與深情會令各位低迴之外,其中許多文學中的「互文」──從里爾克、弗蘭納利.歐康納、到柯慈──必會讓你們覺得是全書的大彩蛋。(多麼湊巧,我也剛重讀完柯慈!)
在學院中教授創作近二十年,對努涅斯描繪的許多教學現場,我更是心有戚戚焉。原來在手機臉書無所不在的年代,年輕一輩對經典的不以為然已是四海皆同。書中有一節提到,學生們不懂為何要讀那些可能已經絕版的經典文學,甚至認為「不是該讀些更成功的作家?」(《摯友》,206頁)。
讀到此處讓我不禁心驚:做為文學教育的傳承者,我如何能不因任務之艱難,而取巧以一些迎合議題與潮流的作品當成安全選項,最後陷入如B教授那樣只能自嘲的困境?
從努涅斯身上,我看到了在面向大眾對純文學的質疑時,最好的一種回應。至於一本文學佳作如何能讓人在瞬間耳聰目明?我想,她的《摯友》亦提供了充分的解釋。
我們都認為自己的付出值得更好的回報,但,什麼才是更好的?讀完這本小說,我心中默默亮起了答案。
(本文作者為作家、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