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舊作往事
如果沒有梁由之兄的堅持,這一套小書是不會編印出來的。這三種書都是寫成於二十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每一種都印過多次,年代久了,再印感覺意思不大。講老莊的一種,因為有許多新的想法,倒是值得重寫一遍,但這幾年家中多事、日子辛苦,又顧不上。但由之對我寫的東西有一種過度的錯愛,做事的態度也比我堅決,於是只能從命了。「駱氏三書」的名目也是由之所擬。聽起來有點托大,邏輯上卻沒有問題:鄙姓駱,書是三種。
就習性來說,我只喜歡讀書,不喜歡寫書。所以寫成的書,大抵皆有人情的緣故。
《縱放悲歌》原來是香港中華書局所出「詩詞坊」叢書的一種,主編是金性堯先生。我跟金先生不相識,是趙昌平兄把我引薦給他。有一次特意拜訪了金先生,想請教關於書稿寫作的要求,但金先生好像很放心的樣子,沒有說幾句,然後隨意聊一會兒天。我見壁上懸有梁啓超所書對聯,問起金先生對書畫的愛好,知道他原本收藏頗多,「文革」中被抄沒,有許多已經無法迫回。聽說過金先生因為知道一些藍蘋在上海的情形且偶有談論,因此遭到迫害,情形慘厲,但金先生並不願說這些事情。他身形小而消瘦,說話謹慎,想象不出舊日灑脫飛揚之態。
書稿已交之後,跟金先生不再有具體事務的往來。我不知為什麼緣故寫信給他,連帶說及自己心情沮喪,不願做事,金先生特意回信,說中國的國情複雜,很多變化不可預料,還是要努力振作。其實我本是無意的牢騷,金先生卻認真了。我想起他遭折磨而形成的謹慎性格,因此很感激他。
二〇〇七年,金性堯先生在上海去世,時年九十一歲,也算是高壽。
《聞道長安似弈棋》曾以《中國歷史上的大陰謀》為名出版過,是上海文藝出版社所出「五角叢書」的一種,後來由台灣遠流印行。「五角叢書」曾經風靡一時,動輒印數十萬以上。叢書主編是何承偉,但後期具體事務主要是副主編戴俊在操持。當時章培恆先生算是叢書的顧問,我亦列名編委,於是戴俊便借機索稿,於是有了章先生主編的《中國禁書大觀》和我寫的這本書。這本書在我來說有一點特別的地方,是因為我對戴俊誇口說一個月可以寫完,於是趕得特別緊。全書是一遍成稿的,僅在稿紙上略作刪改,沒有謄寫過。讀起來文句很流暢,算是由此帶來的好處吧。現在寫東西很慢,常常會想起當年也曾精力旺盛,信筆縱橫,自以為豪爽的樣子。
說到精力旺盛、性情豪爽,其實是戴俊的特點。他當過兵,個子不高,身材敦實,對人厚道而好惡分明。有時說到自己得意的計劃,便神情歡愉,眉飛色舞;說到人間不平事,則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戴俊比我小不了幾歲,但感覺上好像他比我晚一輩似的。
那一段時期,復旦這邊和章培恆先生親近的一些學生,如我、賀聖遂、談蓓芳,與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金子信、戴俊、陳徵幾位來往頗多,也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在靜安賓館十數人全都喝醉了,沒有人管得了,只好各自想辦法回家。後來金子信說起他騎自行車摔倒在半途,腦袋上砸了一個破洞。
金子信和章先生先後去世。最為震驚的,還是在二〇一一年聽到戴俊去世的消息。因為感覺中他年輕而健壯,富於生命力。
香港中華書局在編印了《小說軒》、《詩詞坊》之後,又請人編《智慧殿》;主編是不是葛兆光我弄不清楚了,反正我那本《老莊隨談》是他約的。這本書現在看來有許多不滿意之處,但有些讀者很喜歡它。
我跟葛兆光有長年的交情。十多年前,兆光在清華任職,住藍旗營(他樓上是秦暉)。那時我與孫偉紅結婚未久,我們在北大二十樓有一間小房子。那是所謂「筒子樓」,廚房、廁所在外面,房間也非常簡陋。藍旗營離北大很近,有一次我們去兆光家做客。其實他的房子裝修得很簡單,但是寬大亮暢,跟筒子樓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孫偉紅看著眼神發亮,羨慕得冒傻氣。葛兆光笑起來,說「我這也是熬出來的」。當時孫偉紅在北大法語系任教,資歷還淺。
兆光、戴燕夫婦請我們吃飯。後來孫偉紅說咱們也要回請一次,並說她要自己做法國菜請客。這頓飯欠在那裡很久,然後孫偉紅生了幾年病,離世遠去。
三本小書寫作的念頭,都寫過說明,好不好則要由讀者來評判,合起來要寫個序,不知道說什麼好。看著書,想起來的是一些故人往事,隨手寫下來。或者,這也是跟讀者的一種情感交流吧。
寫這幾本書的時候,也就是所謂「上世紀」八、九○年代,我們曾經有過夢想,有過歡愉,也有過悲哀。漸漸看著歲月流去,親友凋零,難免有無常之嘆。但上課時我也說過,像王維的詩,像《紅樓夢》,在說人生無常的時候,也說無常是美。因此我們對此人世,仍有長長的眷懷。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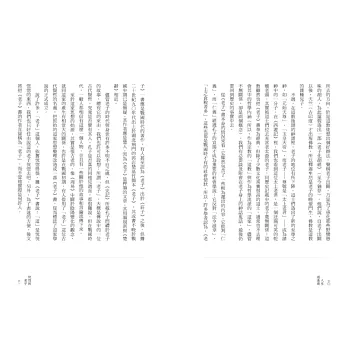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