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歷史事實、社會實在與研究方法
一、前言
本書的出版源於客家研究如何作為一門學問的關心。基於特殊研究旨趣,客家研究需要有一個發展良好的客家研究社群,包括客家研究學會、學術期刊、讀本、教科書,以及學術理論和典範。臺灣的客家研究社群雖然在形式上已有學會、期刊,不過理論和研究方法都尚待發展。在此過程中,現階段的客家研究廣泛地引用各類學科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來了解客家(族群),而具有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學術特色。
客家研究作為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學術領域,需要系統地研讀有助於客家研究的相關理論,例如族群邊界理論、多元文化理論、社會記憶理論等,也需要系統地瞭解有助於客家研究的方法。前者,透過彙編客家(族群)研究讀本的方式,提供新進學習者思考客家(族群)議題的敏感度;後者,匯集熟悉各相關方法的學者,以具體議題的研究分析為例,特別是實作的技藝方面提供學習案例。
客家(族群)研究作為一門經驗性、詮釋性與規範性的學科,必須留意不同觀點(理論)帶來的不同發現,因為不同的方法會看見不同的客家(族群)樣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研究工具,會因研究者的需要而決定。研究者能善選/用工具箱裡的工具,方能善其事,但前提是要有足夠的工具並能瞭解工具的用法。否則可能使用了不合適的研究方法,或因為研究方法的限制,造成研究發現的不足。
本書特別透過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實作案例,介紹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但在進入介紹客家或族群研究的技藝之前,必須確立研究對象的性質,才能進入研究工具選擇的討論。研究方法之設計或選擇與實作技藝,往往相應於預設的研究對象特質。自然科學典範的社會研究,以掌握規則、趨近真理為目標;詮釋理解的社會研究典範,著重的則是社會行動者意義之網的解讀,故各有其相應的方法論與實作技藝。「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概念在知識論的預設上傾向於客觀論,「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概念則屬於建構論的立場。面對所研究的經驗現象時,理解、區辨歷史事實與社會實在的知識論議題,往往左右著後續方法論的思考與實作技藝。
二、歷史事實與社會實在
「事實」(fact)或「真理」(truth)的追尋,是近代科學研究的任務。傳統歷史研究強調陳述發生過的事實,但是這個立場則受到「歷史相對主義」(historical relativism)的質疑,因為研究歷史的人不可能完全外於他自己和時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因此歷史就不是單純地陳述客觀的事實。人類學的觀點也同樣挑戰了上述「(客觀)歷史事實」的概念。對人類學者而言,「在地人/被研究者觀點」是人類學明顯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解釋的出發點之一。換言之,在對任何現象進行解釋時,都應考量到行動者自身主觀上對該現象的詮釋方式,即使此詮釋視角,有可能和所謂「客觀事實」並不全然一致。
例如在談「集體記憶」概念時,王明珂就借用了非洲Jie 族的研究,以便說明由「結構性失憶」所創造出來的虛構式譜系。Jie 族的家族記憶通常只有三代,家族成員通常只有十數或二、三十人。即使如此,在一個家庭兩代男性成員中,依舊可以採得兩種不同版本的親屬關係結構。那麼,到底誰所敘說的版本才是「事實」呢?王明珂指出:「所謂系譜與其說是『實際上的血緣關係』,不如說是『人們相信的彼此血緣關係』。雖然人們相信的族譜有相當程度是事實,但也有許多虛構的成份」(1997:54)。換句話說,族譜就是一種行動者對親族體系的集體記憶,而且在性質上必然是選擇性的記憶/失憶。但這種「結構性失憶」卻提供了理解這群人的重要線索,並非完全沒有意義。
回到客家研究的討論。人類學者Nicole Constable 在討論客家認同之建構時指出,就客家歷史而言,「客家認同較地方化的建構和表述」與「客觀的客家歷史和經驗」要加以區別。前者是「客家人相信他們所共享的集體歷史」,性質上是主觀的觀點,並不必然會和真確或「事實基礎」扯上關係。後者則可以理解為客家族群性之所以能夠生成的「特定歷史力量」,它雖然和前者一樣,也是一種心智建構,但最好是將之理解為一種「第二層次」的歷史建構,重點在於解釋為什麼會形成前者這種歷史觀點(Constable 1994: 4, 7-8)。
對很多客家人而言,近代客家研究奠基者羅香林所倡議「客家人源自(中國北方)中原」的說法,幾乎成為一個不證自明的信仰。但中川學卻以鼻咽癌發生率為證據,提出了將客家視為漢族和南方土著民族混血種的另類觀點。而後,他提出「真實 vs. 事實」的概念來理解羅香林「客家是從中原向南遷移之北方漢人」的說法。簡單講,上述說法是客家人所信奉的「神話傳說」,它雖然不一定反映「事實」,但對他們來講卻是千真萬確的「真實」,因為它已經建構了現實。因此,中川學認為,「我們一方面要承認以中原起源說為基礎的『真實』,另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探討『事實』」(轉引自河合洋尚、飯島典子 2013:133)。
無論是上述歷史學範疇的「歷史相對主義」或人類學範疇的「在地人/被研究者觀點」或「結構性失憶」,還是客家研究範疇的「主觀歷史 vs. 特定歷史力量」或「真實 vs. 事實」,當在進行客家(或其他任何族群)研究時,研究者必須一方面要能區辨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現實建構,另一方面也要對自己的探究重點有所抉擇,清明地知道自己感興趣的,到底是社會所建構的實在,還是所謂的「歷史事實」。
面對「社會實在 vs. 歷史事實」,研究者約略有三種立場的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堅信「實證主義」或「客觀主義」的立場,只關切「歷史事實」的問題。第二個選擇則和上述選擇全然相反,關切的是行動者層次的「社會實在」,並認為「歷史事實」是永遠不可能獲致的鏡花水月。第三個選擇是同時承認「社會真實」和「歷史事實」的存在,並試圖展現這兩者相互交纏影響的複雜圖像。就分析策略而言,社會現象的「經驗」和「神話」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實在」,而發生的「事件」則可類比為「歷史事實」。雖然歷史事實和社會實在是兩種不同的立場,但就現象的性質而言,兩者共存且相互影響的情況,則是不爭的事實。
三、篇章介紹
(一)社會實在 vs. 歷史事實
本書導論所收錄的三篇文章,就是上述同時承認「社會實在」和「歷史事實」存在立場的研究範例。林正慧這篇〈當史學遇到客家:解構後的重新認識〉的問題意識,正始於上述「社會實在 vs. 歷史事實」的兩難。「客家」這一概念的形成,是先從「社會實在」(特別是對「客家= 從中原南遷之漢人」這一論述的信仰)開始的,但一旦研究者抱持著「追求歷史事實」的態度開始爬梳史料,卻又發現「在歷史文獻中找不到客家」。林正慧從「歷史事實」的視角出發,全面性地檢視了當前臺灣客家歷史研究所涉及的重大議題,包括「客家是中原南遷漢人嗎?」
「為什麼歷史文獻中沒有客家?」「清代文獻書寫中的『客』、『粵』是客家嗎?」「清末華南的客家論述臺灣可以通用嗎?」「19 世紀西人的Hakka 論述是臺灣客家嗎?」以及「日治時期種族分類中的『廣東』是客家嗎?」等重要發問,一方面釐清不少既存的迷思,另一方面也清楚整理出學術界目前對上述議題的一些認識和共識。雖然她強調多數「族源論述」(包括創造者本身具備學術背景的文本)是某種意義下的「社會實在」,而非「歷史事實」,但研究者還是必須要「儘量避免以今日的客家概念投射到清代或日治時期的研究當中」,同時也必須善用社會科學的邊緣理論或建構理論等分析工具,「回到[ 上述論述] 發生的時空脈絡,理清其形成的經過,才可能還原歷史的事實」。
張維安的〈東南亞客家華人研究之省思:兼論砂拉越劉善邦現象〉這篇論文,主要經驗分析對象是發生於19 世紀50 年代之砂拉越石隆門的一場華工集體行動,劉善邦是傳說中該行動的最重要領袖。難題在於,自來關於石隆門華工行動或劉善邦現象的研究,不但出現了「叛變、民族英雄或獨立政治實體間的戰爭」等不同結論,晚近有人甚至懷疑到底是否真的有劉善邦這個人的存在。張維安採用了「社會實在 vs. 歷史事實」這個二元架構來鋪陳經驗材料,以便解讀這個「一個劉善邦,各種不同表述」的現象。一方面,如果我們念茲在茲的是所謂「歷史事實」,那麼,各種史料紀錄的確是「查無劉善邦」;另一方面,從「社會實在」的視角出發,我們探查的是「誰需要劉善邦」這個議題,關注的是「劉善邦」這個人/傳說如何廣泛流傳於當地,包括媒體的相關報導和民間傳說,甚至物質遺跡或相關活動。劉善邦的議題就從歷史考察變成了多層次社會實在的詮釋分析。
柯瓊芳的〈族群資料的蒐集方法、趨勢與挑戰〉,則以英國、美國、德國與法國為經驗研究對象,探究這些國家不同的族群/種族資料蒐集方式。對於客家或族群研究,除了社會實在或歷史事實的探究,也必定會觸及族群統計資料,而這類通常由國家所主導執行,以族群進行分類的資料搜集,除了族群分類本身就具高度的政治性之外,族群認定的標準也必定會牽涉「客觀標準 vs. 主觀認定」的爭議。此外,對於是否要收集族群資料,或建立以族群為分類的人口調查資料庫,各國政府因為不同的歷史經驗,也各自採取不同的作法。這篇論文分析比較了上述幾個國家對於族群或種族資料搜集的方法、趨勢與挑戰,藉此提供臺灣進行族群資料搜集的參考,也提示研究者在使用族群統計的量化資料時,不能抽離個別社會脈絡以及搜集資料的目的。
(二)質性研究一:置身事內
「主客關係」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要關鍵字之一。從實證主義的立場出發,「主客體分離」、或「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二元對立」,基本上就預設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的關係是截然二分、互相分離的,即使研究者承認自己特定價值的存在,其主要任務是將這些「主觀」因素加以控制、甚至排除,從而獲得和研究對象有關的「客觀事實」訊息。然而,如果從後實證主義的視角來看,「主客體分離」的預設顯然是不切實際。一方面,由於「價值」和「事實」間不易區分,研究者所宣稱的「價值中立」並無法成立。另一方面,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都會存在相當程度的「相互影響」,也就是「互為主體性」。
本書第二部分「置身事內」的三篇論文,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對象的一份子,三位作者從個人的經驗出發,分別從敘事分析和民族誌的方式提供具體實作的研究範例,並展示了主體性之相互建構的意義。宋文里的〈言說主體與客家敘事〉,分析對象是作者以自身經驗為素材所寫的一篇「自我俗民誌」式文本。雖然作者本人是竹東長大的客家人,但家裡講的卻不是當地的海陸腔客語,而是祖父母講的四縣腔客語,因此對客語「一語多腔」之情境有十分深刻的體認。之後搬遷到桃園福老1 地區的經驗,又讓作者下定決心學會「廣播腔華語」,而終於領悟到客家人身為弱勢族群的悲哀:不是學福老話,就是要學華語,反正就是要學個比客語更強勢的語言。透過作者所自行發展出來的所謂「敘事分析」三原則─(1)「語境重設」(recontextualization);(2)「語意革新」(semantic innovation);以及(3)「『已說』和『未說』之間的『相反相成』或『辯證的相互建構』(dialectical mutual construction)」─以上述文本為準,探問了幾個客家研究的重要提問,比如說客語和(同為「母語」之)福老語的關係、客語和(作為共通語之)華語的關係、不同腔調之客語的關係、乃至多腔語言所帶來之「多語學習機制」可能性的問題。
在〈相遇中的建構:敘事探究取向與客家研究〉這篇論文中,李文玫強調客家研究是由人組成、關於族群和人的學問,因此「研究者就是研究工具」。通過敘事探究,研究者和自己也和研究參與者交會,共同建構研究的主體。文中介紹了生命故事訪談法、敘述訪談法以及深度訪談法這三種常用的資料搜集方式,並成為接下來敘事分析的文本。作者強調敘事文本解讀與詮釋分析的過程,就是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互為主體性」的交會行動,而個人的敘述同時也交疊著主流文化敘事的成分。文中以客家女性的生命敘事,梳理出所在的社會文化脈絡,透過這些個人的故事反映社會文化的樣貌,也讓敘事主體察覺與反思社會壓迫的所在,因此敘事研究的行動,不只是學術研究也帶來實踐的可能。
洪馨蘭的〈轉熟為生的民族誌辯證取徑〉,主要旨趣在於針對初學者介紹人類學的田野民族誌如何可以應用在客家研究上。傳統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以及民族誌書寫而發展出來的方法,大多是長期居住、往返而探究他者的異文化報導記錄。
只是目前客家研究卻出現大量客家人研究客家社區的趨勢,下田野不再等同於置身陌生的境地,反而是「返家」。就此而言,原先人類學傳統的田野教戰手冊,所教導的是研究者如何「轉生為熟」,從局外人的「客位觀點」學習當地人思考的「主位觀點」。但在以己身文化做研究對象的情況下,研究歷程就必須翻轉為「轉熟為生」,跳脫作為當地人熟悉的局內人思維,學習以局外人的觀點來看自己的文化,才能產生對現象的敏感意識,長出「他人之眼」。作者從個人研究的經驗中,提供了幾個具體的策略,強調透過田野的進入/返回、沉浸/超出等動態來回的辯證互動,培養抽離日常熟悉的思維。對帶著熱情要進入客家研究的客家學子而言,本文提供了極其實用的引導。
(全文未完,詳見《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導論)
張維安、潘美玲、許維德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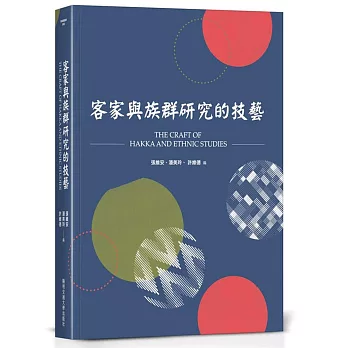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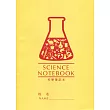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