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在各種愛的斷井頹垣中,開鑿家的新意義
陳育萱
擅長寫詩,也出版過三本詩集的瀅靜,為數可觀的詩作中,總有小說意圖匕現,此中彷彿有一株含羞草,變種的銳刺偶爾勾人血珠。不過正式落筆為小說,瀅靜的文字化身豬籠草,網羅變異怪奇的蟲體,將之納入每則故事袋囊。我以為她將小說視為入世活物,以活物探取活物,練蠱之旅總在途中逗弄挑釁,當小說完成之前,無人能預知蠱王的樣貌。其實,創造牠的豢養者也不知道。
練蠱地點,瀅靜攜來裸露屋脊與樑柱、沙漏或者黏液,交錯搭建了家之群象。倘若讀者緩步在各篇小說轉側,便能一一收集預售屋、新成屋、中古屋、新古屋,甚或是山洞的一爿景觀,接下來發生什麼,端賴書中角色。與其說預期這些角色能完整家之場景,更不如理解為,小說企圖傳遞的是讓讀者窺視那些即將漏光的碎片,其斷垣殘漆,斑駁垮散。然而,看似亟待重建粉刷的場域並不可怖,使人悚畏發寒的都是無法被歸類的關係,這些永遠無法被收攏妥善的岔出線條非關罪愆,它只是不斷脫軌,以失速歪斜的角度,刻意闖壞一幢幢貌似穩固的家。再者,人物情感意向強烈非常,不均衡的糾纏扭曲多半是自身所擇,怨懟之餘,本能接招,用自己的沙漏對應對方的斷樑,沒有誰能解決誰的問題,在小說裡,人物趨向一起荒蕪。
逕自荒蕪的渴家之人,散發揮之不去「背棄╲被棄」感,雖未曾浮現慘到底的結局,不過置身其中,森然詭譎的陪伴關係,步步險途,母親的情敵可以成為自己的伴,換下一篇母親也能成為自己的情敵。細究眾篇小說,母女關係尤其酸澀,尤其總與父親相左的教養意見,加上跟女兒之間的疏遠淡漠,女兒逆骨的源頭其實是夫妻失衡的結果。說到母女相處的家庭課題,向來遠非單純弒母情節可概括,瀅靜的處理翻陳出新。例如〈母親島〉中,主角陽陽年幼時的她,下意識搶奪了父親的關注,變相弒除母親。陽陽年長後交往的對象,俱如父親那般年歲,而父親卻找了如她年歲的第二春。她自忖,「如果對跟年輕女孩交往有一種類似亂倫的愧疚感的話。那麼年輕女孩在跟像父親的人交往時,是否也會產生愧對母親的罪惡感呢?」除了罪惡感,情緒又轉了一層,「該為母親復仇嗎?身為一個女兒該如何為母親的感情陳冤得雪,譬如可以傷害父親嗎?」不只弒母,還當弒父。〈三人餐桌〉這篇,芹作為小三,應邀進入小蘋、父親大偉、母親麗美的餐桌。麗美從這個家離席,取代她的芹成為小蘋的後媽,在大偉死去,兩人相依作伴的過程裡,小蘋開始中性化,而慾望對象逐漸變成芹。潛意識比什麼都直接,小蘋形容「父親喜悅激動的那張臉,越看越像自己」,不知何時,少女時期窺見的那次性事到現今,已經重奪主動權。情感上的弒父已經完成,因此,在百日時殺生(打死那隻驚嚇到芹的蟑螂)也不算犯忌了。窺視原生家庭父女、母女關係之餘,瀅靜挑戰讀者試著想像愛上父親母親,並備註「後父╲母」亦可能成為愛欲對象的可能。
這樣足以讓尚未成形的關係構成一個家嗎?
除了這樣令人心酸揣問,多元成家是否可能,也是她的探問。有些篇章不由得使我想起邱妙津,當然不單純是女女同性之戀,而是其中探犯禁忌的氣味。〈女校〉這篇,明喚與譚譚同為學校老師,同事情誼不知何時漸變曖昧,學生小鬼趁亂直球對決,毫不遮掩對明喚的喜歡,明喚為此時感淤潮軟爛。愛與其他關係的邊界,恆常斷層,而明喚對愛的認識與經歷又似乎能在小鬼與譚譚身上溯接過往或預見未來,愛情之於三人,她恍然原來是飽受情感痛擊的點滴正鑄造著每個年紀的女人,情感作為刻刀,眾人的目光是益發令人悚懼的刻刀。圓滿的愛情關係,已不只發生在彼此之間,它顯然必須向群眾證明,小至社群媒體,大至實境節目,都能是展示關係的場域,也成為窺視者入侵的渠道。〈實境家庭〉這篇,未曾走紅的王碧玉、陳政軍,加上一位被製作單位安排領養的女孩茉莉,一個幸福家庭的實境秀於焉揭幕。實境錄製的家庭生活,究竟有多少能排練預演?就連男主角將一疊用來安撫父親的鈔票矯飾遮掩作父親餽贈婚禮的心意,觀眾也未曾察覺,因為他們留意的是雙方家長是否同意這樁眾所期待的婚姻?所有目光集中的俄羅斯娃娃,拆組層層套疊,核心出現鑽石,乍看浪漫驚喜,鏡頭轉遠,王碧玉卻疑神戒指中或許藏著針孔攝影機。
鑽石是信物,反過來看,也是情感綁架。為了償還鑽石之貴重,以更為珍重的人生付出交換。除了鑽石,各篇畫作、書本、信物,都能暗自察覺流動之中那些不好說破的話,不安全的關係,幾乎就是所有人物互動的基礎。武斷地說,這些小說作品裡沒有任何甜美,橫溢瀰漫的是未能結痂的傷口氣息。失衡的一景又一景,正是傷口的現實化;夢境,也是傷口的另一種變形。本書中,家與人都是用來探測新關係,所有角色都對家的組建方式產生不一致的想像,更有不少角色就是駭異想法的自身,它們的存在改變了現有家庭的僵固想像,於是被我們從無數希望粉末裡遽然凝視。
我想,瀅靜的企圖或許是回應不停滾動的時代,指出其模樣與理解的路徑早已需要更新。更新,就是寫小說的人,面對龐然多語世界的一道必然姿態。
瑪格麗特.愛特伍在《與死者協商》裡提及:「『詩不屬於寫的人。』《郵差》一片中,那個偷詩的小人物郵差對詩人巴布羅.聶魯達說。『而是屬於需要它的人。』」她認為,關於任何作品,唯一該問的問題是─它是活,還是死?能夠和讀者互動的文本,才是活物。這本《沙漏之家》作為瀅靜的首本短篇小說力作,我相信它的確能撐開一個與讀者互動的場域,一起在各種愛的斷井頹垣中,重新開鑿家的意義。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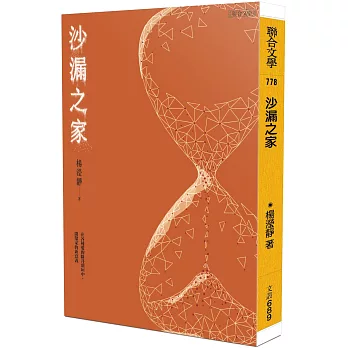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