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歲月把父輩的一九四九年越送越遠。
望著那一代人漸行漸遠的身影,我有追上去多看一眼,多聽一個故事的衝動。師長父輩中,有不少生於二、三十年代的大陸,於一九四九年前後,遷移到臺灣來的「知識分子」。在我心目中,他們是所謂的「民國人」。經過戰亂,逃難,遷徙,身上有一種叫「學識」和「風骨」東西。
我在他們身上,學到許許多多,自認一生受用。那是一個漸行漸遠的年代。我輩中人,也許再也找不到跟「他們」一樣的人了吧。
儘管對「民國父輩」有著懷舊和感激,但通俗小說和電影裡,「民國」卻似乎一直與腐敗,軍閥、大小姐、上海灘的話題掛鉤,與「黑幕」二字不可分割。比如張恨水的小說、阮玲玉的電影。
更有趣的是:八○年代初,我在美國校園裡,結識了一群大陸菁英。他們是曾經革命串連,「上山下鄉修補地球」的一代。大家成了好朋友,他們屢屢開我玩笑,稱呼我為「民國人」。原因不過是:民國人有禮貌,常說「謝謝」、「對不起」。
「民國」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的父輩師長們,是從哪裡得了那些叫我喜歡的「樣子」呢?
於是有了這本訪談集。
我找到一九四九年前後,渡海來臺的幾位女性文壇前輩,請她們告訴我「她們的時代」。在那個叫「民國」的歲月裡,什麼才是「重要的」?
齊邦媛老師把「文化深度」喻為「潭深無波」。林文月老師,把「望月樓的月亮」 (她在校園中的名號)定調為「實實在在過生活」。坐過十年冤獄的作家黃美之,願此生歲月「不與紅塵結怨」。爽氣豁達的專欄作家薇薇夫人(樂茝軍)以「靜靜拿起一本書」 面對人生低谷。余光中師母(范我存)把「妥協的藝術」視為婚姻的必要,稱其為:「一加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我也問張曉風老師,為什麼給自己取個筆名叫「桑科」。她說,「那是唐吉訶德侍從的名字,當不了唐吉訶德,也要當他的侍從。要盡力讓人知道,臺灣這些人是好樣的。」
最近,看了一部電影,叫《愛爾蘭人》。講的是半世紀前美國工會,幫派勢力,與政治之間真人真事的故事。片子足斤足兩三小時,裡三層外三層,剝洋蔥一樣慢慢講著一個漸漸遠去的年代,人和人間的情分,糾葛,和決絕。演員個個經典,舉世皆知的音容笑貌。
這部電影,有人喝倒彩,有人大讚。不喜歡的人認為:太慢,演員不對,節拍不對,怎麼怎麼地不對勁。對他們來說,電影就是電影,成敗論英雄。但對喜歡的人來說,卻完全不是那回事。因為這是部電影,卻也不只是一部電影。他們親身走過電影中這一段「漸行漸遠」的美國歷史,跟著這幾位經典演員以前的每一部電影長大。他們是電影中,也是電影外的「那個時代」的一部分。成就片裡片外,雙重的「漸行漸遠」和懷舊。怎是好壞成敗說得清的?
對我來說,這個訪談集也是如此。
二○一九、十二、十六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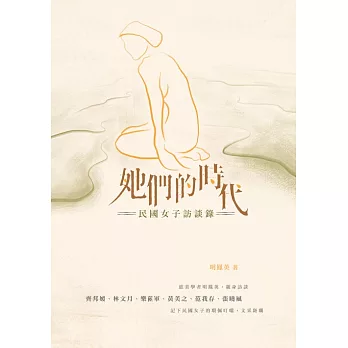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