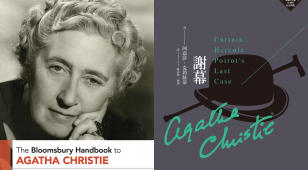推薦序
藏在日常細節中的冒險
楊照(作家)
一開始,就都在那裡了。
一九二○年,阿嘉莎.克莉絲蒂出版了《史岱爾莊謀殺案》,神探白羅就已經退休了。而且在這個案子裡,藉由敘述者海斯汀的轉述,就鋪陳出克莉絲蒂小說最基本的偵探原則:
「那些看來或許無關緊要的小細節……它們才是重要的關鍵,它們才是偉大的線索!」
「豐富的想像力就像洪水一樣,既能載舟亦能覆舟,而且,最簡單直接的解釋,往往就是最可能的答案。」
「沒有任何謀殺行為是沒有動機的。」
還有,一個不討人喜歡的死者,一群各有理由不喜歡死者、因而也就都有殺人動機的人,這些人彼此之間構成複雜的關係,有的互相仇視,有的互相愛戀,麻煩的是,有些愛人其實貌合神離,有些仇人其實私下愛慕;更麻煩的是,不論是愛或是仇,都有可能是扮演出來的。
一個外來的偵探必須周旋在這些嫌疑者之間,從他們口中獲取對於案情的了解,換句話說,他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搞清楚誰是誰、誰跟誰吵架、誰跟誰偷情,然後判斷誰說的哪一句是實話、哪一句是謊言。常常謊言比實話對於破案更有幫助。
再偷偷透露一下,如果要和小說裡的凶手及小說背後的作者鬥智,就像克莉絲蒂對英國社會的了解,祕訣就在於要去追究小說裡的人物背景,尤其是他們的階級地位。基本上,階級地位愈高、權力愈大、愈有錢者,說的話就愈不要相信。例如在《史岱爾莊謀殺案》中,僕人、園丁說的話遠比有頭有臉的人說的要可信多了。就算要說謊,他們的謊言也比較天真,而且往往出於善良動機。當你歸納線索時,就會知道他們並非故意說謊,那是因為他們的認知受到蒙蔽或誤導,而你慢慢就從這蒙蔽或誤導中被引導到真相。
《史岱爾莊謀殺案》出版那年,克莉絲蒂三十歲,但書稿其實早在五年前就寫好了,畢竟要找到有人願意出版一個看來再平凡不過的家庭主婦寫的小說,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有和克莉絲蒂接觸過的人,都對於她的「正常」留下深刻印象。她看起來就和她那個年紀的典型英國家庭主婦一樣,害羞、靦腆,只能在社交場合勉強跟人聊些瑣事話題,完全無法演講,甚至連只是站起來對眾賓客說幾句客套話,請大家一起舉杯,她都做不到。她不演講,也很少答應接受採訪,就算採訪到她也很難從她口中得到有趣的內容。她會講的,幾乎都是記者本來就知道、或者自己就可以想得出來的。
例如說白羅這個神探的來歷。克莉絲蒂回答:他應該是個外國人,這樣就能在英國日常生活中看出英國人自己看不出的線索。她自己碰過的外國人,只有第一次大戰剛爆發時到英國避難的比利時人。比利時警察怎麼能跑到英國來?那一定是因為他已經退休了。他有潔癖,所以對於現場會有特殊的直覺,馬上感受到不對勁的地方。一個有潔癖的人,好像應該長得矮小些才相稱,一個矮小有潔癖的人最適當的名字,就是希臘神話裡的大力士「赫丘勒斯(Hercules)」,製造出荒唐的對比趣味。那白羅這個姓是怎麼來的呢?克莉絲蒂很誠實地說:「我不記得了。」
一切都如此順理成章,一切都如此合邏輯,不是嗎?有記者問她怎麼看自己的舞台劇〈捕鼠器〉,創下了英國劇場、甚至全世界劇場連演最多場紀錄的名劇?克莉絲蒂的回答也還是中規中矩,合理合節:那是一齣小戲,在一個小劇院演出,成本很低,任何人想到了都可以帶家人或朋友去看,老少咸宜,並不恐怖,也不特別荒謬打鬧,可是又什麼都有一點,包括恐怖和荒謬打鬧的成分。
她的身上找不出一點傳奇、怪誕色彩,那她為什麼能在五十年間持續寫偵探小說,創造了那麼多謀殺,還創造了那麼多詭計?
首先因為她是女性,以及她的身世,包括她的階級身分,使得她在描寫故事場景時比一般男性作者來得敏感。因為在她之前的偵探推理小說男性作家的階級身分都是高高在上,基本上他們會從較高的角度看社會,比較看不到底層的感受。
而她的婚變以及婚變中遭逢的痛苦,都使她更能體會與觀察,將英國社會的複雜細節融入小說的核心情節,讓探案與線索分析結合在一起。
克莉絲蒂一生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在一九一四年,婚後不久,丈夫就參加了歐戰,是英國皇家空軍最早一批飛行員。一九二六年,這個丈夫有了外遇,直率地向克莉絲蒂要求離婚,在那之前,克莉絲蒂的媽媽才剛過世,雙重打擊之下,又遇到車子無法發動,克莉絲蒂崩潰了,她棄車而走,忘記了自己究竟是誰,躲進一家鄉間旅館,登記時寫了她心裡唯一有印象的名字──她丈夫情婦的名字。
離婚後,一次在晚宴中,有人提起近東烏爾考古的最新收穫,克莉絲蒂就取消了原定要去西印度群島的計畫,改訂了跨越歐洲到君士坦丁堡的「東方快車」,是的,就是這趟旅程給了她寫《東方快車謀殺案》的靈感。不過更重要的是,在烏爾,她認識了一位年輕的考古學家,比她小十四歲,這個人後來成了她的第二任丈夫。
這位考古學家陪她去參觀在沙漠中的烏克海迪爾城,卻在沙漠中迷路困陷了。幾小時中克莉絲蒂卻沒有一點驚慌不安,當下考古學家就決定要向她求婚。
原來,克莉絲蒂的內心是有這種冒險成分的。要不然她不會兩次選到的,都是喜愛冒險的丈夫,而她本身大概也不會吸引一個在各種危險情境下挖掘古代寶藏的人,讓他願意向一個大他十四歲的女人求婚。
這樣說吧,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英國環境,壓抑限制了克莉絲蒂冒險、追求傳奇的內在衝動,她只好將這樣的衝動寄託在丈夫和寫作上。她一邊陪著第二任丈夫在近東漫走,一邊在小說中寫各式各樣的謀殺與探案。謀殺和探案都是冒險,還有,偵探偵查中做的事──蒐集線索,還原命案過程──其實和考古學家的考掘,如此相似!
克莉絲蒂寫得最好的,正是「藏在日常中的冒險」。她個性中的雙面成分,造就了特殊的偵探魅力。既嚮往非常傳奇,卻又有根深柢固的日常邏輯信念,兩者就都在克莉絲蒂的小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謀殺案幾乎都和日常習慣緊密編織在一起,日常環境成了凶手最重要的掩護。有些日常規律明顯地被破壞了,讓我們很自然以為那會是謀殺的線索,沿著這些線索形成了閱讀中的推理猜測,然而白羅早就提醒了,真正重要的反而是那些「細節」,也就是看來像是依隨日常邏輯進行的事,或說藏在日常邏輯中因而不被看重的事,那裡要嘛藏著凶手的核心詭計、煙幕,要嘛藏著凶手致命的破綻。
凶案的構想,就是如何讓異常蓋上日常、正常的面貌,又如何故意將日常、正常予以扭曲,製造假象;那麼偵探要做的,就是如何準確地在日常中分辨出真正的異常,將假的、明顯的異常撥開來,找出細節堆疊起來的異常真相。
此外,克莉絲蒂的小說裡隱藏著極其曖昧的情感價值觀,最典型、最有名的就是《東方快車謀殺案》。透過追查過程,讓讀者知道為什麼凶手要訴諸於這種手段,其動機具有可同情之處,再加上克莉絲蒂對身分階級的觀察,她比較相信或讓讀者相信那些沒有權力、地位的人,隨著偵查節奏去認識可能或必須懷疑的人。克莉絲蒂最擅長營造「多重嫌疑犯」的小說特質,因為讀者在閱讀時必須被迫去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在她最受歡迎的作品,大概都具備這樣的特質。
當然,她的作品中還有兩個最突出的神探,即白羅和瑪波。白羅是比利時人,但為什麼必須是外國人?這是因為英國人具有高度階級意識,這種觀念一路滲透到所有互動細節,包括人與人之間如何說話。而白羅因為不是英國人,他會發現一般英國人不太看得出來的東西,以及兩個人互動的方法哪裡不正常。至於瑪波為什麼得是老太太?她一如那個年代的老人家,總是靜靜坐著打毛線,因為不起眼,自然讓人放鬆防備,所以瑪波探案的線索都是來自於這樣的互動模式。
然而,白羅有很明顯的優勢,瑪波的身分使她基本上只能進行「靜態」的辦案,案子的空間受到侷限,白羅卻可以跨越各種空間,恣意揮灑。而且白羅擁有警官身分,可以合理出現在各種犯罪現場,瑪波能出現的地方,相形之下就勉強、不自然多了。白羅是明白的outsider,在英國,只要他出現,就會覺得有外人在而感到緊張,於是很容易露出平常不會表現的行為;瑪波則看起來是insider,但實質上是outsider,因為總是沒人發現她、當她空氣人。這兩人的探案,是兩個極端。雖然讀者最愛白羅,但克莉絲蒂自己偏愛瑪波勝於白羅。
不管後來的偵探、推理小說發展了多少巧妙詭計,克莉絲蒂卻不會過時,因為她的推理如此密切地和日常纏繞在一起;活在日常中,我們就無可避免被克莉絲蒂的「日常細節推理」吸引,隨時讀來都充滿驚奇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