噹!噹!噹!
二○○五年七月,外雙溪畔的柳樹微微彎腰,聆聽著炎夏蟬鳴裡,似有若無的,小學堂的鐘聲。
那一年,我剛剛在大學升等為教授,卻覺得生命悄悄的停頓了。每天仍努力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教書以及創作,卻是在原地踏步。
生命應該是一條河,哪怕速度很緩慢,也應該往前流動著。
孔子是這麼形容生命之河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我的生命之河,在我成長之後,確實流動得緩慢了。
單身與未生育,使我的女人身分一直都只是個女兒,缺少了母親的體驗。我撫抱過嬰孩,卻不是母親的姿態;我注視過孩子奔跑的背影,卻不是母親的眼神;我曾經纏綿的愛過人又疼痛的割捨,卻不是母親的艱難。
一年一年過去,我感知到了生命的凝滯,卻是無能為力的。
二○○五年,在幾個好友的鼎力相助之下,我還願似的開辦了「張曼娟小學堂」夏令營的課程。原本只是想帶著國小的孩子「讀經」、「讀詩」與「創作」,卻沒想到,一個巨大的轉機開啟了。
夏令營借用「錢穆故居」舉辦,交通並不便捷,卻仍有那麼多家長,不辭辛勞,頂著豔陽,接送孩子。而我們也見到短短五個半天,孩子可以有多大的改變,這樣的效果,其實是出乎我的預料的。
「夏令營之後呢?」許多家長都在問。
「只是夏天上課是不夠的啊,可不可以規劃一系列的課程呢?」我們接到不少這樣的電話。
但,我明白,一旦這個空中樓閣落地生根,我就不再是現在的我了。工作量更繁重,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閒更稀少,也許連我最愛的發獃時刻也會消失。我確實考慮了一陣子,那段時間,與教育政策相關的新聞,每一條都令人感到憂慮,以及慍怒。於是,我做了最後的決定。
噹!噹!噹!
二○○六年五月,「張曼娟小學堂」在台北城的市中心,捷運站的出口處,安頓了第一個家。最令人喜悅的,是與一株宛若巨傘的芒果樹比鄰,已經有二、三十年樹齡的芒果樹,長得有五層樓高。像個守護神似的,守護著我們在季節中成長的每一個孩子。
每個星期,小小孩與大孩子從四面八方來,他們有時候膩在我身上背書;有時候牽著我的手聽課;有時候不明所以的衝過來攔腰抱住我,緊緊的,彷彿永遠也不想放開。那些大一點的孩子,或許矜持一些,可是,他們還是渴望被注意、被稱讚、被安慰與環抱。遇見國語文程度原本就很不錯的孩子,我便思考著,還能給他們哪些不同的激發,讓他們超越自我?遇見國語文程度欠佳的孩子,我思考的是,該怎麼鼓勵他們,讓他們找到自信,有勇氣挑戰自我?
在芒果樹旁,我開始體驗作為一個母親的角色與經歷。我把每一個孩子,都當成自己的孩子。愛他們,而不強制他們成為我期望的樣子;不期望,卻能影響他們,讓他們走在最適合的道路上。
於是,夏令營、秋光營、春日營,漸次展開。而我已停頓的生命之河,又開始潺潺地,歡快地,向前流動。
噹!噹!噹!
二○○八年七月,新的學堂在景美打造著,我們在芒果樹旁的學堂裡辦最後一次夏令營。從西班牙、德國、加拿大、新加坡、香港來的孩子們,令我們的聚合更為國際化。許多從南部或中部來的孩子,由父母親送到台北,度過小學堂的暑假時光。
有個少年,每天獨自搭乘高鐵,往返新竹與台北,他伏案振筆疾書,寫著作文,我看見他開啟的鉛筆盒裡,那張「台北-新竹」自由席的高鐵票,忽然之間,太多情緒紛紛湧起,無法承受,感動、疼惜,還有許多說不清的,化成一股酸楚,即將變為淚水。而他突然抬頭,望著我,給了我一個燦爛歡愉的笑臉。那笑容如此明亮,像是一種宣告:在這裡找到了他想要的,他很快樂。我於是向他點點頭,無言,也無淚了。
「為什麼我的小孩到這裡來,就心甘情願的背古文、背詩詞?之前我怎麼威脅利誘,他都不肯背!現在每天回家自動背,還叫我幫他聽聽看背得夠不夠熟?你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啊?」夏令營的家長問。
我想到秋光營的那個母親,攬抱著兒子,對我說:「老師!我覺得你們很神奇,真的不知道你們是怎麼做到的?就像是Magic touch!」
Magic touch!那是什麼?我無法具體形容。也許是一個環境吧,一群工作夥伴,老師們、孩子們、家長們,共同創造的一種氛圍。歡樂的、安全的、溫暖的、充滿創造力的,我夢想的,一個小小的學堂。
噹!鐘聲是一種召喚,把孩子聚在一起,有些孩子是孩子的形貌;有些孩子是成年人的形貌,但,我們一直聆聽著,學堂的鐘聲。
噹!我們同在一起,生命的河流,不舍晝夜,終將匯聚成一片海洋。所有的生命,都是自海洋孕育而成的,不是嗎?
張曼娟
謹序於台北盆地
二○○八年七月大暑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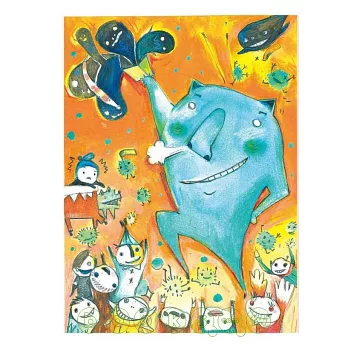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