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歸去來
距離上一本出版,平路已經讓她的小說讀者翹首企盼了八年。再出手,平路很有誠意地推出顯然經過長久籌備蘊釀的長篇小說,一樣是她拿手的以女性敘述觀點折射歷史政治的重層皺縫,一樣運用擅長的後設互文虛實環扣,卻有更意味深長的寓寄。平路的題材選擇和詮釋觀點總有別出心裁的慧眼。早在歷史書寫蔚為風潮之前,她就寫出一系列嘲諷臺灣奇蹟和民國史的小說,當大河小說此起彼落之際,你以為久駐香港的平路會以香港或臺灣歷史為題。猜錯了。這一次,平路瞄準的是兩岸關係波濤洶湧的今世與前生。
八、九○年代以降,包括平路在內的不少臺灣當代作家,採取以女性或另類的發聲位置去質疑主流的論述與價值,類似的寫法常會被評論家解釋為是以小博大、據邊緣反中心、以私我感性顛覆父權理體的書寫策略。以這樣的詮釋觀點來解讀平路雖然適切猶有未盡。誠然表面上平路不懼憚呈現出對立的兩極,並且加重了弱勢端的砝碼,她最深刻著墨的倒不在於對抗,而是兩端辯證的關係。她的小說情節也都是扣合著辯證中翻轉的競合矛盾去推演鋪陳男女、主客、強弱的相對關係。平路對辯證法的興趣使得她的小說常常處於一種偵查懸疑的中間狀態(in between),推理小說的通俗敘述模式承載的其實是綿密緊湊的邏輯思辨。辯證法本來就是與文法和修辭學並重的學問,藉由爭論與辯駁進行推理模擬,從命題到反命題再到新的更高的統合。平路的辯證思維顯然比較趨近阿多諾提倡的「否定的辯證法」,否定歷史進程會循正反合的進步模式發展。這套辯證法的主軸旨在批判看似「自然而然」因此獲致正當性的「真實」,對於真正的主體性是否得以恢復亦感到悲觀。因此,不管是《行道天涯》、〈百齡箋〉或是《何日君再來》, 平路做了種種還原歷史人物凡人面貌的嘗試,目的並非是想脫離歷史現實另立一個新的形象。畢竟正是特定的歷史語境造就了人的非凡與平凡。小我的故事與時代社會如何共生互利、如何拉扯角力、相互影響震盪的過程遮蔽壓抑扭曲犧牲了什麼?最後織就出什麼論述?其間種種的明暗折騰、可說與不可說的行為心事、歷史的偶然巧合與弔詭反諷,方是平路小說用力和精彩之所在。與其說平路想批判歷史∕人物或為之翻案、追溯歷史∕人物更多面向的真相,不如說是借前者的連環曝光攤開了真實與主體的不確定性。
《東方之東》的敘述話語和情節編排同樣暗藏平路式的玄機。在層疊穿插的障眼法下,不妨以文本內較為鮮明的三組二元辯證法來理解這部新作。故事的現實層始於一個臺灣女人到北京去追查臺幹丈夫的失蹤案,期間收留了一個被公安追捕的民運男子進而發展出戀情最終人財兩失。她的先生其實為了保護一個誤犯刑責的大陸女子雙雙隱姓埋名逃到澳門,同時間透過一封封未寄的家書細述他選擇拋妻自毀的心路歷程。故事的歷史層則出自臺灣女人的筆下,小說中的小說, 描寫鄭芝龍降清陪侍順治皇帝時,不斷講述關於大海和臺灣的異聞奇景,企圖引發帝王對海權的想像委以拓殖海洋帝國的重責;順治與鄭成功則透過鄭芝龍各有招安與獨立的謀算。小說的現實層對應兩岸男女社經情感交流的狀況,讀者不難有各自的詮解。小說的歷史層中鄭氏父子相異的政治立場以及滿清政府的策略,一方面類比小說現實層裡不寫、但顯然是此書念茲在茲的臺海關係。另一方面歷史幽靈的輪迴宿命似乎寓示著,兩造(兩性、兩代、兩岸)對彼此的了解想像與期待,儘管有難得的時光交疊隙縫,往往在單向度的對(不上)話中錯判與錯身。
除了上述較為一般的二元法,小說結構裡還有作家專擅的另一組辯證,話語和物質。在平路過往的作品裡話語的力量和物質的樂趣是反覆出現的母題和內容。《東方之東》不例外地出現不同形式的話語:臺灣女人和大陸民運人士講的自己故事、逃夫寫的信、公安的簡報和公文、女主角構想的小說、小說裡鄭芝龍說的軼事、順治君臣的奏章……鄭芝龍希望用故事影響政治的企圖乍看猶如天方夜譚。但《天方夜譚》的女說書者雪賀拉莎德即是憑藉著故事換取生命甚至換來地位與名聲。古代的縱橫家與說客不也做過將話語權力極大化的成功示範?話語是弱勢者的利器。馬上得天下的君王一聽入迷, 主導權可能就落入嘴裡的江山。 鄭氏與順治的對話也讓我們想起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裡,安排馬可波羅對忽必烈講述的域外城市百態。經由馬可波羅博古通今的描述,忽必烈和讀者, 了悟到,真實只有在虛構的話語中得以再現與記憶。
相應於對話語以及抽象論述的興趣,平路的作品一向對於感官和物質生活的描寫同樣津津樂道。女主角日常起居的細節、家裡的擺設用品、以至城市中街坊邊的飲食氣氛口味在小說中都有詳緻的描繪。有趣的是,小說裡具備良好教養和品味的中產階級夫妻,一個投入菸酒不忌、邋遢傖俗的歡場女子懷裡,一個受滿口粗話、不修邊幅的騙子吸引。好萊塢電影裡,男人愛上女人對她致上最高敬意的情話是,You make me want to be a better man,在這本小說卻變成莫大的詛咒。想要成為比真實自己更好的人太辛苦,粗糲的感官反而令人放鬆,雖然伴隨著一定的代價。
在《東方之東》以及前作中,作家總是再三強調文字話語的魔力。誠然,若非這股執迷信念,寫作者何能長久堅持筆耕。弔詭的是在這本書裡相信話語的都是上當的人,話語產生的作用也未必一如預期。敏惠寫一官說服順治的小說,著迷於捕獵主客間的張力,全然不知自己早就吞下民權份子故事的餌。一官使出三寸不爛之舌遊說順治打造大航海時代,不料勾引出帝王個人驛動的心,朝中無靠山的鄭芝龍終於難逃逆賊家屬的結局。謙一聽信了小美的悲慘遭遇不惜亡命走天涯,說到底,這女人犯上的事是真是假?風塵女子不常有幾套淪落或急難的說詞誘騙有救美欲望的恩客嗎?根據這樣的邏輯,敏惠和謙一雖則在最後的書信中總算是對上話、坦誠道出對彼此對婚姻的感受。這些自白是有效的雙向溝通?還是另一種自白體的敘述文類、做自我的內視淨化?喁喁獨白何嘗不是自我展演最純粹的形式,在話語的絕對沉溺中布置或遮蔽意義的讀取?真實與謊言在辯證的衍繹中始終籠罩著層層迷霧。
第三組則是消失與重現(fort/da)、逃離與回歸的辯證。消失∕重現是佛洛伊德有名的心理分析例證。佛洛伊德把小嬰兒丟玩具讓它不見再順著繩子把玩具拉回來的遊戲,解釋為是嬰兒對某種無意識的失落(出生、母親)的象徵性克服。 拉岡接續衍生,正是原初喪失客體∕母體的匱乏感,逼出敘事的原型,迫使我們在無止境的言說運動中尋找替代品,而且儘管客體重新出現,也無法解除再次消失的擔憂焦慮。簡單來說,敘事的古典模式即是失而復得的原型:某人某物不見或某種秩序瓦解了,讀者忍受著劇情的延宕與懸疑尋求著結局大團圓,或至少某種程度的回復。消失與重現的心理狀態亦類似我們與家鄉的關係,離家的時候想返家,回家的時候想逃家,往與返、來與去的情結反覆翻攪。欲望的匱乏與焦慮引發敘述的填補,小說裡的鄭芝龍如此、敏惠如此、謙一和尚軍亦如此。這個離與返的心理原型甚至應當溯源自平路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玉米田之死〉、 稍後的〈百齡箋〉以及《何日君再來》。
既然原初的欲望緣於分裂或匱乏,人只得欲求他匱缺的另一半,而且總在他者中投射尋找自己的欲望。這說明了小說裡的諸多人物為何總要追逐著他∕她不是、不在的缺角。敏惠欲求更好的家庭生活、謙一欲求越軌、小美欲求從良、 尚軍欲望著他失落的理想、海賊王一官渴望穩定強大的帝國、紫禁城內的順治卻嚮往天涯海角。但是心理學告訴我們,最後自己的欲望就隸屬於他者的欲望,原始的潛意識欲望則在需求中被異化。換言之,欲望永難滿足,唯有在無盡的能指置換和敘事輪迴中追索痕跡。欲望的歸返,或在臺灣,或在大陸澳門,或在東方之東、之東、之東……
為什麼平路的作品這麼愛用辯證法的模式,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心理學訓練的學養,知道人心輾轉幽深難測;也許是新聞專業累積的平衡報導習性,或是小說家對世事的通明練達、又或者就是藝術家的直觀直覺。不斷正反合的推演讓熱中益智的讀者處於腦力激盪,不容諱言也讓人感覺曖昧和游移。當觸及批判性題材的時候,作家客觀的距離造成發聲位置的模糊,迴避掉不同立場的讀者群可能的檢視。所以平路的小說明明飽含了當代許多嚴肅甚至爭議性元素,在各種議題的選材中不見得被視為最典型的範本。
喜歡平路作品的讀者才不在乎這些,她的犀利將否定辯證法的質疑和批評發揮得淋漓盡致,戳破許多偽善和假說,刺得人又痛又清醒。相形之下,《東方之東》倒溫和、保留了些。不知道這是幾年公職生涯培養的謹慎,抑或幾次筆舌風波的後遺症?雖則鄭氏父子應無後人或是狂粉會向平路提告誹謗,順治和鄭氏父子三種立場的追隨者四海都有,一不小心就落入三方夾殺的窘境。旁人即使能大聲應援打氣鼓譟:姊姊妳大步的往前走,但當事人的心頭點滴豈足為外人體會。「公道自在人心」或者什麼「文章千古事」的安慰,不也是言說?是真理還是虛妄?平路還會吞下這麼古典又明顯的餌嗎?我所確定的是,一旦作家磨圓了指爪、無法盡情施展才情與智慮,絕對是個體和全體的損失。既然成為自己不是的那種人不過是徒勞,又何必屈從在他者的欲望。求全或求快?應該是難不倒平路的辯證。
范銘如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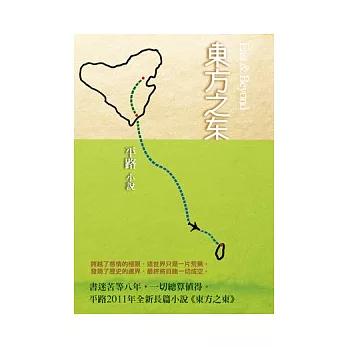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