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酷兒專語怪力亂神 張小虹
有沒有勇氣闖一闖酷兒的擬像視界,瞧一瞧薔薇遍野的標性立異?
《感官世界》收集了紀大偉的七篇文字,展現了一片科幻魔界,滿足初生之犢的衝撞力與企圖心。一路讀來,像是刺激精彩的電玩世界,顛來倒去之餘,有施虐與被虐的促狹快感。
《感官世界》中的遊戲種類,族繁不及備載,以下將僅就「性別遊戲」與「語言遊戲」二項加以穿鑿附會、附庸風雅一番。
在人獸界限都已模糊的世界人(《感官世界》中充斥著人魚族和食蟲族),女/男、同/異性戀,又怎有可能依舊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呢?〈美人魚的喜劇〉以女同性戀的詮釋手法改寫了原先淒艷美絕、痴心人魚化為泡沫的故事,也用大膽無邪的色情文字,挑逗原有「去性化」(de-sexualized)的童話版本。在〈美人魚的喜劇〉中,美人魚俯貼著王子如大法螺般長滿黝黑毛髮的腿,迷惑著他那「挺立磨光的紅珊瑚……脆弱、振奮、張狂」,而王子則在夢中瞥見撒尿的美人魚和她身上「象牙雕鏤的剔透乳房」和「毛絨絨的黑瑪瑙三角地帶」。然而王子與公主並沒有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當王子在馬車上強暴了美人魚後,落落寡歡的美人魚一直尋獲不到應允中的情愛迷戀,直到在夜半的水池旁遇見了另一個「她」。作者用「奧麗維婭」與「薇奧拉」來稱呼這一對女性戀人,逕呼莎士比亞《第十二夜》因扮裝而誤墜愛河的兩名主角,〈美人魚的喜劇〉似乎還給了她們在莎劇中被遏止而被剝奪的情流盪。
〈儀式〉則處理韓與魏二人之間在拜把兄弟般的「同性社會」(homosocial)與「同性戀」(homosexual)間的掙扎困惑,而韓竟也能從對亡父「勇武得像蒼鷹、尊貴得像天鵝」的追念,「移情」到對女兒的迷戀:「韓有種猥褻但貼切的詮釋:彷彿,身著潔白和服的父親,遁離照片中的母親……蜷伏在韓的血液裡……蛻成矯健的精蟲……打自韓的男體射出……假借妻子的子宮……這才造就令韓讚嘆不已的美麗生命……」。
然而這種父親/女兒借屍還魂的混亂,在〈憂鬱的赤道無風帶〉則變成同慶、趙與小刀間欲解還結的女同志愛慾糾葛,但最幽微奧妙的卻是同慶與小刀母親之間貌似親暱、實如情敵(母親視女兒的女友為情敵?)之尷尬角力。但看官切莫驚惶,更大逆不道、不倫不類的絕妙好戲,都將在〈蝕〉與〈他的眼底,你的掌心,即將綻放一朵紅玫瑰。〉中陸續登場:前者中的爸媽皆為男同性戀,共同領養了一對孿生兄弟,但由於媽媽喜著女裝、揚言要變性,終於氣走了爸爸;後者則是在記憶晶片、人體寄生的科幻魔法之外,也安排了男同性戀人,不過做為頂尖科學家的他們,沒採用領養的方式,反倒是將其中一名的精蟲轉化為卵子與另一名的精蟲結合,產生了小說中變性自如的主角。就是如此這般怪異,《感官世界》中沒有汲汲打破禁忌的焦躁與控訴,卻有一而再、再而三「此路不通」卻要連連看的腦力激盪與A、B、C、D、ㄅ、ㄆ、ㄇ、ㄈ的排列組合,嬉笑怒罵過後,記住,寶藏永遠出現在最(不)可能出現之處。
至於「語言遊戲」方面,《感官世界》的機智趣味,有時是會令人拍案叫絕的,SM變成Simulate Miracles之縮寫,像「愛吃病」(AITS)是食蟲族As Insects Teribly Suck的瘋狂傳染,褻玩文字的小把戲,總在《感官世界》中以反諷嘲謔的方式,忽隱忽現。
而「語言遊戲」的規則之一,就是永遠把「你」、「我」、「筆者」、「讀者」、「作者」放入引號。譬如〈儀式〉中的敘事者便大膽質疑、小心求證於主角韓對事件之回憶:「由於韓個人對於戀情,以及同性愛的錯愕、驚慌與恐懼,因此根據筆者臆測,韓平日大概並不大願意回想那段歲月;所以,這時他猛然挖掘出來的記憶,恐怕與當時的真相有相當的落差」;然而在一邊敘述、一邊修正的同時,敘事者更將「事實」比做「一團不斷發脹、不斷分裂的胚胎細胞」,而情節發展因果關係中的「因為」和「所以」只不過被視為遊戲機的代幣:「好不好玩?不知道。唯一確定的是:這兩種代幣像一群一群的黃蜂在空中姿意飛舞,你看不清在鼻頭前跳動的那枚代幣是『因為』中的哪一枚,你甚至分不清它到底是『所以』還是『因為』」。
又如在〈色情錄影帶殺人事件〉中,敘事者為赤裸躺在浴缸、全身捆綁皮件的屍體——奄奄一息臨界狀態下的死者,一個深信「作者,沒有大於作品的時候」的漫晝家,而全篇小說就在「我來、我看、我被征服」的信念之下,由死者一手編導演自己的謀殺場景中完成。這些「後記」的敘事手法、配搭科幻魔界的出人意表,使得《感官世界》成了一大座互文(intertextual)的文字符徵迷宮,不僅角色忽男忽女,遊走亂竄於不同之文本,更相互指涉、雜交繁衍。形構上的「後設」,使悖德得以模擬,使叛逆無上安全。
「玩/頑童」紀大偉有時撒撒野、有時也吊吊書袋,在他魑魅魍魎的文字世界裡,畫蛇理當添足,是為序。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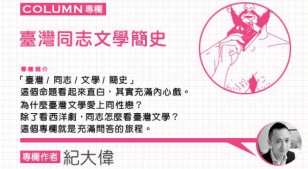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