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歌者使人繼其聲
您現在打開的是一本飲食文化散文。
飲食文化散文,說白了,就是文人談吃的文章;如果要咬文嚼字,按我的理解,它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飲食文化,一個是文化散文。飲食文化是它的內容;文化散文是它的外在表現形式。
飲食,也就是吃喝,實際上更偏重於吃。嬰兒呱呱墜地,便張嘴要吃,沒有母乳,也要吃牛奶或者是米湯,從此吃便貫串了人的一生。貴為天子,「食前方丈,無處下箸」是吃;貧如乞兒,一無所有,衣不蔽體也仍然要吃,乞討就是討吃,吃是最後的唯一。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前面六件事都是吃,後面一件事是喝,開門七件事實際是吃喝一件事。 飲食文化,簡單地說,也可以說是關於飲食的知識。諸如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節令佳品、民族風味,重慶火鍋、廣州早茶,宮廷裡的滿漢全席、大排檔的生猛海鮮、街頭巷尾的臭豆腐烤羊肉串、遙遠飄渺的曹植七寶羹、流傳至今的蘇軾東坡肉、列入典籍的《閒情偶記》《隨園菜單》、口頭流傳的「佛跳牆」「翡翠白玉湯」的傳說,乃至「染指於鼎」引發了鄭國的一場宮廷政變、「破釜沉舟」決定了秦漢時一場戰役的勝敗等等,莫不屬於飲食文化的範圍,它涵蓋了中華民族在飲食方面實踐創造的全部成果。
飲食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我國的飲食文化與戲曲、國畫、書法、園林等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構件,都是中華文化的長存因素。它歷史悠久,博大精深,豐富多彩,享譽世界。外國旅遊者有不到長城、不遊故宮、不吃北京烤鴨、不看中國京劇不算來北京之說,這裡的烤鴨其實是飲食文化的符號。無論是在歐洲的公路邊,還是北美的無名小城,甚至是非洲小國,你都會與中式餐館不期而遇。飲食文化又是維繫炎黃子孫的感情紐帶,飄泊海外的遊子思念故鄉,莫不對兒時家鄉的食物魂牽夢繞。
飲食文化又是一種歷史現象,它隨著社會經濟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一九六五年在我國雲南省元謀縣考古發現,年代約為一百七十萬年前的元謀人遺址中,有很多炭屑,表明元謀人已經知道用火。這大概是人類使用火的最早證據。有了火,先民開始熟食,從此告別了茹毛飲血的時代,揭開了我國飲食文化史的序幕。那時候,先民們靠漁獵維持生存,捕獲到獵物後就圍著篝火邊烤邊吃。詩經小雅︿瓠葉﹀裡反覆唱道:「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燔」是直接把肉放在火裡燒;「炙」就與火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如同今天的烤鴨、烤乳豬;「炮」則是用濕泥之類把肉裹起來放在火裡燒,「叫化雞」便是這種古風的遺響。看來燔、炙、炮是中華飲食中最古老的烹調方式。把這三者再比較一下,似乎燔更為原始,以後也較少使用。我們不妨猜測,首先使用的烹調方式有可能是燔;後來也許覺得這樣太浪費,操作也不便,才逐漸改進為炙和炮。
今天最常見的蒸和煮,是需要容器的,只能是在發明了製陶以後。我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與此相關的便有叫做「鬲」的有三隻空心腳的鍋,和底部有許多孔眼的甑。進入青銅時代,炊具的形狀由鬲演變為有腳的鼎和無腳的釜、鑊。《史記主父偃傳》說:「丈夫生不食五鼎,則死烹五鼎。」可見鼎是食具,又是炊具,還可以兼作刑具。作為炊具,鼎日常煮的是羹,一種雜煮的濃湯。關於羹 ,司馬遷還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楚漢相爭時,項羽俘虜了劉邦的父親,便要脅劉邦:「你不馬上投降,我就烹了你的父親!」爭天下的人是顧不得父子之親的,劉邦就對項羽耍無賴:「我和你曾經結為弟兄,我的老頭子就是你的老頭子,你要是烹了老頭子,也分給我一杯羹吧!」
東晉開發江東以後,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江南成為魚米之鄉,提供了大量的魚類等水產品和菜蔬,豐富了飲食文化的內容,飲食審美開始轉為崇尚清淡雋永;而此時的北方,長期由遊牧民族的政權統治,飲食以羊肉和乳酪為代表,重在肥膩厚重。北魏孝文帝時由山西大同遷都到洛陽,鼓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改姓漢姓,加強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結果在鮮卑人迅速漢化的同時,北方的一些漢族士大夫也習慣了健啖豪飲,大吃羊肉,大喝乳酪。
發展至兩宋,日常起居方式的變化又引發了飲食方式、烹調技術的重大變革。中國古代是席地而坐,分案而食,這種方式一直保持到唐代;現在的日本,還可以看到這種遺風。《後漢書梁鴻傳》裡,梁鴻隱姓埋名為人打工,每次回到家裡,妻子孟光為他開飯時都不敢仰視,恭恭敬敬地將食案齊眉舉起來。由此留下了「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的佳話。我們看到漢畫像石上的食案和馬王堆出土的漆食案,不過是一種能放下五六個碗的盤子。兩宋時,由外族傳入的胡床演變成為椅子,坐在椅子上當然比坐在地上舒服;人們不再席地而坐,食案便被無情地淘汰了,隨之出現了與椅子相適應的桌子;有了桌子,家人父子不妨圍桌而坐,聚而食之。由分食到會食,飲食方式改變了,烹調技術由適應分食的需要轉變為適應會食的需要,食物的分量、刀工、火候之類都大不相同,必然導致新的突破和發展。烹調技術中最後發明的是炒,大致也起源於宋代。按情理推想,這肯定是由於長期使用鐵鍋的結果,也可能與會食制導致大鍋菜變為了小鍋菜有關。宋人《東京夢華錄》和《夢粱錄》開列的菜單中,前者有炒兔、生炒肺、炒蟹、炒蛤蜊、炒羊;後者有炒鱔、銀魚炒鱔。至此,中國的烹調技術已經大體完備。
中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晚期後,明代出現了幾個講究美食的特殊階層:坐擁巨額田產而又不能過問政事的宗室藩王,雄踞一方、勢焰熏天的鎮守太監,聚斂田產、家奴以千百計的豪紳,揮金如土、附庸風雅的鹽商和徽商。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有錢、有閒、有地位而又對美食有興趣,便不惜重金,雇請名廚,搜羅天下奇珍異味,爭新鬥巧,創造了許多珍饈美味。清代重視水利,專設了東河總督和南河總督。南河歲修經費為白銀四百五十萬兩,有人說只要用到十分之二三,這年就可以不出事,每年可盈餘三百萬兩銀子怎麼辦?除了裝腰包,便是胡吃海喝。清人的《水窗春囈》記載,河工的宴席從早上九十點鐘開始,吃到深更半夜還不罷不休,小碗可以上到百把幾十樣。廚房裡幾十個煤爐子,每個廚師只作一樣菜,別的都不管。如此常年吃喝的經驗積累,便逐漸形成菜系,據說揚菜便由鹽商的家宴發展而來,河工的宴席則分別發展為魯菜和豫菜。
達官貴人們講究美食,豐富了飲食文化的內容,推動了烹調技術創新,總體上是向著精細化的方向發展,選料求精,工序細緻繁複,分工越來越細。但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飲食,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一些名菜尋常人家做不了也吃不起。《紅樓夢》裡的茄鯗,雖是一味茄子,卻是工序複雜、配料名貴的典型,難怪劉姥姥聽了要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多少雞配他!」
精細化走向極端,便是奢侈化。宋代的廚娘,做一份羊頭肉,要用十個羊頭五斤蔥,原來羊頭只剔臉頰上的兩塊肉,蔥只要蔥白裡像韭黃一樣的嫩芯,其他都棄置不用,這已經是暴殄天物了。唐代的李德裕卻每食一杯羹,費錢三萬。據說裡面除了朱砂、雄黃還有珠寶。同時期的元微之,官做到了尚書這一品級,自言「今日俸錢過十萬」,但也只夠李德裕吃三杯羹! 山珍海味都吃膩了,窮奢極欲,便墮入了魔道,「以殘酷取味」。為了吃到美味的烤鵝掌,有的太監把活鵝洗淨放在鐵板上,籠內另放醬油蔥薑等調料一碗,然後在鐵板下加熱。鵝燙得無法立足便不停地行走,由於乾渴便不停地喝調料,最後,「毛盡落,未死而肉已熟矣!」乾隆年間作過巡撫的王亶望,特別喜歡吃炒驢肉絲,據說在廚房裡養了幾頭肥健的驢,要吃驢肉絲了,廚師便拿把快刀,在驢身上肥美之處血淋淋地割下一塊來;為了給驢止血,便拿通紅的烙鐵在傷口上一烙。殘酷至極!
中國飲食文化的現狀如何?有人說在墮落,有人說在衰落。在下沒有研究,不敢妄下斷語。但有一些現象似乎是和尚頭上的蝨子:一是許多原料沒有了,或是變質了。二十年前就聽說,出動一條機動漁船捕撈兩三天,也不一定能遇上一條鰣魚,現在恐怕早已絕跡了。地球上的物種,目前平均每天要滅絕幾十種;之所以造成對自然界的過度索取,無所不吃的饕餮之徒難辭其咎。許多食物由野生變為人工培養,變為工廠化生產,固然是一條出路;如果是靠激素催出來的,不僅味道變了,也有損健康。保護生物,保護環境,實現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共處,也就是保護人類自身。二是公款消費多,流動人口多。決定餐館經營的好壞,烹調質量似乎已經退居為次要因素。三是在一切追求時尚,追求「短平快」的風氣下,一些傳統的工夫菜、火候菜,餐館耗不起那個工夫,有的食客也未必有那個耐心。這後面兩點只是就商業餐飲而言,並非是飲食文化的全部。
雖然許多文人都愛吃、會吃,而且有不少文人善於談吃,但是飲食文化散文並不是好寫的。設想一下,至少要有三個方面的資本:一要見多「食」廣。你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先要嚐一嚐梨子。你沒有嚐過美食,怎麼寫美食?十多年前,汪曾祺先生編過一本《知味集》,廣泛向作家們約稿,結果有好幾篇是談豆腐的。汪先生對此頗生感慨,以為作家大都是寒士,鰣魚、甲魚之類吃不起,只好談談豆腐。二要雜書讀得多。孔老夫子雖是主張「君子遠庖廚」的,殺豬宰羊時只要沒有親眼看到,也就無礙於仁者之心。幾千年來的孔孟弟子們,雖然有不少美食家,卻不大敢違背先師的遺訓,極少有人大張旗鼓地著書立說專門談吃談喝。他們有一些見聞,有一點體會心得,只能是一鱗半爪地夾雜在筆記之類裡,要你到大海裡去撈針。如果有了這兩項資本,最好是還能夠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想談美食也是同樣的道理。做菜是有訣竅的,道聽塗說不行,照著菜譜按圖索驥也不行,必得要繫上圍裙,挽起袖子,舞刀弄鏟,親自操作一番,經歷幾次周折,終於能拿出幾樣看家菜了,才算得是跨進 了知味的門檻。
本書的作者呂永超,此前的半生經歷,似乎都是在為寫這本書作準備。一九九九年前後,他每年發表散文五十多篇,有散文集《靈魂囈語》、《歲月憑證》出版。就寫散文而言,這算得是相當充分的積累了。寫散文出過集子的作家,在一個省裡少說也是數以千計,但要找一個真正在餐飲圈子裡實地摸爬滾打過的,恐怕就不大容易了。永超的獨特優勢就在於他在這個行業曾經一幹就是十三年。他又是一個有心人,幹一行,愛一行,鑽一行,走南闖北,開會、學習、觀摩之際,走訪了一家家馳名全國的老字號,品嚐了形形色色的地方名品,搜羅了一冊冊菜譜書刊,記下了一本本學習筆記。僅僅是一味餛飩,他就光顧過上海的「雨林苑」、「金師傅」、北京的「餛飩侯」,品嚐過蘇州的綠揚雞絲餛飩、黃山的豆腐餛飩……與此同時,他又潛心學藝,頗得本地名師的真傳,不但宮保雞丁、清蒸武昌魚之類做得有滋有味,而且興致來了,還能自出機杼,新創兩味小菜。
永超在這本書中,談起春捲、粽子、年糕、臘八粥之類的源流演變,或徵引古籍,或講述民間傳說,旁徵博引;同是一味宮保雞丁,他將魯菜、川菜、黔菜的不同特色,香辣、糊辣、麻辣的微妙區別,條分縷析,細緻入微;小小一個燒餅,他一口氣列舉了北京的芝麻醬燒餅、天津的爐乾燒餅、唐山的棋子燒餅、商丘的空心燒餅、山東的周村燒餅、蘇北的黃橋燒餅、銅陵的太平街燒餅等一二十種,南北風味,各有不同,見多識廣,如數家珍;他愛吃魚,清蒸(魚扁)魚、松鼠鱖魚、五柳魚,如何選魚、如何用刀、如何配料、如何烹製,一一娓娓道來,儼然是一位行家。這些內容,都大大豐富了本書的知識性、趣味性,也大大增強了它的可讀性。但是,永超並不僅僅止步於此,他更突出了文化散文的特色,將作者的主觀情感充分地融入了寫作的對象。
這本《舌尖上的美味》共分五輯,曰節令佳品、日常菜蔬、平民小吃、特色風味、吃之境界。主要談的是平民飲食,大眾風味。此類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飲食,不同於皇宮御宴、豪門盛宴、乃至八大菜系中的一些名菜,大概可以分別視為中華飲食文化中兩個截然不同的分支。從表層來看,一個是原料務求珍稀名貴,另一個卻是普普通通;一個是極其豪華奢靡,另一個卻是簡易樸實。從深層次來看,一個重的是物質和技藝,另一個卻蘊藏著前者所缺乏的濃郁的人情味。賈寶玉那位才選鳳藻宮的大姐賈元春,在歸省時頗為悲涼地傾訴道:「田舍之家,雖虀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之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永超這本書的主要特色,我以為就是將平民飲食中的人情味和散文的感情色彩很好地結合起來了,善於捕捉、體驗和表現「虀鹽布帛」中的天倫之樂,那種蘊藏在平常飲食生活中的美和意趣。
品嚐美食,不僅僅是滿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種精神享受。不僅要調動視覺、嗅覺、味覺這些感官,還要調動大腦皮層中的積累,展開思維的翅膀,引起回憶和類比、想像和聯想,甚至將感受昇華為一種意境。在永超的眼中,那形如偃月的餛飩,「偃月為半月,彎彎的一角新月芽,不是殘,是追求盈圓」;黃州燒賣「下部如石榴,上部似梅花,形態豔麗,油潤香甜,亦叫石榴梅」;湯包則是「每道褶彷彿一片菊瓣,每只包子都如一朵即將開放的白菊,而湯包中間小圓孔中露出的蟹黃又有如菊花的花蕊。」在富有詩意的感受中,這些小吃就是美的結晶,美的化身。在永超的眼中,「釀酒的日子到了,老家的女人們一個個神聖美麗起來,」她們的衣著是美的,笑靨是美的,動作是美的,整個釀酒的過程是創造美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本身也是美的;飲了老家的米酒後,永超更進入了一個美的境界:「在微醉中,高低錯落的村落農舍,煙雨籠罩的青瓦灰牆,楊柳依依的小河拱橋……絲絲縷縷,密密實實,纏成心頭綿延悠遠的記憶。」
書中發掘和體驗平民飲食中的人情美,不僅表現在闡釋了各種節令食品中,古往今來人們寄託的所思所想、所求所願;也不僅表現在捕捉到了許多地方風味與民間傳說的獨特組合:興國魚絲裡傳遞著妻子對丈夫的思念,蝴蝶魚裡蘊含著賢德嫂子對小兄弟的一片真情,而油炸燴則永遠地附著了人們對權奸秦檜誤國的憤慨;更表現為作家自身對一些平常食物內在意趣的獨特感悟:由孵豆芽的一個孵字,「聯想到雞蛋在母雞溫暖的翅膀下,漸漸變為雛雞的美妙過程,那是偉大母愛對綿延不息的生命的守望。」由米酒若有若無的淡淡酒味,感悟到「米酒最實用的是給人快樂,而不是給人享樂。」在談粥時,他寫道:「有時,一碗粥不過是父母念念不忘的關切,不過是子女拳拳的赤子之心,不過是君子之交的平和內斂,亦不過是夫妻之間的相濡以沫。」
其實,飲食中蘊含的親情、友情又豈止在粥中!在他的筆下,兒時冬天的清晨,奶奶煮一碗湯圓送堂兄去參軍;一家人圍著小泥爐吃著父親燉的豆腐;遠在家鄉的母親包的粽子、煮的臘八粥;經過長期感情的發酵,都已經定格為永恆的美好的回憶,昇華為一種無法代替的精神慰藉。你和我又何嘗沒有類似的經歷?何嘗沒有類似的回憶?讀到這些地方,內心的琴弦會被他輕輕地撥動,不由自主地產生了親切的共鳴。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讀永超的書稿時,正是初春時節,薺菜肥美,不由得食指大動,一再敦促老妻,終於買來了春捲,大快朵頤一番。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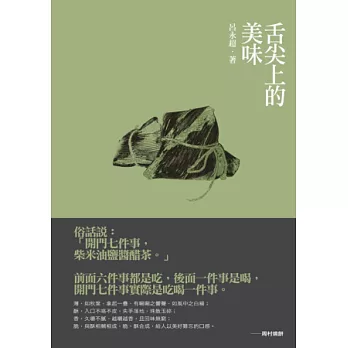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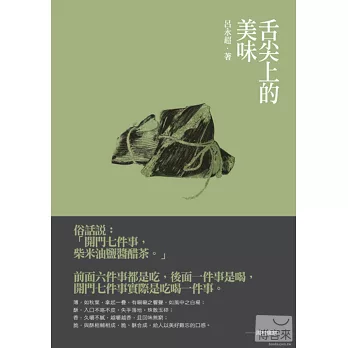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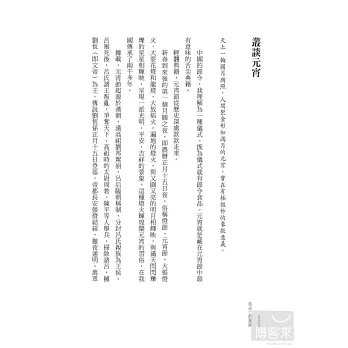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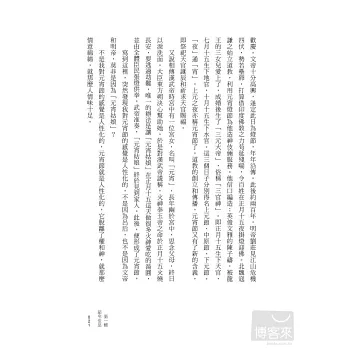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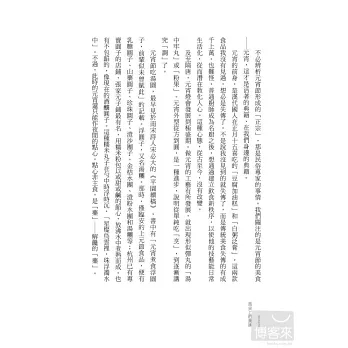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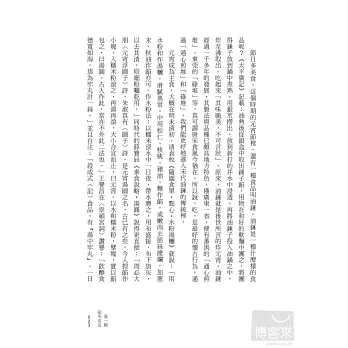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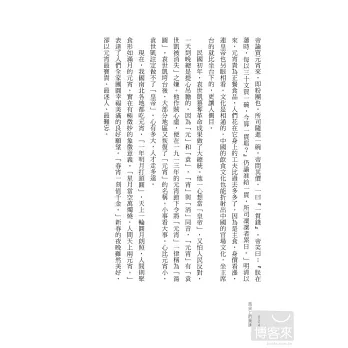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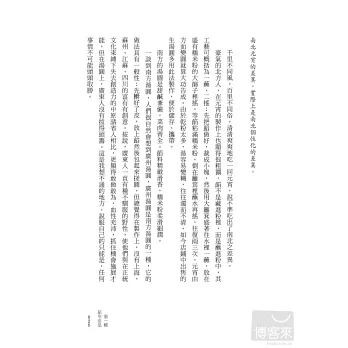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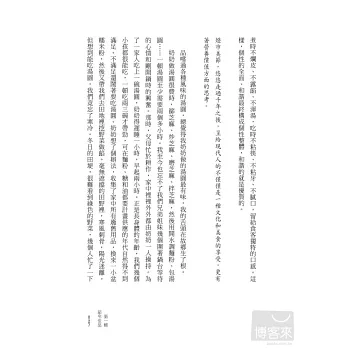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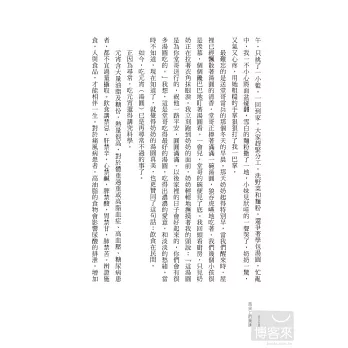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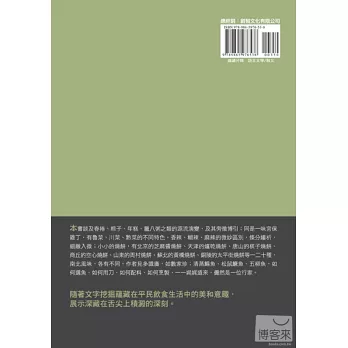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