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二十五年前,當我開始在巴勒斯坦的山中漫步時,我並沒有意識到我是在穿越一片正在消失的風景。幾百年來,巴勒斯坦中心的高地山丘相對完好地保持著地理原貌,它的一側向遠方傾斜,連接大海,另一側延伸到沙漠。我在拉馬拉(Ramallah)長大,運用一點想像力可知,我的城市到北部納布盧斯(Nablus)的土地看起來和耶穌基督的時代很類似。我相信,那些山是世界天然的寶藏之一。
我的一生都住在可以遠眺拉馬拉山的房子裡。我把它們當做自己的私人後院,無論是供我漫步、野餐或者採花。我曾經觀察它們在一日和四季中的色彩變化,無止盡的戰爭時期也是如此。我一直喜歡在山中漫步,不論是在巴勒斯坦還是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或者蘇格蘭高地和邊遠的島嶼,在那裡漫步你可以享受到純粹的快樂,而不用擔心煩擾,不用分心去考慮即將到來的政治和自然災害。
1970年代末,我開始了我的漫長步行。那時,許多讓土地遭受摧殘並留下陰影的、不可挽回的改變還沒有發生。當時的山林就像龐大的自然保護區,有原始的美麗和該地區特有的自由。本書所描述的七次漫步歷時二十七年。雖然每次路線不同,但是都穿越了時間和空間。這是一場於1978年開始,2007年結束的旅程,期間我寫到我所目睹的該地區的發展,我的生活和環境的變化。我描述了我在拉馬拉周圍的山間漫步,穿過耶路撒冷荒野乾涸的河床以及死海邊風景絢麗的溝壑的經過。
長久以來,巴勒斯坦一向是朝聖者和遊客最常到訪的國家之一。我所讀到的描述並未寫出我熟悉的土地,而是這些遊客們的想像。巴勒斯坦被不斷地再創造,給原本的居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不論是地質學家繪製的地圖,還是遊客在廣泛的旅遊文學中的描寫,重要的不是土地和居民本來的樣子,而是確認觀察者或讀者的宗教或政治信仰。我只希望我的書不會落入這個傳統。
也許巴勒斯坦受的詛咒就在於它是西方歷史和《聖經》想像的中心。因此,這片土地要被裁剪成符合嚴峻事件所記載的樣子。薩克雷(Thackeray)就是這樣描寫我所熱愛的山岡的:
焦灼的山,陰鬱黯淡的橄欖樹四處瑟瑟戰抖,荒涼的溪谷和溝壑覆蓋著墳塚——整個城市彌漫著無法形容的恐怖和悲愴,滿眼蕭颯悽楚。這地方很適合希伯來歷史故事中記載的事件,對我而言,它們和恐怖永遠不能分開。恐懼與血腥、罪惡與懲罰,一頁一頁連篇累牘。你所見之處沒有絲毫痕跡,但某些暴力行為已在此發生:屠殺被犯下、受害者遭到殺害、偶像被以鮮血和恐怖的儀式膜拜。(《從康希爾到大開羅之旅札記》)
仿佛遊客們經過艱辛的旅程來到巴勒斯坦,卻沒有找到他們所追求的、存在於他們想像中的土地,於是他們強烈地厭惡起真正的所見所聞。馬克.吐溫寫道:「巴勒斯坦披麻蒙灰……巴勒斯坦荒蕪醜陋……巴勒斯坦不再屬於當今世界。它對詩歌和傳統來說是神聖的——它是一個夢中之境。」(《傻子旅行》)
西方世界和巴勒斯坦的對抗也許是有史以來上演的最久的戲劇。這不是我的戲劇,雖然我覺得我是裡面的一個小角色。我想思考我和這片土地的聯繫,我始終在這裡生活著,直接去看它,而不是透過寫及它的文字的面紗,那些文字通常都充斥著曲解和變形。
然而正是在此無可避免的文學脈絡中,我寫下了我自己對於土地,以及玷污了它的「恐懼與鮮血、罪與罰」的當代文化的想法。也許很多人會在這本書上讀到不同於他們的電視螢幕上殘酷影像的背景的東西。他們在閱讀七次漫步中美麗的鄉間風光時可能會經歷不和諧的片刻:無始無終地充滿衝突鬥爭和流血犧牲的土地真的能夠如此平和寧靜嗎?不過我仍然希望讀者把這些全都放在一邊,以開放的心態去接近它,我希望說服讀者,儘管過去的二十幾年裡它飽受摧殘,巴勒斯坦這個國度卻依然這麼的輝煌和壯觀。
長篇戲劇還沒落幕。舞臺已經更換為約旦河西岸的山岡,以色列規劃者把猶太人聚居區安排在山頂,讓他們只能望見其他的居民區,並同時策略性地主宰著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村落所在的山谷。發現路標上的阿拉伯村名被過於活躍的居民塗黑也沒什麼奇怪的。
為了伊曼紐爾(Emanuel)的約旦河西岸極端正統派的聚居區,而在布魯克林出版的成員招募宣傳冊,呼喚著如畫的風景:「伊曼紐爾的城市,位於海平面四百四十米以上,有美麗的海濱平原和猶太山脈的景色。綠色橄欖園點綴山景,充滿田園風光的靜謐。」再造出聖經般的如畫的風景,成了對這片土地擁有古老權利的證明。
在評論這樣的廣告時,以色列建築師拉非.塞格爾(Rafi Segal)和伊亞.維茲曼(Eyal Weizman)敏銳地發現了「殘酷的悖論」:使風景成為「聖經式的」東西的正是傳統聚落和耕作的梯田、橄欖園、石頭建築和家畜,這一切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創造,卻被猶太人接管了。種植綠色橄欖園並使土地成為聖經式的人們卻被排除在全景攝影以外。巴勒斯坦人創造了風景,然後就消失了。
土地被認為是「無人之地」,這樣,以色列的猶太人市民就可以佔用了,從此他們不再能宣稱自己是「無地之人」。
以色列開發協會指示它的研究者,要他們提供「從約書亞到我們這一代的內蓋夫統治者的持續的歷史線索的具體文獻」。要達到這個目標,介於其間的年代和當地居民的世代必須被刪除和否定。在這個進程中,我和我的民族的歷史遭到了扭曲。
這樣的態度正好符合西方旅行者和殖民者的古老傳統,他們根本就不理會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偶爾注意到也是帶著偏見和嘲笑,僅僅當做來自他們想像國度的消遣。所以,薩克雷曾經這樣描寫耶路撒冷城外一個無名的阿拉伯村莊:「一個海狸的村莊,或者螞蟻的群落,使得居住條件和那些堆積在平原上的陰暗小棚屋沒什麼兩樣……」(《從康希爾到大開羅之旅札記》)
我是作家也是律師。自1980年代初就從法律角度描述有關的土地紛爭,呼籲反抗以色列將巴勒斯坦土地開發成猶太聚居區。現在我要敘述這些案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我還描寫了這麼多年我為之獻身的土地,其法律爭端造成的黯然後果。同時挖掘出這被分割的土地的神秘和我對它的不確定未來的擔憂。
自從聽說歷屆支持在佔領殖民區建立聚居區的,以色列政府所籌畫的對我們山地的改造計畫,我就像一個被告知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如今,當我漫步山間時忍不住會想,我能這樣漫步的時間已然不多。也許折磨群山的這些惡性腫瘤增強了我對漫步經歷的感受,讓我不能視其為理所當然。
1925年,巴勒斯坦歷史學家達文斯.米喀蒂(Darweesh Mikdadi),帶著耶路撒冷公立高中的學生遠足,通過巴勒斯坦多岩石的風景,一路走向敘利亞青蔥的平原和豐饒的山谷,然後穿過黎巴嫩的小溪、河流和岩洞。學生們沿途參觀了著名的、幾個世紀前留下的戰爭遺址,受到慷慨村民的熱情款待。1948年戰鬥繼續時,這樣的旅程就不再可能了。
1980年代,巴勒斯坦地理學家卡瑪.阿卜杜.法塔(Kamal Abdul Fattah),帶領比爾澤特大學的學生,穿過歷史悠久的巴勒斯坦,進行地理考察。有一年我加入了他們,我們共同度過了令人興奮的三天,從最為富饒的北部到貧瘠的南方,觀察地形、熟悉地質變遷及地理、歷史與當地居民生活方式的關係。這次旅行對我來說可謂大開眼界。但自1991年以來,約旦河西岸和以色列之間的活動受到限制,這樣的旅行也不再可能。
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禁止進入加薩走廊。一個拉馬拉商人發現去中國進口籐椅比去迦薩還要容易些,僅僅四十分鐘的車程,籐椅製作在那裡曾經是很興盛的行業,現在卻到處堆棄、滿是灰塵。我所寫的80年代初發佈的主要居民計畫已經按部就班地執行,為巴勒斯坦人規劃四散的飛地。非人道的計畫帶來了隔離牆(Separation Wall),設計不是沿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邊境,而是包圍「聚居區」,把它與以色列合併,像用匕首一樣將巴勒斯坦的土地刺穿。所有這些開發的結果是,即便是短距離的教育旅行都遭到限制,學生只能在他們自己的檢查區內,重複探訪那些令人絕望的地點。。巴勒斯坦飛地越來越像貧民窟。很多村民只能在有同情心的以色列人和國際團結組織的保護下從自己的橄欖樹上採摘橄欖。2005年選舉日,一個賣甜食的人告訴我說他不想參加投票。「我已經有五年不能離開拉馬拉了,為什麼要我參加?這些選舉能帶來什麼改變?」隨著巴勒斯坦世界的縮小,以色列的地盤在擴大,更多的聚居區被建立起來,永遠地破壞了溪流和山峰、削平了山脈、改造了寶貴的土地,而很多巴勒斯坦人將永遠無從知悉。
僅僅三十年,就有近五十萬猶太人在5900平方公里的地區定居下來。維持這麼多人口所必須的基礎建設造成對土地的損害,大量的混凝土被傾倒在幾百年來一直保持原貌的山地上,建立整座整座的城市,這不能不引起注意。我目睹到靠近我長大的地方已被全面改造,而我就在此地描寫它。美麗的溪流、泉水、山崖和古老的廢墟都被摧毀了,被那些自稱對這片土地無比熱愛的人們。通過努力記錄這片土地在經歷災難之前的感覺和樣子,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夠用我的文字,保存永遠失去的一切。
在巴勒斯坦,所有溪流、泉水、小丘、陡坡和懸崖都有名字,通常都有特殊的意義。一些是阿拉伯語,一些是迦南語或亞拉姆語,證明這片土地是多麼古老,千百年來它是如何被不斷地居住和佔領。我以前全然不知道它們的名字。和我一樣的人很多。現在幾乎沒有什麼人在山間漫步,瞭解這類地方歷史知識的人少而又少。經過地理學家卡瑪.阿卜杜.法塔和他的學生的協助,他們採訪了很多仍能記得的老人,一些長久被人們遺忘的名字重生了。
經常,在漫步回來的路上,當黃昏的微光降臨,沿途的石頭在朦朧中變形,我開始看到某些石頭上的輪廓和形狀,就把它們搜集起來帶回家。我盡自己的力氣拼命地多撿,但是一回到家通常就丟棄一邊。我的公寓無情的燈光讓它們的魔力消退。其中只有一塊,我保存了很久。灰白的石頭仿佛人面,一條裂縫如張開的嘴,在驚恐中哀號。也許這塊石頭適合保留下來,連同折磨這些山的東西。
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意識到寫作本身就是第八次旅行。我不知道在這趟獨特的探索中要前往的方向,也不知道它將如何結束。寫著寫著,我才注意到,我有時對於自己過於簡化、片面地批評那些十九世紀旅行者而感內疚。整本書中,殖民者,即故事中主要的壞人形象,不斷出現。我蔑視他們對我的土地和居民侵略性的意圖和行為,但是我很少正視他們。他們被化約,就像十九世紀的旅行者把當地的「阿拉伯人」籠統化一樣,因為想把他們從他們希望描述的土地上刪去。不同的時刻,我從遠處觀察著聚居者們。擔心他們的行為,揣測他們的想法。問自己,他們究竟有沒有看到我和我的人民。
第七次旅行,我們遭遇了一個年輕的猶太人聚居者,他在同樣的山上長大並生活了二十五年。我知道他對世界的大部分認識是基於謊言。他也許是在專屬於他的人民的國度裡那種典型的虛構事實中長大的,儘管那個地方就在拉馬拉附近。不會有人告訴他,那土地是從幾公里外的巴勒斯坦人那裡剝奪來的。但是,不管構成他的世界觀的神話如何,我怎麼能說我對這些山的愛就能抵償他所付出的愛呢?這種認知對我們和我們尊敬的國家的未來又意味著什麼?
隨著拉馬拉聚居區附近這次不可避免的遭遇,本書的寫作,即我的第八次旅行,也在雜亂不安中結尾了。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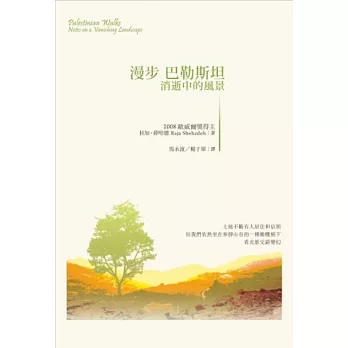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