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這本書中的感想和看法,是沒有什麼次序的,而且差不多是不連貫的,它開始是為了使一位善於思考的賢良的母親*看了高興而寫的。最初,我的計畫只是寫一篇短文,但是我所論述的問題卻不由我不一直寫下去,所以在不知不覺中這篇論文就變成了一本書,當然,就內容來說,這本書的分量是太大了,然而就它論述的事情來說,還是太小了。要不要把這本書刊行發表,我是考慮了很久的;而且在寫作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雖然是寫過幾本小冊子,但畢竟還是說不上懂得著書。我原來想把這本書寫得好一點,但幾次努力也未見成效,不過,經過這一番努力之後,我認為,為了使大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我應當照現在這個樣子把它發表出來;而且,即使說我的見解不好,但如果能拋磚引玉,使其他的人產生良好的看法,我的時間也就沒有完全白費。一個深居簡出的人,把他的文章公之於世,既沒有人替它吹噓,也沒有人替它辯護,甚至不知道別人對他的文章想些什麼,或者說些什麼,那麼,即使說他的見解錯了的話,他也不用擔心別人不假思考就會接受他的錯誤的。
我不想多說良好的教育是多麼重要,我也並不力圖證明我們常用的教育方法不好,因為這種工作已經有許多人先我而做了,我絕不喜歡拿那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填塞我這本書。我只想說明:很早以來就有人在大聲反對這種舊有的教育方法了,可是從來沒有人準備提出一套更好的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和科學,傾向于破壞的成分多,傾向于建設的成分少。人們可以用師長的口吻提出非難;至於說到建議,那就需要採用另外一種口氣了,然而這種口氣,高傲的哲學家是不太喜歡的。儘管有許多的人著書立說,其目的,據說,完全是為了有益人群,然而在所有一切有益人類的事業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業,卻被人忽視了。我闡述的這個問題,在洛克洛克(1632—1704),英國哲學家。盧梭在這裡所指的是洛克於1693年發表的《教育漫話》。在兒童和青年的教育問題上,盧梭在《愛彌兒》中幾次表明他是不贊同洛克的觀點和方法的;特別是在第5卷的開頭,盧梭更是直截了當地說:“至於我,我可沒有培養什麼紳士的榮幸,所以,我在這方面絕不學洛克的樣子。”的著作問世之後,一直沒有人談論過,我非常擔心,在我這本書發表以後,它仍然是那個樣子。
我們對兒童是一點也不理解的:對他們的觀念錯了,所以愈走就愈入歧途。最明智的人致力於研究成年人應該知道些什麼,可是卻不考慮孩子們按其能力可以學到些什麼,他們總是把小孩子當大人看待,而不想一想他還沒有成人哩。我所鑽研的就是這種問題,其目的在於:即使說我提出的方法是很荒謬的,人們還可以從我的見解中得到好處。至於說應該怎樣做,也許我的看法是很不對頭,然而我相信,我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出人們應該著手解決的問題了。因此,就從你們的學生開始好好地研究一番吧;因為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你對他們是完全不瞭解的:如果你抱著這種看法來讀這本書,那麼,我不相信它對你沒有用處。
至於人們稱之為做法的那一部分,它在這裡不是別的東西,只是自然的進行而已,正是在這裡最容易使讀者走入歧途;毫無疑問,也就是在這裡,人們將來會攻擊我,而且,也許就是人們批評得不錯的地方。人們將來會認為,他們所閱讀的,不是一種教育論文,而是一個空想家對教育的幻想。
有什麼辦法呢?我要敘述的,不是別人的思想,而是我自己的思想。我和別人的看法毫不相同;很久以來,人們就指摘我這一點。
難道要我採取別人的看法,受別人的思想影響嗎?
不行。只能要求我不要固執己見,不要以為唯有我這個人比其他的人都明智;可以要求於我的,不是改變我的意見,而是敢於懷疑我的意見:我能夠做的就是這些,而我已經是做了。
如果有時候我採用了斷然的語氣,那絕不是為了要強使讀者接受我的見解,而是要向讀者闡述我是怎樣想的。我為什麼要用懷疑的方式提出在我看來一點也不懷疑的事情呢?我要確切地說出我心中是怎樣想的。
在毫無顧慮地陳述我的意見的時候,我當然瞭解到絕不能以我的意見作為權威,所以我總連帶地說明了我的理由,好讓別人去加以衡量,並且評判我這個人:儘管我不願意固執地維護我的見解,然而我並不認為就不應當把它們發表出來;因為在這些原則上,儘管我的意見同別人的意見相反,然而它們絕不是一些無可無不可的原則。它們是我們必須瞭解其真偽的原則,是給人類為福還是為禍的原則。
“提出可行的辦法”,人們一再地對我這樣說。同樣,人們也對我說,要實行大家所實行的辦法;或者,最低限度要使好的辦法同現有的壞辦法結合起來。在有些事情上,這樣一種想法比我的想法還荒唐得多,因為這樣一結合,好的就變壞了,而壞的也不能好起來。
我寧可完全按照舊有的辦法,而不願意把好辦法只採用一半,因為這樣,在人的身上矛盾就可能要少一些:他不能一下子達到兩個相反的目標。做父母的人啊,可行的辦法,就是你們喜歡採用的辦法。我應不應該表明你們的這種意願呢?
對於任何計畫,都有兩種事情要考慮:第一,計畫要絕對的好;第二,實行起來要容易。
關於第一點,為了要使計畫本身能夠為人們所接受和實行,只要它具有的好處符合事物的性質就行了;在這裡,舉個例來說,我們所提出的教育方法,只要它適合於人,並且很適應於人的心就行了。
至於第二點,那就要看一些情況中的一定的關係如何而定了;這些關係,對事物來說是偶然的,因此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可以千變萬化的。某種教育在瑞士可以實行,而在法國卻不能實行;這種教育適用於有產階級,那種教育則適用于貴族。至於實行起來容易還是不容易,那要以許多的情況為轉移,這一點,只有看那個方法是個別地用之於這個或那個國家,用之於這種或那種情況,才能斷定它的結果。
不過,所有這些個別的應用問題,對我論述的題目來說,並不重要,所以沒有列入我的計畫的範圍。
別人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可以去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每一個人可以研究他心中想研究的國家或者想研究的情況。對我來說,只要做到下面一點就算是滿足了,那就是,不管人們出生在什麼地方,都能採用我提出的方法,而且,只要能把他們培養成我所想像的人,那就算是對他們自己和別人都做了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履行這個諾言,那無疑是我的錯誤,但是,如果我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人們再對我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話,那就是他們的錯誤了;因為我所許諾的只是這一點。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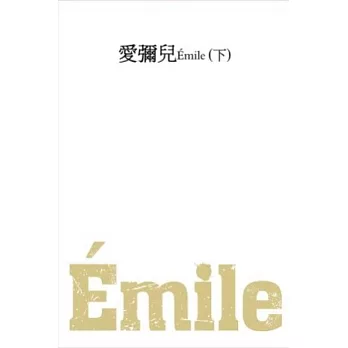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