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本書《異地繁花:海外臺灣文論選譯》是教育部「海外臺灣文論中譯計畫」的成果,分為上下兩冊出版。上冊以綜合性的文論為主要的選譯對象,所以書中冶各種文類的評論於一爐。下冊則把重點一分為二:首先是新詩的評論,其次仍為詩歌以外的各種文類的研究。臺灣文學浩浩蕩蕩,文評家秉筆論之,向來以小說的評論居多。臺灣或中國文學的固有傳統中,詩話詞話一向以壓倒性的態勢賽過金聖歎與李卓吾等人立下的說部傳統。如今文學史早已改寫,小說的評論後來居上,硬把昔日大眾的詩歌壓成了小眾。2008年開始本計畫,我就想逆轉情勢,讓詩話重現往昔的雄風。此時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教授適才編成《現代中文詩新論》(New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一書,我遂趁他來中研院之便,與他商量,取得版權,然後矻矻專心,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帶領整個中譯團隊譯出了《現代中文詩新論》中有關臺灣詩論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共有五篇文章,領頭的乃是陸敬思的鴻文。陸敬思教授自康乃爾大學學成,在美國上庠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本有機會層樓更上,至芝加哥大學接任苪效衛(David T. Roy)教授的職缺,不過後來長駐華盛頓州立大學作育英才。陸敬思一生不曾和臺灣文學須臾離,但他也治詩,則是我始料未及。本書所選的第一篇文章討論的是鄭愁予,題為〈尋找當代中國抒情詩的聲音:鄭愁予詩論〉。無可置疑,鄭愁予始終都以抒情詩貫串其詩人生涯,「達達的馬蹄」帶來的是詩人自己,也是詩中的敘述者內在的思緒或愁緒。陸敬思除了指出鄭詩清亮的音樂特質外,也因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重詮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而得到啟發,認定「他的詩象徵資本主義邁入了新紀元,因而可作為雄渾(sublime)概念的新定義看」。從詹明信揭櫫的新美學下手重讀鄭愁予的詩,使鄭愁予由美學及隱遁的抒情者和歷史連結在一起,詩中透露出一股論者罕察的時局與歷史的動盪之感。
鄭愁予的父親是國民黨時代的高階將領,不過做兒子的卻稱不上早期臺灣文壇所謂「軍中詩人」。在1950、1960年代,適合貼上這張標籤者大有人在,若提起饒博榮(Steven L. Riep)教授在本書論及的□弦,我想反對者一定不多。饒博榮出身洛杉磯加州大學,現任猶他州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中文教席,在臺灣現代文學的研究方面下過不少功夫。他在〈蕎麥田之景:論□弦詩歌裡的戰爭〉裡獨排眾議,所論不僅是□弦提筆寫詩時未曾得見的巴黎或芝加哥,而且觸及□弦詩論者少有人提的戰爭意象。十來歲上,□弦在河南老家被人拉夫充軍,自此變成一位幾無實戰經驗的職業軍人。身為海軍,□弦來臺灣後駐紮左營,開創了其後稱為「創世紀」的詩派。洛夫、商禽、張默、辛鬱、楚戈與管管紛紛來歸,都是此派詩人的佼佼者,共同啟動了臺灣軍中詩人全盛的年代。對□弦而言,戰爭的歷史、社會與其他文化意義恐怕勝過一切。他關懷的是史上飽嚐戰禍的都市,是連年兵燹帶來的社會蕭條與人心窳敗。1950、1960年代,國府全面備戰與宵禁戒嚴等,也是他詩中難以忽略的戰爭問題。饒博榮的研究顯示「□弦寫於1957到1962年的反戰作品」,於時局根本就是批評:他既不滿國民政府,對社會上的主戰跟風就不無異議。□弦反戰,也反共。他主持《聯合報》副刊編政的1970年代,可能是他最不見容於臺灣本土派與左派的一段時間,如果沒有饒博榮就□弦與戰爭的關係提出分析,我們對此時的他,了解可能片面不全。
洛夫同樣出身軍中,曾戍守臺灣最前線的金門,但詩裡反而不易嗅到砲火與煙硝。以《石室之死亡》為例,即使寫戰爭,寫國家民族的遭遇,洛夫也「呈現出極具個人觀點與興趣的史觀」。陶忘機(John Balcom)教授在〈通往離鄉背井之心:洛夫的詩歌漂泊〉一文中,因此強調中國與人類歷史的整體對洛夫的威脅,強調「歷史」這一「殘暴的展覽」有其令洛夫不得不駐足參觀的力量,也強調洛夫雖身處臺灣卻有其鄉愁,充滿了疏離(alienation)與離散(diaspora),甚至是荒謬之感。陶忘機於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於蒙特利國際研究學院教授翻譯。他對詩人特有的感性相當熟悉,這也強化了他閱讀《石室之死亡》等洛夫名詩的感受力。洛夫有一句話,頗能講出自己面對歷史的無奈,陶忘機在其文中亦引得好:「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
1980年代以前,國府的中原心態與相關的政治舉措,造成了洛夫,甚至是□弦與鄭愁予在臺灣的疏離感,而且在離散後還繼續以離散終其後臺灣時代。他們是臺灣的代表性詩人,傳唱的卻是十分不確定的臺灣之歌。是以在臺灣,現代詩人的「確定感」反而得見諸女性詩人。回首傳統,父權的聲音只能造就矯情的女「聲」,抒情婉約變成了陰性書寫應有的特質。然而在傳統的男性霸權之後,我們終於得見夏宇這位真正的女性主義女詩人。凌靜怡(Andrea Lingenfelter)教授的〈翟永明與夏宇詩中的對立與改寫〉慧眼獨具,把夏宇和中國四川的女詩人翟永明並置而論:不論是文革時代或國府治下的詩人,都能完全切斷自己和文化傳統的關係,而翟永明與夏宇各自便以她們獨特的聲音再現文化傳統。她們批判過去的婚姻制度,抗議男性霸權對女性情慾的壓抑,也書寫自己性別下的宇宙觀。女媧伏羲開天闢地或姜嫄肇建民族的神話經過重寫,在她們的詩中一一回復其有情本質,詩人也因此建立了一個「得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凌靜怡教授本身既是翻譯家,也是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博士,更是一位傑出的女詩人,由她來論述夏宇和翟永明,我想再合適也不過。
我另外也選了一篇文章,專論劉克襄和自然書寫,即柯德席(Nick Kaldis)教授的〈大自然的守護者:劉克襄自然寫作(中)的「焦慮反射」〉。柯德席是紐約州立大學賓罕頓(Binghamton)分校教授,翻譯過無數劉克襄的詩文,他對梭羅以降的美國自然書寫傳統研究獨到,認為詩人作家早已形成某種焦慮,一心想要護持一個乾淨而健康的地球。臺灣的生態危機之險惡,比起西方國家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克襄就在這種狀態下崛起,唱出我們這個時代比任何議題都要重要的詩歌。而且也因為劉克襄的關心,自然書寫這個概念所導出的詩文日受重視。且不談廖鴻基和陳黎等海洋與山林的謳歌者,連簡媜等傳統散文作家也開始正視日益嚴重的環保議題。人類三千年的父權思想迫生了女性主義,人類三千年的濫墾開發,也催發了自然書寫。因為父權與環境問題都非朝夕之寒,拔除不易,我們有理由相信新興的自然書寫風潮還會持續有年。人類如果不思改過,那麼自然書寫恐怕更會世代不滅,變成永久性的文學研究現象。劉克襄的自然詩不是無病呻吟或理論空談,而是護衛臺灣自然生態的先聲。
臺灣現代詩人的專論是本書的特色,不過我也不敢偏廢其他時代或文類的研究,包括某些後現代議題。以日人領臺期間為例,本書便收入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有關西川滿的一篇專論。西川滿當然是日本人,然而他活躍在臺灣的日治時代,一生幾乎都在為臺灣文學奮鬥,我覺得他當然也是臺灣文學史的一部分。《文藝臺灣》領導臺灣早期的浪漫主義,殖民色彩與政治性不低,近年來常為人詬病。雖然如此,執教於科羅拉多大學的阮斐娜教授卻提醒我們:西川滿挖掘民俗臺灣,引進法國文學的貢獻可觀,而「《文藝臺灣》的後期階段正值太平洋戰爭戰況激烈」,這本刊物迫於時勢,實在是不得不跟著宣傳「皇民文學」,其情可憫。楊逵反日,此時同樣高唱「八紘為宇」,何況西川滿是日本人,他的「東方凝視」本來就「投向他的日本祖國」。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學者日益增加,阮斐娜出身臺灣,中英日文俱佳,其結論特別值得研究者重視。
清末以來的臺灣現代文學,淺見以為成就最大的是小說。就國府時代言之,現代主義濫觴於1950年代末,大盛於1960年代。在本書裡,我們中譯了陸敬思與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兩篇論及1960年代小說的文章。陸文處理王文興的《家變》,何文則是黃春明與大江健三郎的比較。陸文題為〈王文興及中國的「失去」〉,把《家變》視為詹明信所重視的「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這個「國家」不只是國府的「中國」,也包含外交及意識形態上均「失去了中國」的美國。易言之,陸敬思從《家變》的字裡行間讀到了「冷戰時代的最後一役」,認為王文興此一名著意義多重(multivocalities)。何依霖教授研究中日文學,曾經擔任過劍橋、牛津與倫敦大學的教席。她認為在呈現東亞的美國霸權問題上,黃春明和大江健三郎有異曲同工之妙。何依霖堅信以往東西並比的批評模式應該退讓。在文學研究方面,東亞國家本身的通性才值得我們深思,因為在此一區域內的國家歷史,其遭遇相去不遠。小說家──不論黃春明或大江健三郎──所寫,其實又都是國家寓言。
關於1960年代臺灣小說的研究,德州大學張誦聖教授的成就有目共睹,本書選入張教授的力作〈高層文化理想與主流小說的轉變〉,研究的時間重點則轉到了1970年之後。這個時間點距今未遠,張文提到的袁瓊瓊、蘇偉貞、蕭颯、蕭麗紅、張大春與朱天文、朱天心姊妹,迄今猶活躍文壇,而他∕她們的共同特色是幾乎都出身副刊,乃文學獎拱出來的時代寫手。為此,張誦聖特別由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學場域論展開分析,洞見頻頻。這個時代的另一特色,是小說界才女特多,致令張教授以傳統的「閨秀文學」稱之。今天的「閨秀」,當然不是中國或臺灣傳統的「女子無才便是德」那一類人物。相反的,她們才德兼備,歷代罕見。她們在小說創作上的才華洋溢,歷代則根本未見。張誦聖注意到1980年代臺灣不僅發展出了菁英文化,也形成了以張愛玲的小說為中心的大眾文學。此刻的文學現象,張誦聖觀察尤精,例如張大春日益大眾化;朱家姊妹反求諸己,往內心尋找寫作的資源;李昂則逐步外露,要從內在拔除中國的鬼魅,完全向臺灣認同。張誦聖觀察最入微者,我以為是「中原心態」的逐步瓦解。因為就在張大春與朱天心猶承繼父輩的鄉愁之際,文學上某種「臺灣意識」早已悄然形成,沛然難禦了。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後,上述政治態勢在文學界變得更加明顯,即使兩岸開放交流,一邊一國的認知似乎也愈益強化。為深入了解文學界這股新興的「國家運動」,我特將張誦聖教授的〈解嚴後臺灣文學場域的新發展〉一併收入本書。臺灣解嚴之後,文化上獲得從「日本」到「國府」時代從未有過的政治自由,各種思想百花齊放,有如戰國時代或民國初期。甭說「中原心態」,連「中國中心論」都廣受質疑,而戒嚴時期的主導文化及文學場域裡對應的主流位置自然勢移時易,「嚴重受損」了。本土主義扮演的反對角色,「獲得新興臺灣國族主義的強力支持,因此公共資源漸增」,其力量足以和傳統主流抗衡,而且「目前正在文化場域裡爭奪主導地位」。而在這同時,「後現代潮流又已經取代了現代主義,成為另類文化視野的主要來源」。這股潮流「激發社會各領域發起運動」,向傳統挑戰,向威權發出檄文。就文學生產模式而言,臺灣已一步步「接近其他先進資本社會的文學」,蓋個別參與者(agent)「對場域變化的運作法則」警覺性變得更高了。
張誦聖的詮釋十分嚴謹,也深富警覺性。她知道後解嚴時代就在當下,「大部分受檢視的現象仍在發展當中,其長期意涵仍不明顯」,因此此文敘述性的說明多,分析性的結論少。張誦聖首先概述文學行動者(literary agents)對本土論述新猷的貢獻,其次「介紹含括在後現代主義之下的各種激進文化潮流的發展」,然後再「以當代小說為例,觀察比較專門、專業的文學行業」,最後再論1999年由《聯合報》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合辦的「台灣文學經典」評選這件如今已時過境遷的媒體爭議,希望「一窺文學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動態交互作用」。
臺灣的後解嚴時代也是後殖民論述大鳴大放的時代。在西方,掌後殖民論述的大纛其中之一者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他所謂文化上的「混血」(hybridity)之說甚囂塵上,歷數十年而不衰,對集體的偏執性認同大有破解之功。本書選了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陳綾琪教授的〈全球化自我:交混的美學〉,希望一睹巴巴的理論對臺灣小說美學的影響。此文實乃本書上冊所收錄〈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一文的姊妹篇,相較於前文以朱天心的《古都》為討論的重心,此篇的分析重點放在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儘管如此,巴巴依舊是她分析《荒人手記》的交混性形成的理論背景。對巴巴而言,交混的過程動態而不全,蓋「殖民勢力的文化」與「本土文化」互動時每存在著某種張力,「第三空間」(third space)遂生,而被殖民者可於此一空間內「商討」其文化認同,產生交混。由是觀之,這種交混理論內含「殖民情境的種種創造力」,而透過交混,「殖民主體或許能夠將殖民者的凝視原原本本地反轉於其自身,藉此顛覆殖民者的支配」,其「適用範圍已從殖民主義延伸到全球文化現象」了。《荒人手記》乃由女性作家以男同志的口吻寫作,所論亦男同志的情慾問題。這已是混合之一,加以書中語言異化,詞藻又夾雜傳統說部、英文音譯的外國詞彙與名物,而且還引用種種篇章,光是文類形式就光怪陸離,難以歸類,引人深思。朱天文喜歡跨越性別與文類的傳統關係,也喜歡在性別政治、後現代詩學與物質主義、作者意識形態與保守主義等議題上發揮。加上她對戒嚴時期的懷念,在在反映出典型臺灣外省第二代作家特有的社會歷史情結,而這種情結本身也是個交混的過程。陳綾琪於此琢磨者再,為1990年代臺灣作家交混的美學建祠立碑,值得玩味。
本書的「壓軸之作」──這個詞「名副其實」,而我用來也別有深意──是王德威教授的〈「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在這篇文章中,王德威首先並列清末憂患餘生與民初魯迅、沈從文三人筆下所寫的砍頭故事,藉以一探近代中國敘事文學中因「砍頭」所形成的「身體政治」。刀起頭落原是行刑手段,是典型的司法行為。然而在中國,砍頭也可表示戰爭頻仍的時代中,軍閥勢力的消長。讀了尤其是魯迅的《吶喊》與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後,我想中國的砍頭敘事的含義似乎超越了上述軍政問題,蓋其更深刻的意義仍然關乎「國家寓言」:觀人砍頭的群眾無不幸災樂禍,叫好之聲四起。他們又萬人空巷,有如爭睹一場宰豬殺羊以為犧牲的祭典!砍頭固然野蠻,更野蠻的是圍觀砍頭的民眾。魯迅認為中國早已是舉國愚民,沈從文的湘西那砍人之頭的「靖國聯軍」又與肆虐中國、到處為禍的日本皇軍有何差別?
皇軍到處「砍人之頭」,只有在臺灣作家舞鶴筆下才變成了「被人砍頭」的對象。我同意王德威的看法:「晚近有關砍頭的小說敘事中」,以舞鶴《餘生》「最值得重視」。《餘生》寫1930年臺灣中部發生的霧社事件:日人侵臺近乎三十年後,賽德克族部落有朝一日突然「起義」,砍下上百個日本殖民者的項上人頭。日本人與繼日人來臺的國民黨,對霧社事件都有個「官方說法」,但是舞鶴重構的歷史卻雙雙質疑,傾向於把砍頭視為一種「扼殺文明的暴力形式」,或是一種原住民「出草」的傳統祭儀。舞鶴有意從田野調查下手,為霧社事件重覓定義,王德威則在其間看到「扼殺文明的暴力形式」與原住民「出草」的傳統儀式之間「此消彼長的道德意涵」。舞鶴刻意書寫、重構歷史,《餘生》最後──再用王德威的話講──連「野蠻與文明的分界也變得幾乎難以辨識」。也是因此之故,王德威才認為「《餘生》處理的議題──(後)殖民抵抗政治和書寫暴力的倫理學──可以看作是對憂患餘生、魯迅和沈從文的砍頭敘事一個遲來的回應」。這裡我想指出另一點:霧社的賽德克族部落並非漢人,他們砍人之頭,基礎應和漢人不同。舞鶴旁觀其事,理解上有如一場後出轉精的「砍頭敘事」。王德威讀小說多有獨到見解,此所以我以此文為本書的「壓軸之見」。
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教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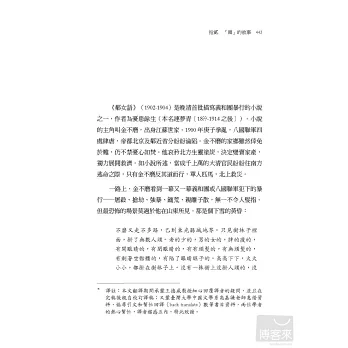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