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安土桃山的歷史寫真 陳銘磻
只要還有人,這個世界的戰爭就永遠存在;人類喜歡你爭我奪,喜歡相互殘殺,為了持有欲望而不斷爭戰,稍為放把火就能引起戰鬥,戰鬥製造仇恨,仇恨生仇恨,然後,又開始戰爭;人類自幾千年前就這樣從夙夜戰慄中活過來,也都寄宿為血腥歷史的一粒塵埃。常常,美麗的花朵明明一直在身邊,但人們卻連察覺的靈魂都喪失了,那是因為人類的欲望不被滅絕,人世間的戰爭就永遠不會結束!
讀日本安土桃山年間的「戰國史」、戲作家曲亭馬琴撰著的《南總里見八犬傳》、觀賞以戰國時代為舞台的影劇,無不被將士用兵謀略與征戰氣勢吸引;戰國時代之於日本歷史,是個群雄並起,紛爭權力,各國大名為拓展領土和權勢,使用奇襲妙招,盤據城池,預想成為英傑猛將的亂世。這場歷經一百五十年的戰亂時局,雖則群英並立、庶民凡夫也能殺出頭頂一片天,卻也令人看盡險象環生的人性極醜與極惡的詭譎多面,一如變化多端的世局,悟不透誰才是真英雄,誰又是真梟雄?
就因爭鋒亂局、人物眾多,正史和野史傳述的故事益加引人入勝,兼而為後世文學家、企業家、軍事家和政治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靈感,尤有甚者,其層出不窮的精采戰役,更成為後人探究企業經營戰術、政治謀略的樣板、典範,歷久不衰。如德川家康名言:「我們這些小國,若想要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生存下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兩強的勢力保持均衡,誰也不會贏過對方。」「如果一個人不能在第一次見面時,就讓對方知道自己的長處,那又有甚麼用?」再如織田信長所言:「在膽小鬼的眼中,敵人看上去都是大軍。」「所謂靈巧,就是跟別人思考的不一樣。」上杉謙信也說:「武運在天,鎧甲在胸,功勛在腳下。」豐臣秀吉於臨終前則說了句蘊含哲學意味的話,他說:「身隨朝露而生,隨朝露而去,我這短暫一生,如巍巍大阪氣勢盛,也只是,繁華夢一場。」
詳閱戰國史,讀到明智光秀叛變帶領織田軍朝本能寺出陣,攻打主公織田信長時,竟大言不慚喊道:「敵人就在本能寺!」被困本能寺的織田信長,看見敵軍打出水色桔梗家紋的旗幟,冷冷說道:「情非得已。」便喚侍從取來長槍出外迎戰。然而敵軍人多勢眾,信長在陣仗中負傷,侍衛忙喚信長逃脫。他以大勢不妙為由,不肯離去,走回殿內自盡。半生征伐無數的織田信長,最終在「本能寺之變」死於愛將之手,這不正如他自己所說:「今日之友乃明日之敵,是亂世之常。」亂世本無常,究詰史事,卻成為織田信長口中的「亂世之常」,使人讀後不勝噓唏。
戰國時代衍生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位「天下人」,他們不光是平定盤據全國各地的驍勇梟雄,還徹底改變日本列島長期以來遭受割據的局勢。孰強孰弱?孰贏孰輸?自非三言兩語可詮釋清楚。
有人偏好年輕的織田信長身為織田家當主時,胡作非為,喜好穿著奇裝異服、探究新奇事物,輕視王侯公爵、唾棄傳統禮儀,不把宗教信仰放入眼裡,卻擁有能屈能伸,超乎常人的胸襟。是個象徵理性主義與實力主義的「新型」戰將。「人的一生短短五十年,若與天地相較,像夢境,又像幻影,既一度享有此生,又豈有不滅之理。」這是織田信長出戰桶狹間前,吟唱「幸若舞」的曲目《敦盛》中的一句台詞,不難看出這個特立獨行,有謀略、有膽識,情緒起伏大,敢於破壞,又不斷創新的狂傲奇才,多變的性格。
有人偏愛豐臣秀吉以一介出身低微的平民,依仗才能與努力,擅用察言觀色處世;這個人,能在一夜之間,憑藉少數人力,少得可憐的材料,在尾張國和美濃國邊界墨股為織田氏建造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堅固堡壘,終獲桀驁不馴的織田信長賞識重用,從一個農夫破格提拔為武士,繼而成為織田信長身邊不可或缺的智將;乃至步步升遷,登上權力巔峰,縱橫亂世。
有人喜歡德川家康由小小的三河國主起家,以無比的謀略,無情的忍耐,驚人的毅力,機關算盡的奪取天下。人們認為,德川家康是從「弱」、「由弱轉強」到「強」三個階段展現求生存、謀發展、圖壯大的意志。他無異議的承認自己實力弱小,因而在政治上採行低姿態,在戰場上,他了解退一步即無死所,只能「有進無退」的以賭命方式完成心願,德川家康的成功在於擁有「認知力」,「認知」使他從忍辱負重轉進為否極泰來的非凡成就。
不過,也有人認為,若非明智光秀叛變,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兩人將只是織田信長身邊的隨從、跟班,不足一提。
不論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上杉謙信、伊達政宗或各氏家臣、軍師,這些從戰國亂局竄起的人物,叱吒風雲或引領風騷;各懷鬼胎或爭權奪利,無不豐富戰國史記的多樣魅力。讀史或閱覽戲劇,日本戰國時代的史事特別撩人激情。
這本《戰國武將歷史之旅》,便是從讀史、觀影中,因喜歡、好奇,繼而身體力行,走進歷史書籍中,真實地景的寫照,並列舉出與戰國武將大名相關的史蹟、領地、景地,再就這段精采歷史的進程報導,以文學旅行方式,帶領讀者進入戰國時代大名武將的時光隧道,窺探歷史之謎、文學之實,以及風格迥異的安土桃山文化之美。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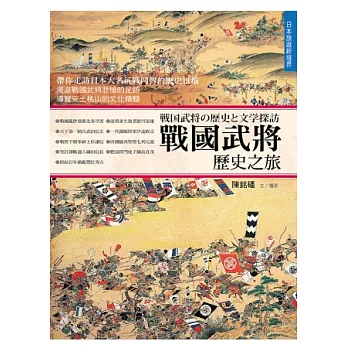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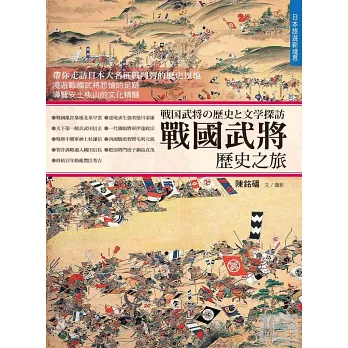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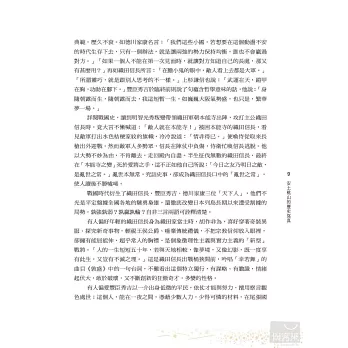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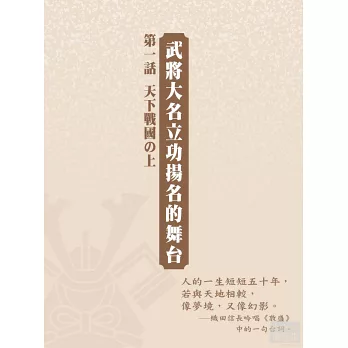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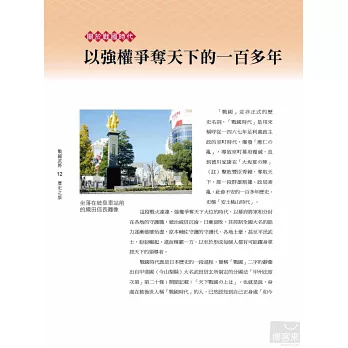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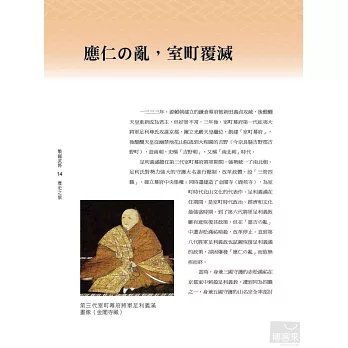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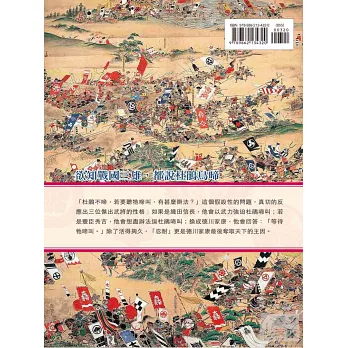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