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病中寫莊
《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甫出版刊行,內心已給自己一個許諾,接下來要解讀的是承老子之學而開出新理境的莊子。
問題在,只解讀莊子自家作品的內七篇呢?還是要擴及出於後起門徒之手的外雜篇呢?因為,「解讀」不同於辭句的注釋,與字面的翻譯,而是義理內涵的抉發,與生命智慧的體悟。且外篇道已流落在主體生命之外,成了客觀認知的對象;而雜篇對道的觀解,雜陳偶現,而難期精純。加上外有十五篇而雜有十一篇,為了避免篇幅過於冗長,而失去詮釋的重心,故外篇只取〈秋水〉,而雜篇則取〈天下〉。這兩篇獲致歷代學人的絕高評價,〈秋水〉被認為是文學藝術的巔峰之作,〈天下〉則被當成《莊子》一書的後序。我在數十年講論莊學的路上,惟有這兩篇是以單篇論文的形態發表,前篇為〈莊子秋水何以見外〉,後者為〈論莊子天下篇評析各家思想的理論根據〉。由是解讀莊子即以內七篇、外秋水與雜天下三者並列而依序詮表。
民國百年七月,我在大學的專任教職,就在淡江大學中文系所主辦之「第一屆新儒家與新道家學術研討會」熱烈展開聲中,宣告終結。八月,永和住家全面整修,一家五口分居三處,我與家貓阿橘寄身在附近公寓的加蓋頂樓,在漂泊流落的孤寂歲月中,開啟了解讀莊子九大名篇的書寫工程。這是博士論文之後最龐大也最用心的寫作規畫,從重讀歷代注疏,再勾勒出篇章綱目,並依段落逐句給出義理的解析詮釋。九月,新學期開課,每星期仍在淡大中文所授課四小時,並有華山講堂、敏隆講堂、三千教育中心、經典研習班等處的民間講學,還外加一個來家上課之一對一家教,堪稱寫書與講學兩頭忙,完全感受不到教職退休卸下重擔的輕鬆自在。
隔年元月,家整修完成,一家五口又重回舊家新居,人貓不再流落漂泊,而回歸家居日常,身心稍得安頓。一直到六、七月間,整整投入了一年的時光,勉力草成初稿。這期間還安排了新加坡、香港、南京及山西的講座與研討會行程。在內外交逼之下,好幾回腸胃不適就醫,貓也因尿道結晶阻塞,幾度進出醫院,最後做了人工尿道的手術,似乎人貓之間有著相依為命的存在感應!
九月中旬,腹腔劇痛,永和小診所未有檢驗設備,仍依循舊病例,以腸胃炎治療,三天之後病情未見緩解。十七日請華山講堂聽課的紀建興醫師來家觸診,判定病痛在肝膽,而不在腸胃。當晚即開車送往榮總急診,驗血結果,染毒指數破表,白血球升至一萬六、七,外科主治醫師前來告知情況嚴重,安排做斷層掃描,發現膽囊阻塞而感染發炎,立即進行引流手術。在這一抽血、打顯影劑的流程中,全身忍不住的劇烈發抖,我試圖以意志力來壓制,卻完全無效,當下還自我批判何以如此禁不起考驗,病痛纏身,生命即面臨全面崩解的邊緣。躺在病床上,蓋了兩層棉被,還兀自抖個不停,測量體溫,已高達三十九度五,難怪畏寒如此之甚。原來,生命病痛是生理官能之形氣邊事,與理想性、價值感、精神涵養跟人生智慧完全不相干。歎了一口氣,躺在急診室的偏僻角落,過了最漫長的一個夜晚,閉著雙眼耳邊盡是病患家屬與醫護人員匆忙來去的吵雜聲,心想眼前景象不就是人間困苦的濃縮寫照嗎?一直挨到第二天中午,才入住內科病房,打抗生素進行對治性的治療。
突然病發住院,所有課程緊急喊停,人情道義一概放下,鎮日困守病床,寫書完全停擺,看《笑傲江湖》解悶,形同令狐沖被師門誤解的一段自我放逐的生涯。住院十二天,九月二十八日主治大夫朱啟仁醫師說老師可以回家了,兩個禮拜之後,再來做摘除膽囊的手術吧!
回家說是調養,實則是加緊彌補被耽擱下來的書寫進程。兩週之後向外科主治大夫報到,驗血結果膽紅素太高,而血紅素偏低,說狀況不好不宜開刀。回轉內科調理,再開抗生素,等膽紅素下降。一週之後,膽紅素未見下降反倒上升,與預期落差太大,內心十分沮喪,有好幾班正等我回去講課呢!十月十六日一女中老學生余美瑛女史來電說病房有空位,請老師再來住院,我斟酌再三,實在不想再去空等,紀醫師隨即在通話中力勸,說總比在家易於控制病情,且可以進入診療醫護的程序中。當天夜晚再度住院,並攜帶書本稿紙前去,得空可以書寫。
十八日午後,紀醫師來病房探視,約請他的同學李醫師,前去跟外科主治大夫溝通,而外科主任也在座,說王教授有地中海型貧血的家族傳統,故膽紅素太高可能是間接性因素造成。三點多四位醫師一起來到我的病房,石主任說假如王教授願意,明天上午即可進行摘除手術,就由石主任與王大夫共同主刀,並謂開完刀就得連袂趕去上海開會。不過兩位大夫還是力勸等情況好轉再開刀較妥,說發炎的膽囊已做了引流手術,基本上生命是安全的,何必急在一時而承擔不必要的風險?並強調有人身上掛著引流袋半年之久,甚至好幾年也可以沒事。此話一出,我再無考慮空間,立刻做出決定:「那就開了!」當下簽同意書,兩位主刀大夫起身離去,做相關安排。那時我正在夕陽斜照中寫〈大宗師〉的最後兩段,向兩位內科醫師致謝送別,護理師要求轉往外科病房,進行心電圖檢測,與肺部X光透視。
那時光線夠亮,我還是將當下放下一切的「坐忘」工夫與窮困之極歸之於「命」的這兩段寫完,因為心境完全相應。心想萬一開刀而回不來的話,至少寫出了完整的內六篇,而不要〈大宗師〉缺了末兩段而徒留遺憾。「坐忘」是當下可以放下一切,理由在一切已在當下,故重點在「道」的體悟,而不在「忘」的工夫。最後一段問生命的困窮是誰造成的,既不會是生萬物的天地,也不可能是生兒女的父母,所以給出了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沒有理由的理由,說還不是「命」嗎?認了也就不苦了,原來,認命等同坐忘,在放下的同時給出了自身存活的空間。
當晚折騰了一晚上,輸血兩袋,因血管太沉,三位護理師忙得團團轉,在我兩隻手上尋找可以扎針的地方。隔天早上八點,推入開刀房,十一點在恢復室醒來,生命存在只剩下一個「痛」字,我什麼都不能想,什麼也不能說,我知道開的不是內視鏡的小刀,而是在腹腔劃了一大刀。石主任來到身邊說了一長串情況是多麼不好的話,我沒有力氣回應。就在書寫莊子的體道過程中,而有此病痛之極,「道」解消不了痛澈心扉的痛,不能問是誰造成的,「命」終究要「認」。道是一切,一切已在當下,而當下卻不再是一切,「痛」僅能自我承擔,因為切身之「痛」是放不下、忘不了也走不開的。
同時開刀的二十八床病患,我是最後一個被推出來,本來還以為依年齡排序;未料,竟是等待再作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以確定總膽管出現的陰影是不是結石。原來,苦難還未結束,在檢驗室換床劇痛之下,忍不住喊痛,還好麻醉之後,此身已非我有,痛就此離身而去。由是可以了悟,道家支派的慎到,何以會說出「塊不失道」的絕望話頭,意謂即使生命如土塊,此中自有道。因為道在生人救人,土塊無知無感,人在痛苦不堪的時候,沒有感覺等同得救。這是戰國亂世從宋榮子的「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再到告子的「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最後逼出慎到「塊不失道」之一系列逐步沉落的生命自救之道。宋榮子不要外在的世界,不求功名利祿,就可以遠離屈辱,而保有生命本身的榮耀;告子說當外在的不合理現象,已闖入心頭,而擾亂了生命的平靜,那就不要再求助於血氣去硬撐對抗,因為最後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作息,也將持守不住。現代人的病痛在此,什麼都想要,「心」亂之後,意志跟進,且鼓「氣」前行,此之謂「心使氣曰強」與「強行者有志」。而使氣強行的後遺症在心律不整、消化不良、內分泌失調,甚至吃不下,也睡不著,說是打天下,實則掏空了自己。「塊不失道」是沒有希望的希望,也是沒有出路的出路,只要把生命壓縮成土塊,就無憂無患,不痛也不苦了。〈應帝王〉說列子「塊然獨以其形立」,放下平生榮耀與一身傲氣,讓自己回到什麼都不是的存在本然中,從泥土裡尋求再活回來的價值空間。
確定不是石頭而是水泡之後,推回病房,又輸血兩袋,打止痛針。迫切的問題在麻醉之後尿解不出,此中尚有一打不破的尊嚴問題,我真的要躺在床上對著尿壺解尿嗎?午夜十二點,住院醫師前來關切,說超過十二小時沒解尿,就得插管導尿。只得忍痛下床,推著點滴架到洗手間,幾番來回,總算解開了壓在心頭的大患。吾人立身處世,在複雜微妙間,「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心知執著名號,就在爭排名的人為造作中,失落了本德天真,執著自困,而造作自苦。問題在,我們也能就醫求診,像開刀一樣的決斷割除,且強忍痛楚一步一步走去面對,並三番兩回的尋求化解之道嗎?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人生路上理想的可能失落,情意的不免挫折,也就不會留下那麼多不堪回首,卻又掙脫不了的憾跟痛了。
開刀之後,轉住單人病房,除了清靜之外,友朋來訪,較有立足對坐的餘地閒情,最重要的是吾家太座伴隨照護,起居作息也當有個獨立的空間。每天清晨,起身梳洗,等待小醫師來換藥,再恭候大醫師帶隊來問病情,好像回到成功嶺受訓的歲月。輪班的護理師隨時進來量血壓心跳與脈搏,或抽血吊點滴。第三天,醫師慈悲,點滴架掛上了嗎啡袋,被痛感淹沒時按它兩下,讓痛感暫且離身。嗎啡成了救護靈丹,儼然以「道」的姿態出現。不過,它僅能離苦,而不能活命,故用了五天,即被撤離,以免病人過度依賴,而成了毒品。當代社會,人心盲昧不明,人間茫然不定,而人物忙碌不堪,除了投靠怪力亂神之外,要不就藏身大麻迷幻間,在沒有出路中找出路,在沒有感覺中製造感覺,此身飄飄然,在迷離幻境中,忘了自己是誰,不必背負責任,也不用承受壓力,當下就從苦難煎熬中獲得解脫。問題在,那就是〈天下〉篇所說的「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哲理智慧本在開發「生人之行」,卻在人間扭曲與人物變形之下,自我異化沉墮而為「死人之理」。從宋榮子不要「外」,而只要「內」,到了告子不要「心」,而只要「氣」;再到慎到竟連「氣」也不要了,只要生命如土塊。「生人之行」竟成了「死人之理」,這是人文價值的全面崩解。
十月卅一日,傷口仍未癒合,兩位醫師說可以回家了,或許擔心病人離開醫療體系會沒有安全感吧!又體貼的說,你想多住幾天也可以。不用考慮,立即辦出院手續,未料,周進華先生偕同兒子上觀,煮來一大鍋熱騰騰的鱸魚米粉,盛情可感,一道打包回家。心裡只有一個意念,回家寫我猶未完成的解讀工程。
十一月就在家安居療養,除了躺臥擺平自己之外,都關在書房寫稿。老問題又來了,不甘寂寞的阿橘看我打開桌燈,雖然大書桌上已擺滿了書,燈光溫暖卻散發出不可擋的吸引力,牠縱身一跳,總會找到牠最舒服的位置,就橫身躺臥在我的稿紙上。有時我還得讓出大位,偏安一隅,極其委屈的寫稿。看牠頭枕郭象、成玄英,身跨王船山、宣穎,足蹈阮毓崧、王先謙,一身跨越千年傳統,一切已在這裡,一切可以放下,牠坐忘片刻,就夢為蝴蝶去了。牠沒有學究天人,至少已身通古今,是否「成一家」,就看牠的主人能否「虛室生白」而「吉祥止止」了。心「無何有」,生發湧現的是深藏在字裡行間的道妙哲理,而人間美好就依止於筆觸書寫的「希微」聲中。整整一個月足不出戶,寫出了〈應帝王〉、〈秋水〉與〈天下〉三篇,十一月二十九日終告完稿。
十二月我重回講堂,復歸舊有的生活軌道,只是步調放慢許多,英雄無膽,西螺七坎不成,僅能守著第八坎,解讀經典當學者了。民國一○二年元月中旬,在球友力邀之下,重返網球場,步履猶虛浮,看似輕盈,實則腳跟不穩,踩不著實地,下場拉球十幾分鐘,趕緊喊停,在大榕樹下陪友好喫茶聊天。
回首退休之後的這一年半歲月,變動不可謂不大,而今家整修好了,一家人都回來了;病治好了,書也寫成了。一切放下,一切還在這裡。客廳茶趣,講堂論道,球場競技,一切回歸家常日常,而人生不就在家常日常中活出天大地大嗎?剩下來的考驗在,也可以在生死無常間來去自如嗎?
王邦雄序於民國一○二年三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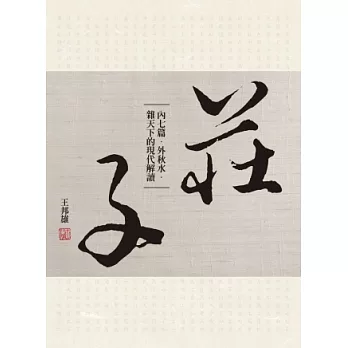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