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外翻譯史上罕見的誤譯∕單德興
在中外翻譯史上,像《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舊譯《格列佛遊記》、《格利佛遊記》或《大小人國遊記》)這般普受歡迎、卻又遭到誤譯與誤解的作品甚為罕見。誇張地說,《格理弗遊記》的中譯史本身便是一部誤譯史,因為這部英文經典之作在易「文」改裝後,改頭換面程度之大不僅是「一新耳目」,甚至可說是「面目全非」。於是便出現了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格理弗遊記》在中文世界裡幾乎是人盡皆知的兒童文學、奇幻文學之作,另一方面這種盛名反倒掩蓋了它原先在英文世界的經典地位,以及作者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身為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諷刺作家的評價。
綏夫特的生平簡介
綏夫特於1667年11月30日出生在愛爾蘭的都柏林,父母親都是英國人。他於1682年就讀當地最高學府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1686年獲得學士學位,1688年前往英格蘭,擔任田波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的秘書,1692年獲得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702年獲得三一學院神學博士學位。
倫敦是當時政治、經濟、宗教、文學的中心。綏夫特穿梭於倫敦與都柏林之間,一方面希望在英國文壇謀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有意往政界發展,涉入惠格黨(the Whigs)與托利黨(the Tories)之爭,以致得罪當道,未能如願在倫敦獲得任命,只得於1713年6月接受都柏林聖帕提克大教堂總鐸(Dean of St. Patrick’s Cathedral)一職,直到1745年去世,前後長達32年。愛爾蘭在政治、經濟上長期遭受英格蘭剝削,綏夫特心中甚為不平,提起如椽巨筆,充當被壓迫者的喉舌。時值新古典主義時期,諷刺文體(satire)盛行,他便以此文體撰詩為文,諷刺時事與人性。〈野人芻議〉(“A Modest Proposal” [1729])藉由「野人獻曝」的手法,建議愛爾蘭窮人將嬰兒賣到英格蘭充當佳餚,既能減輕人口壓力,又可賺取收入,為英國文學史上最有名的諷刺文。
在他的眾多著作中,流傳最廣的就是1726年10月28日於倫敦出版的《格理弗遊記》,不但頗受英國人矚目,廣為流傳,不少人針對書中影射的人、事對號入座,以此為樂,而且得到外國青睞,譯本紛紛出現。由於有些諷刺過於露骨,倫敦書商莫特(Benjamin Motte)於初版時唯恐因文賈禍,於是增刪、改寫。綏夫特甚為不滿,九年後在都柏林書商福克納(George Faulkner)出版的作品集中,納入親自修訂的《格理弗遊記》作為第三冊,書前特以主角格理弗的名義撰寫一函,批評遭到竄改的版本。
綏夫特四十歲左右罹患梅尼爾症,導致暈眩、重聽。七十歲之後,痼疾益發嚴重,逐漸喪失記憶與心智能力,於1745年10月19日逝世。綏夫特終生未娶,身後與紅粉知己瓊森(Esther Johnson)同葬於聖帕提克大教堂的地板下,遺產的三分之一(一萬一千英鎊)在都柏林設立聖帕提克醫院,至今依然是愛爾蘭著名醫院,以治療精神病聞名。他除了為愛爾蘭伸張正義,發揚人道精神之外,最大的遺產便是他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格理弗遊記》。
必也正名乎?
Gulliver’s Travels原名“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寰宇異國遊記」),在中文世界裡最為人知的譯名是《大小人國遊記》。其實全書共有四部,依序是主角到小人國、大人國、飛行島等國與慧駰國的冒險記聞。《大小人國遊記》一名簡單明瞭,響亮易記,文字對稱,其實不僅在內容上腰斬了全書,而且在名稱上以音害義,掉反了原書的順序。
《格列佛遊記》或《格利佛遊記》之名較忠於原作,也往往保留第三、四部,但此譯名仍有商榷之處。如“Gulliver”一名很容易就讓原文讀者聯想到“gullible”(「容易受騙」)。「格列佛」或「格利佛」雖稱得上是忠實的音譯,卻未能傳達原文幽微、諷刺之處。故本書採變通之計,將“Gulliver”譯為「格理弗」,除音譯之外,力求維持原文意涵,暗示主角勇於冒險、敏於學習、「格」物窮「理」,卻屢遭拂逆,到頭來落得自以為是、窒礙難行、違背常理、格格不入、落落寡歡(「弗」)。
早期中譯
《談瀛小錄》
此書第一個「中譯」《談瀛小錄》實為改寫,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1872年5月21至24日)連載於上海《申報》。此版並未署名,然而根據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考證,譯者可能是《申報》編輯蔣其章。
為了加強「真實」的印象,《談瀛小錄》以頭上安頭的方式加了一段前言,指稱有人發現數百年前遺稿,提供報社披露。此版依該報體例以文言撰寫,沒有任何標點,甚至把主角轉化為中國東南沿海人士(「某家籍隸甬東」)。然而,此篇連載僅四日即戛然而止。總之,《談瀛小錄》為此經典之作的中譯開啟先河,並為「譯寫」(transwrite)、翻譯就是「改寫」(translation as rewriting)以及譯文的「馴化」(domestication)、「歸化」(natur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提供了具體例證。
《僬僥國》∕《汗漫游》
第二個中譯以章回小說形式連載於《繡像小說》,由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至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配以中國風插圖,未著譯者。此版起初使用「僬僥國」一名(「僬僥」為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矮人),非但未掩飾其為翻譯,甚至刻意標舉異國風味。後來易名「汗漫游」,兼具「不著邊際的漫遊」及「漫漶難以稽考」之意,而其「水勢浩瀚洶湧」之意涵又與主角多次海上冒險吻合,比原譯名更為適切。此譯本各章標題採取中國章回小說的對仗回目,內文卻以白話翻譯,長期連載,並配上「既中又西」、「不中不西」的插圖,生動展現了圖文互涉的況味。
《汗漫游》將四部全譯,提供了更完整的面貌,但不乏歧出之處:如第三部僅譯出飛行島之遊,割捨其他奇國異域;第四部在主角離開慧駰國後,另增遭巨鯨吞入腹中一節。前者為省略之過(sin of omission),後者為增添之過(sin of commission),顯示《汗漫游》依然難逃改寫的命運。
《海外軒渠錄》
林紓與魏易(一說曾宗鞏)合譯的《海外軒渠錄》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第一個以專書形式出版的該書中譯,而且托桐城名家林紓盛名,成為流傳最廣的譯本達數十年之久,在此書中譯史上佔有獨特地位。
《海外軒渠錄》意指「以海外奇聞異事博君一粲」,並藉以諷刺時事及人性,與《鏡花緣》有異曲同工之妙。林紓不曉外文,只得與人合譯,畢生竟完成一百八十部左右的文學翻譯,誠為世界翻譯史上的異數。林紓在諸多譯序中表達感時憂國的強烈情懷,可見他從事翻譯除了為稻粱謀之外,實有更深的懷抱。林譯古雅生動,甚受歡迎,影響遠較前二版本深廣。然而由於腰斬全書,以致國人誤殘為全,以訛傳訛,形成中文世界裡「大小人國遊記」的傳統。
《小人島》∕《小人島誌》
台灣最早的漢文譯本很可能是刊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的《小人島》(第二期起改稱《小人島誌》),自明治四十二年(1909)10月25日至次年1月25日,連載四期,譯者為蔡啟華,序言以駢文撰寫,對仗工整,譯文也出之以文言,標點主要為圓圈,如傳統之句讀,偶爾出現引號,並以日文譯出兩處地名,在此書中譯史上難得一見。由使用文體與刊登場合推測,讀者多為教育界人士及社會菁英。
蔡「試於公退無聊之候。偶檢逸史。為述一絕奇絕巧之事。」英文原著第一部共八章,蔡自稱「抄譯」,意即摘譯,序言與譯文分刊四期,篇幅短小,內容簡略,著重原書奇巧之處,志在娛悅讀者,而非諷喻,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然而在大力鼓吹日化的時代,蔡譯以典雅漢文發表,此舉本身便可能隱含愉悅∕逾越之動機與效應,值得深思。
《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
台灣另一早期譯本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小人國記》刊於昭和五年(1930)3月3日至5月18日,《大人國記》刊於7月6日至12月6日──也是節譯∕腰斬,譯者不詳。然而兩篇〈緒言〉的文言典雅,旁徵博引,用於翻譯的白話相當流利,足證譯者對古今文體之駕馭能力,譯文中也呈現對人性與政治的諷喻。
此版特色在於透過譯文暗示當時台灣殖民情境以及譯者的反殖民態度。譯者有意經由新聞媒體,讓讀者得以接觸西方文學與社會,達到啟蒙作用,更透過翻譯(運用漢語,而不是殖民政府大力提倡的日語),暗示對當權者及其政策之不滿,既達到諷喻的目的,也避免牢獄之災。
綜而觀之,此書雖可概稱為奇幻文學,但中譯傳統大致有二,一為諷刺文學,一為兒童文學,後者對該書的普及作用甚大,大都以改寫的腰斬形式出現,直到晚近才漸有納入全本的趨勢。此外尚有一旁支:由於故事具想像力,內容生動有趣,半個多世紀來便有英漢對照本或註解本,晚近更搭配有聲書CD、MP3、電子書等,作為學習英文之用。
文學理念與效應
筆者參觀都柏林作家博物館(Dublin Writers Museum)及翻閱愛爾蘭文學史相關論述時,發現許多以綏夫特為愛爾蘭文學的鼻祖,然而詢問當地民眾,卻發現不少人似乎對他有著矛盾的情感,或許與其認同與諷刺有關。
然而,諷刺文學為何大受歡迎?綏夫特在為諷刺下定義時,順帶諷刺人性:「諷刺這面鏡子,觀者在鏡中通常只見他人的面孔,而不見自己。它之所以那麼受世人歡迎,很少人反感,主要原因在此。」綏夫特對自己諷刺的手法與心態則有如下說法:
但他的目的從不在於惡意;
嚴厲斥責罪惡卻饒過姓名;
沒有一個人能夠憎惡他,
因為成千的人都是對象;
他的諷刺所指向的缺點,
無非所有凡人都可改正……
綏夫特對於寫作目的也有獨特體認,宣稱自己「殫精竭慮的主要目的是攪擾世界,而不是娛樂世界。」弔詭的是,他不但以寫作去攪擾世界,更因為諷刺手法獨特,反而化攪擾為娛樂。他對《格理弗遊記》的說法是:「這些遊記精采,大益於世道人心。」由此可見,他所謂的攪擾或娛樂都只是手段,目的是回歸到當時盛行的文學觀:「寓教於樂」、「文以載道」。只是此處「寓」、「載」的方式不是單純的「說教」或乏味的「傳道」,而是透過「攪擾」與「娛樂」的高超手法,讓人印象深刻,即使哭笑不得,卻仍舊「受教」、「明道」。因此,《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George Orwell)對此書推崇備至:「如果要毀掉世上所有的書,只保存六本的話,我一定會把《格理弗遊記》列入其中。」
江森(Samuel Johnson)曾盛讚莎士比亞的戲劇宛如「人生的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綏夫特以超凡的想像創造出小人、大人、慧駰、犽猢(“Yahoo”)……來對照人類,提供的是一面哈哈鏡,透過文字的折射,人性某些方面被放大,某些方面被縮小,看似扭曲,卻是顯微,然而其攪擾與娛樂正在於此,其寓教於樂也在於此,有請讀者親自領會。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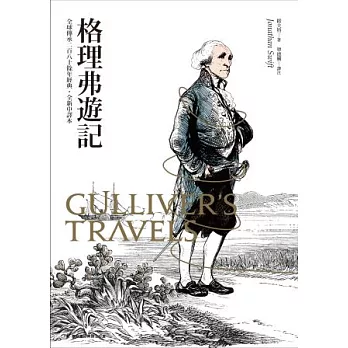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