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導讀
追尋親情的烏托邦
經過漫長二十年的積澱,先後於一九九0年與一九九四年以《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和《記憶傳承人》(The Giver)兩部作品,兩次榮獲紐伯瑞金牌獎的青少年小說大家露薏絲.勞瑞(Lois Lowry),終於在二0一二年,七十五歲高齡時完成理想國四部曲。《記憶傳承人》於一九九三年出版後即好評不斷,不久就得到紐伯瑞獎;二千年完成《歷史剌繡人》(Gathering Blue);二00四年我們讀到《森林送信人》(The Messenger);二0一二年《我兒佳比》(Son)問世。
細讀這四部作品,讀者可把它們歸類為反烏托邦小說,雖然每個故事各有主角,也可獨立,但基本架構仍然有連結之處。譬如首部曲《記憶傳承人》的主角喬納思逃離同化社區,放棄記憶傳承者的身分,他的生死成為一個謎。作者在二、三部雖沒有直接點明,但聰明的讀者細讀時,不難發現書中的另一村落樂土的領袖,就是大難不死的喬納思。到了第四部曲時,喬納思與綺拉結婚,卸下領袖重擔,主角換成克萊兒與佳比母子。克萊兒在同化社區裡,身為孕母,因為未服用藥丸,竟一直思念編號三十六,即被喬納思帶走的嬰兒佳比,於是決心遠離家園尋找兒子。
好的少年小說總不離親情、友情、愛情的宣揚,這四部曲尤其強調親情。在首部曲中,主角喬納思是孕母所生,與所謂的「父母」毫無血緣關係,因此與家人互動時,彼此言語僵硬,不含情意。他在接受記憶傳承訓練時,反而嚮往為長者慶生的畫面,渴望可以擺脫制式的生活,以獲得真正的親情滋潤。他的出走當然也受到記憶傳授人親生女兒蘿絲瑪麗(Rosemary)自求解放的影響,因為他們父女展現的是大愛。後來喬納思從未提到他形式上的養父母,對自己的養妹也只是輕鬆帶過,因為他追尋的也是人類大愛。
對於熟悉《記憶傳承人》的讀者來說,《歷史剌繡人》的情節似曾相識,同樣是閉鎖型的社區。社區的生活同樣由一群所謂的長老掌控。綺拉的遭遇宛如喬納思的翻版。隨著年齡的增長與細心的觀察,她發現了真相,只是為了更大的使命,她必須隱藏自己的情感。母親的過世讓頓失親情的她轉而對小麥、湯瑪、小喬深切的關懷,直到未曾謀面的盲父出現,她才無法抑制的宣洩對親情的渴望。
《森林送信人》中的麥迪(即小麥)也一直期待親情的滋潤。他在原生家庭裡並未得到應有的照顧。認識綺拉後,感受到她的和善,便把她當作親姐姐般看待;後來與綺拉的盲父同住,也視其若父,甚至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帶領綺拉勇闖森林。至於《我兒佳比》中的克萊兒,則是終其一生都在追尋親生兒佳比,她歷盡艱辛,縱使捨棄青春也要請求交易大師指點迷津,最後終能達成願望。克萊兒的強烈母性,可以說是作者追憶喪子的情緒轉移,作品帶有淨化作用。
勞瑞書寫這四部曲的基本手法,仍然依循著「在家→離家→返家」(home→away→home)的追尋(quest)模式(也就是神話大師坎伯在《千面英雄》裡提到的英雄歷險過程:啟程、啟蒙與回歸)。《記憶傳承人》中的主角喬納思帶著佳比離開居住的社區,目的有二:一是將傳授人背負的一切,歸還給社區裡的每一個人。二是自己去尋找另一個真正的樂園。《歷史剌繡人》中的綺拉被迫毀家,走入預先設計安排的另一個舒適卻冰冷的處所。等她認為自己使命已達時,再跟隨麥迪到另一個家──她盲父的家。《森林送信人》中的麥迪離開充滿暴戾的家,去追尋新的歸屬,終於在另一個略具烏托邦模式的村子落戶,並與綺拉的盲父同住。《我兒佳比》中的孕母克萊兒為了尋找親生佳比,被迫離開原來的社區,經過艱辛的考驗後,終於到達新的烏托邦村子。
這些角色即使能夠完成旅程,重返家園,也會赫然發現,原來的家已經不是原本的模樣,因為經過不同時空的陶鑄與冶煉,擴展了自己的省察視野與生活歷練,對家的觀念也會有另一層新的看法。他們可能學會自我調適,讓自己適應新家,或者顛覆已經瀕臨滅絕的老家,另起爐灶,給家人帶來新氣息、新希望。
作者刻意鋪陳各書中主角的追尋旅程,其用意並不難理解。「大同世界」一直是古今人類嚮往的理想社會,但實際生存的社會,卻始終與理想社會差距太遠,於是一些先知先覺便把這種願望寄託在創作中。在中國,我們有陶潛(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李汝珍的《鏡花緣》(如「君子國」的說法);在西方,除了較早的柏拉圖的《理想國》與穆爾的《烏托邦》說法外,希爾頓的《香格里拉》也給予我們相當程度的憧憬。但這些作品基本上不切實際,不合人性人情,因為禁絕飽暖以外的一切物欲,根本違反人類天性。在經過上天下海,苦苦尋覓之後,人們發現烏托邦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激勵,所以二十世紀開始,出現的反烏托邦文學就是這種理念的反動,例如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島》,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山莊》;這些作品強調的是:烏托邦社會只是一種虛幻的想望,不可期待。
藉由理想國四部曲,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烏托邦制度的檢視。《記憶傳承人》裡的老傳授人在傳授記憶的過程中,幫喬納思揭露了社區的真相,並間接鼓勵喬納思出走,把所有記憶還給社區的每一個人。《歷史刺繡人》中的綺拉以近乎神奇的刺繡天分僥倖存活,但盲父卻告訴她:迫使她差點成為孤兒的,正是她一向視為恩人的長老;她又在傳唱大會上,親眼目睹傳唱人腳踝上的腳鐐時,才終於了解這個社區的本質。即使在《森林送信人》中接近真正理想烏托邦的村子裡,亦有許多異議的聲音。良師益友的反常態度、社區出現反對收容更多外來者的聲浪,加上交易大師的攪局,都令人不安。整個理想社區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
《我兒佳比》先從不同角度重述克萊兒與喬納思曾經生活過的同化社區的故事,再把前面三本小說的角色牽連在一起,故事既有魔法又帶神祕。背景雖是三個獨特的社區,但主軸都不離對愛的渴望與反思。在《記憶傳承人》和《歷史刺繡人》裡,作者把「自私」與「掌控」描述成一件自然不過的事。統治階層往往站在制高點,做出一些不見得正確、甚且有害大眾的決策。在《森林送信人》、《我兒佳比》裡,人性中的「惡」以一種超自然的、巧妙的處理方式,做出相同的詮釋;只是擁有奇特力量的交易大師,終因誤用能力而導致滅亡。
這些追尋理想夢土的故事,同時告訴我們,即使是像大森林之外的那個力主自由民主、收容不同族群的村子,也難免會出現「良師益友」或「交易大師」這類自命不凡、自以為是的人物。他們自私自利,以完成某種企圖為終極目標,往往使整個村子陷於不安、混亂的狀況。他們忘記村子創立的宗旨是「無私」,他們忘記他們逃離「政府殘暴、嚴刑峻法、民不聊生、虛幻不實」的故鄉,是為了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生存空間。人們在追求與形塑完美社會的過程中,如何避開或去除這類人性中原本具有的「惡」,是許多深信人性本善的人必須費盡周折才能達成的。
在細讀這四部曲後,我們充分了解烏托邦永遠無處可尋。無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生存的空間永遠有無數的難題等待解決。
這一系列小說和一般科幻小說不同,它們不刻意強調高科技的奇幻與毀滅性殺戮的場面,沒有恐怖的爭權奪利的描繪,沒有虛無渺茫的未來承諾。它告訴讀者,人間天堂不是香格里拉,不是人民公社,而是我們目前正生活其間的現實世界。縱然這世界並不完美,有太多的生死離別,依然是最理想的世界──不要畏懼,也毋須排斥。
張子樟(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理事長)
導讀
找回選擇權
對於未來,我們總是懷抱奇思夢想。也許穿越時空的飛行器已經發明,也許飲食方式起了革命,也許學校的學習不再是一場噩夢,也許星球之間已沒有藩籬。因此科幻小說興起,以破除現實世界規則的天馬行空,建構虛擬的未來世界;然而未來世界出其不意的邏輯,乍看之下或許充滿新意,但是新世界的新邏輯,卻可能隱含更多生存的難題、人性的考驗,這也是科幻小說令人怦然心動的地方,它迫使人們正視文明演進的軌跡,提出未來可能產生的危機,讓讀者不得不回頭省思眼下的生活和腳步。
在一九九四年摘下美國紐伯瑞兒童文學金牌獎的《記憶傳承人》,是一部看似寫實小說,細讀之下,方知進入了一個烏托邦,描繪未來社區型態的寓言小說。書中沒有邦國關念,取而代之的是社區意識。
故事以即將邁入十二歲的喬納思為主軸。喬納思最喜歡每年的十二月,因為眾人翹首盼望的社區「大慶典」即將來臨,它不是聖誕節,因為社區裡沒有宗教意識,而是所有十二歲以下的孩子,都將在這一天一起進階,領受長一歲的賀禮。比如一歲的孩子將有自己的名字,八歲的孩子可以開始依據興趣當義工,九歲的孩子可以領到自己的腳踏車,最重要、也最受關注的是:十二歲的孩子將獲知未來被派任什麼工作。
在這則故事裡,令人眩目的不是機器戰警或奇形異狀的外星人,而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社區。它的領導結構很簡單,最高單位是長老會,由一群社區裡最具智慧的長老組織而成,負責決定社區的大事、法則、眾人的工作。
為了讓農作物有最佳產能,這裡恆溫,沒有春夏秋冬四季,沒有太陽、月亮、動物和風雨。為了將危險減到最低,不讓大家有病痛,這裡沒有汽車,醫藥免費,婦女不用生育,而由職業「孕母」代理。為了避免增加社區成本,成長遲緩的嬰兒、年紀過大的老人、第三次犯錯的犯人,都要被「解放」──也就是安樂死。
這裡崇尚一致性,避談個人特質,以免凸顯差異。因此周遭不需色彩,每個人也喪失色彩辨識能力,每家每戶住同樣的房子,用同樣的家具,吃分配的食物,過著單調一致的生活。
唯恐居民判斷力不足,做了錯誤的選擇,長老會還為大家決定人生的伴侶、一生的工作,為每個家庭分配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只有八歲到十二歲的孩子可以選擇自己想要擔任的義工,享受自由選擇的快樂,並藉以讓長老了解每個孩子的性向和能力,然後在十二歲的慶典中,每個孩子就會知道自己被派任的工作。
書中主角喬納思在「十二歲的慶典」裡,被指派擔任「記憶傳承人」的職務。這是一項備受尊崇的工作,只有最聰明、最有智慧和勇氣超強的人,才可能中選。在「上級指導員」──現任記憶傳承人的帶領下,喬納思一點一滴的領略:過去的世代裡,所有的東西都有顏色,生活中處處有選擇,有冒險的快樂,也有溫馨的情與愛;當然也有殘酷的戰爭,病、傷、飢餓的痛楚,以及使人心碎的生離死別。而這些,在他十二歲生日以前不曾經歷過;甚至整個社區除了記憶傳承人之外,也無人知曉。所以他們需要像他這樣的人來傳承過去的經驗,以便在適當的時機,給予大家智慧的建言。
喬納思在接收記憶的過程中,經驗了過去家庭組成方式特有的溫馨、關愛,享受了色彩繽紛的喜悅,也經歷了戰爭嚴酷的傷痛,他這才發現:在自己所處的烏托邦社會裡,雖然不用擔心沒工作,甚至不用擔心身體不適,但是,單調、沒有變化、沒有選擇權的生活竟是如此的無趣。
他慢慢體會到現今的社區缺乏真愛,逐步認清社區制度不合理與嚴重缺失:人與人之間過度冷淡,缺乏對人類最基本的憐惜和對個人差異的尊重;於是他最後決定逃亡。因為現任記憶傳承人曾經說過:記憶傳承人一旦離開,所有的記憶就會重回社區成員的身上,讓大家體會人與人間的差異性,並能運用判斷力獲得選擇權的快樂。
在本書的最後兩個章節裡,作者描繪了喬納思身心受到飢餓、恐懼、寒冷的煎熬,以及逐漸步入另一社區的喜悅,卻沒有明確點出喬納思的逃亡行動是否成功,而是以喬納思彷彿看見聖誕佳節闔家團聚的溫馨情境,留下了一個讓讀者思考、臆測的空間。因而這本雖然沒有感官刺激,卻被公認為最能激發閱讀興趣的寓言小說,在美國出版後,旋即引起孩子們的熱烈討論。到底喬納思是否抵達了另一個他所嚮往的社區?或一切只是他臨終前的幻想?學校的老師也很喜歡在課堂上讓學生討論書中想要傳達的價值觀、探討社會的各種形式,並藉以引導孩子尊重歷史、珍惜眼前所擁有的一切。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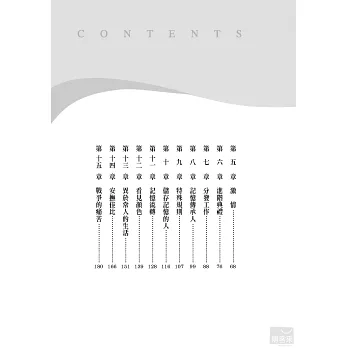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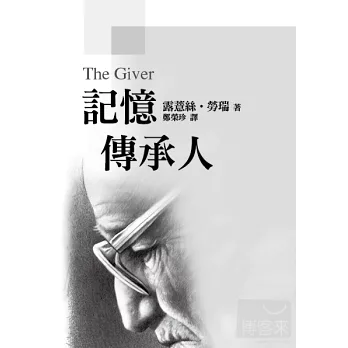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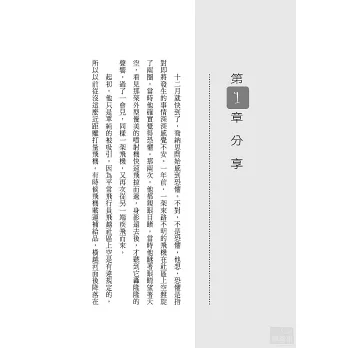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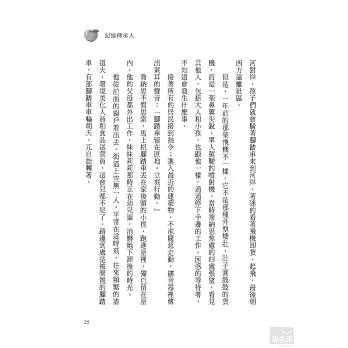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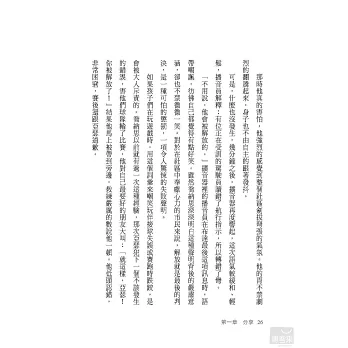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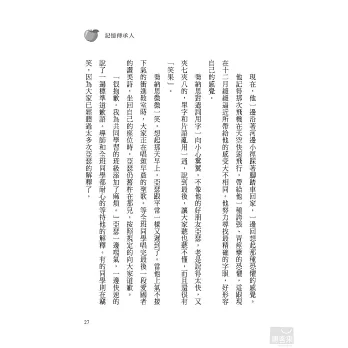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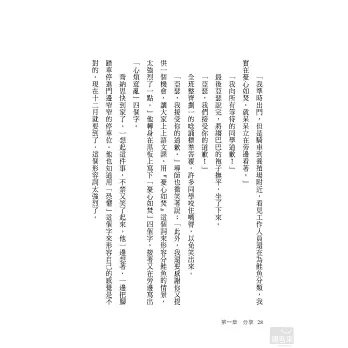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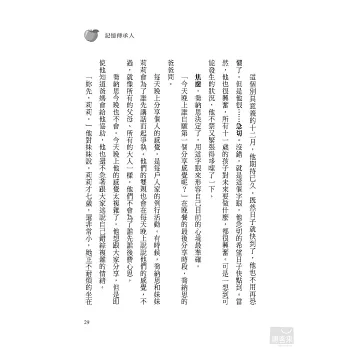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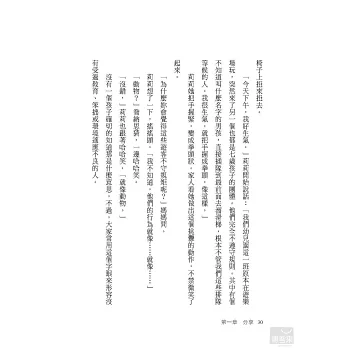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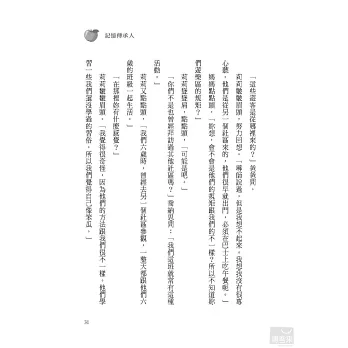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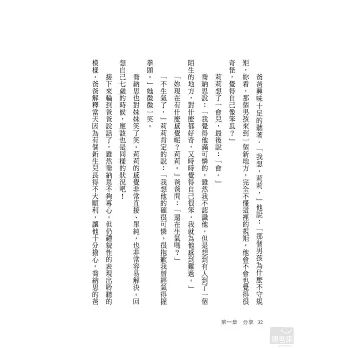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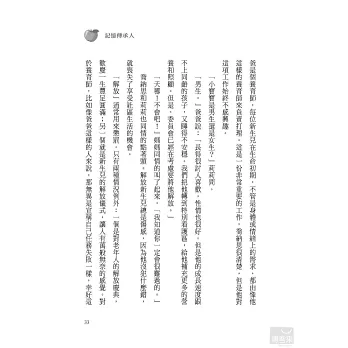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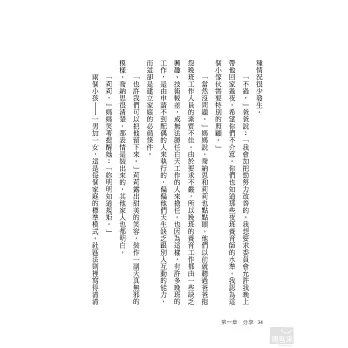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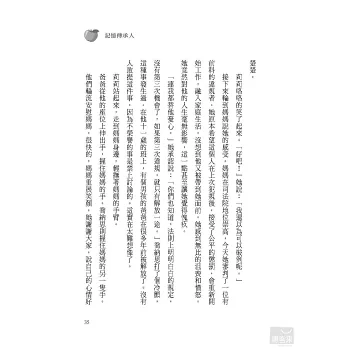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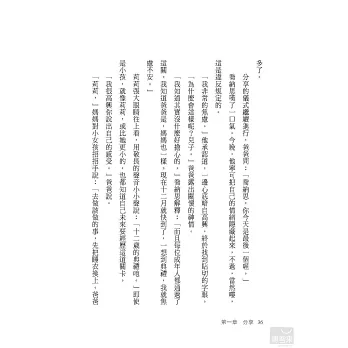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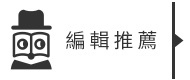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