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介紹一位新一代的歷史學者
我第一次遇見紀祥是二○○○年的一個八月天,地點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咖啡廳。那次我專門到台灣去開漢學會議,想順便認識一些新朋友,所以熊秉真教授特地把紀祥請來─那天老朋友王德威教授和王璦玲博士等人也在場。記得,我們每個人都叫了一杯冰咖啡,就天南地北地聊起來了。我正巧坐在紀祥的身旁,就開門見山地問到:
「李教授,你平常除了教書之外,還有什麼嗜好?」
「啊」,他微笑道,似乎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我的嗜好就是咖啡和寫作……。」
他的回答頓時令我感到驚奇,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專攻歷史的傑出學者;在我印象中,一般的歷史學者都不會如此回答。然而,也正因為他這個不尋常的答覆,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發現,他的文學功力很深,頗有「文人」的氣質。在短短的兩個鐘頭之內,我們從明末陳子龍談到吳梅村,再從清朝的文人袁枚談到龔自珍。我們同時也互相交換了個人讀書和寫作的心得和計畫,覺得許久以來已經沒碰過這樣有「趣」的學者了。
紀祥的「趣味」使我想起了晚明文人所提倡的風氣─那是一種「才」和「趣」融合在一起的非功利的人生品味。張潮就曾在他的《幽夢影》一書中說過:「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意思是說,一個人的才華一定要兼有率真的「趣味」才能達到「化」的高境界。
另一方面,我發現,紀祥對咖啡和寫作的愛好幾近於「癡」。我告訴他,這樣的偏好也很有晚明的特質,因為當時的文人相信,唯其有「癡」,一個人才有真性情。張岱曾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其實那個「癖」字也是「癡」的意思。因此,我提醒紀祥,他既然對寫作有那麼大的興趣,就必須努力堅持下去。有很多人以為研究歷史就不能從事寫作,但我認為那是錯誤的想法。能用生動的筆調把歷史再現出來,並能寫得引人入勝,才是高明的歷史家,我特別舉出我的耶魯同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作為範例。
不久之後,我和紀祥成了筆友,也隨時交換寫作的成果。第二年春天我們又一同在加州史丹佛大學開過一次學術會議。散會後幾天,我就接到了他的來信:
「會議結束後,一個人在舊金山又留了三天,天天喝咖啡,看來往行人,寫行遠筆記;街邊也喝,陽光下更是不能少,晃到海邊,遙遙對著惡魔島、天使島,也不能不喝;喝了就可思可想可念,懶洋洋的筆下,隨著年紀,天空的藍也多層次起來...... 望著天使島,竟不知不覺想起您文章中已表出的華人華工華史,中間已是多少映照……。」
後來紀祥轉往佛光大學執教,在學術上進了另一個階段。接著,他又來了一封信:
「今紀祥已至宜蘭,小朝在山,心可以遠,意可以收,可以望海,可以依山,可以細思量…… 於是知人之生命經歷,皆是文章筆下自返而原心之運動……。」
這些年來,我發現紀祥是我所認識的新一代歷史學者中比較富有文人氣息的人。我特別欣賞他把學問和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態度。他曾說:「無論是那一門學問,如果與自家不貼切,也終是枉然」;「唯有生命的『躍出』自己,才能『呈示』自己,才能在大化與時間的遷逝之流中,繼續領略文字與書寫。」此外,他在信中時常談到歷史形上學,也談到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不但有議論,而且字裡行間總是充滿了詩意。我特別喜歡他這種富有「詩意」的人生觀─對他來說,詩即人生,人生即詩。但他絕不是一個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的人,他廣泛涉獵,充滿了好奇;而且對於所讀到的新理論和形象思維,總是設法用自己的語言再現出來。他有關這一方面的想法,有時流露在學術文章裡頭,有時流露在信件中。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我一向精讀海德格(Heidegger)、呂格爾(Paul Ricoeur)、托多洛夫(Todorov)、傅柯(Foucault)、高達美(Gadamer)、哈伯瑪斯(Harbermas)等人的作品,總覺得這些理論大師的聲音有如磁鐵一般地吸引著我。現在看見新一代的歷史學者李紀祥居然能用一種富有詩意的語言把這些理論和生命銜接在一起,怎麼不令我感到興奮呢?
在紀祥著手撰寫《時間.歷史.敘事》這本書的那段期間,我有幸先看過其中的幾章,因而特別感到欣慰。我認為,他書中的章節,不管是內涵或形式都相當突出,為歷史的「書寫」寫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其中他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歷史敘述」和「文學敘述」的關聯作出了深刻的探討,此外還把傳統意義上所謂史實之「真、假」進行了令人十分信服的「解構」。記得當初剛接到〈趙氏孤兒的「史」與「劇」〉那一章時,我就衷心佩服紀祥的功力,覺得那是重新檢視「歷史」定義的一篇難得的佳作。這篇文章主要在討論歷史上「趙氏孤兒」的故事之演變,全篇寫得十分生動而有趣。原來根據《左傳》的記載,這個故事本來只是有關趙氏家族由於私通亂離而產生的流血事件。一直到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該主題才漸漸涉及趙氏孤兒的復仇故事。但最後真正把焦點變成「趙氏孤兒」,而又開始關注女性角色趙莊姬者,卻是元代的劇作家紀君祥。可以說,「趙氏孤兒」的故事後來之所以在中國民間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實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劇本不斷被搬上舞台一事息息相關。(請注意,這裡存在著一個有趣的巧合─李紀祥的名字與元代劇作家紀君祥頗為相似。)重要的是,紀祥在此利用了「趙氏孤兒」的故事演變來說明歷史「真相」的無法捕捉─事實上,任何敘述都是一種更動,一種新的解釋。即使作為第一個「文本」,《左傳》並不一定比《史記》來得更接近歷史真相。所以,其關鍵「並不是史實真假的問題,而是本事與新編的對待」。換言之,既然歷史都是由人一再敘述出來的,它已經無所謂真假了,歷史本來就充滿了某種「詩性」。
我認為紀祥的書中所處理的主題就是今日西方文學批評界裡最為關切的「representation」(再現)和「performance」(演述)的問題。
本來,「再現」和「演述」既然都涉及到語言的敘述,它們就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歧異和「漏洞」(gap)。據著名文學批評家米歇爾(W. J. T.Mitchell)所說,這種「漏洞」其實說穿了就是所謂的「文學」。
在這裡,我必須強調的是:紀祥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把這種充滿「漏洞」的文學敘述性推廣到歷史的研究領域中,而這也就是他撰寫這本《時間. 歷史. 敘事》的主要目的。有趣的是,這本書的緣起涉及到作者個人的一種「困惑」,一種對歷史研究本身的困惑。於是他就把書寫本書的經驗形容為一個「惑史的心路之旅」,他希望他的書能終究「貫穿其間之『惑』,撐開來說其所惑之世界。」
紀祥以「不惑」之年而能進行他的「惑史」之旅,也算是性情中人了。盼望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也能以充滿情趣的心懷欣賞本書中的言外之旨。是為序。
孫康宜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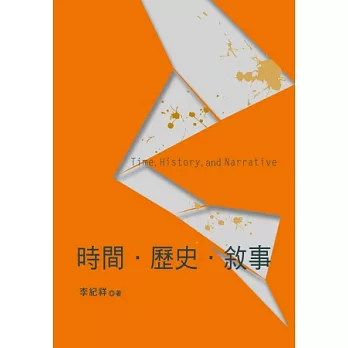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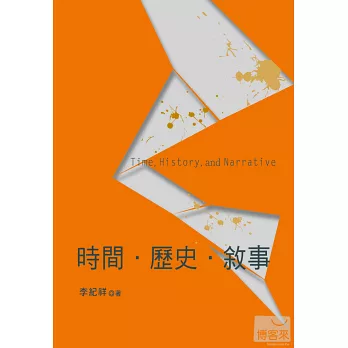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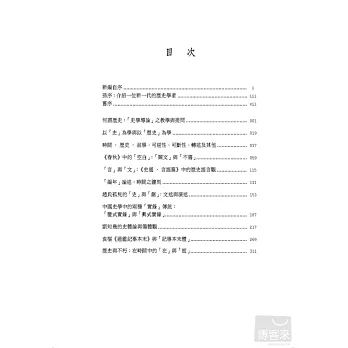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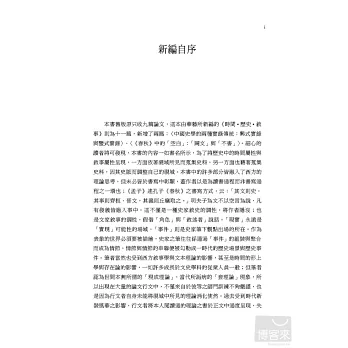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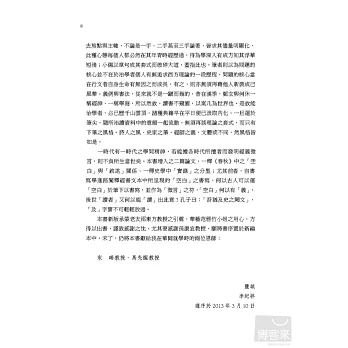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