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八年一月,當我接到來自華盛頓特區一位世界銀行高級官員的電話,讓我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我正在休寒假,忙於準備下一學期的教學和各種經濟政策問題的研究。這通電話讓我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沒有讓我覺得特別驚訝,因為在兩個月前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訪問中國時,我與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會談了一個半小時,比計畫的時間長了一個小時。這不算是一個正式的工作面談,至少在當時不像。我們會談的目的原本只是探討中國的通貨膨脹、收入差距擴大、農村發展等國內議題。伴隨著他好奇、禮貌和關注的眼神的驅使,我們的討論逐漸深入到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取得更具包容性的成長和減少貧困的途徑、外國援助和多邊組織潛在的作用,以及其他許多問題。會談結束時,我送了他一本一年前我在劍橋大學擔任馬歇爾講座的演講集。這本演講集總結了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與轉型問題的研究。
一份有趣的工作
世界銀行提供的這份工作既令人興奮又讓人倍感壓力。我被邀請去世銀任職是一個特別的機會,也是時代變遷的標誌。世界銀行自一九四四年成立以來,第一次邀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國民擔任其首席經濟學家,引導世銀在知識方面的領導作用,並制定其經濟研究議程。為了迎接經濟發展的挑戰,世銀必須進行改變。為了有效地發揮作用,世銀必須把其財力與想法、知識結合起來。我將擔任的負責發展經濟學的副總裁一職,是透過向世界銀行以及更廣泛的發展經濟學界提供知識方面的指導與分析服務,來增進對經濟發展政策和項目的理解。其目標是提高世界銀行的營運效率,滿足成員國對優質服務的需求。
但是對我而言,要放棄我正在從事的令人興奮的教學研究工作,即便只是暫時的,也不容易。作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與創始主任,我已經在此工作了十五年。這些年來,我與許多學生、同事及朋友建立了緊密且富有成果的關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我的幫助下開始探索引人入勝的研究問題。此外,在完成了芝加哥大學的四年博士學習和耶魯大學的一年博士後研究,並於一九八七年回國之後,我也曾積極深入參與中國的經濟政策討論。中國經濟的成功既使我感到驕傲,也成為我研究興趣的來源。我渴望繼續致力於研究中國所面臨的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在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預言艱難時世即將來臨的情況下,留在國內參與論戰並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還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
於此同時,世銀向我提供了一個一生難得的機會,從許多不同方面去研究發展問題,還可以就成長與減貧策略展開全球對話。該職位的職責包括:透過提供知識來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做出更明智的政策選擇,以加速減貧與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進展。過去許多年來,這些知識也用於向全球的公共宣傳活動提供資訊。這些知識的產生則涉及研究、數據收集、分析、全球監測、預測、統計能力建設以及政策評論與建議。
負責發展經濟學的副總裁的工作包括了所有這些方面、資助世界銀行其他部門的研究項目、提供旗艦研究報告,並為國際發展以及該領域的兩份頂級學術期刊設定研究議程。該部門有許多幕僚是世界知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都是該領域最受人尊敬的學者: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斯丹利.費希爾(Stanley Fisher)、安妮.克魯格(Anne O. Krueger)、霍利斯.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邁克爾.布魯諾(Michael Bruno)、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 Stern)勳爵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緊隨這些人的腳步是一種偉大的榮譽,也是一份艱鉅的責任。
自我童年開始,我人生的追求就是幫助各國實現持續的動態成長,以消除貧困和實現繁榮。我明白加入世界銀行將讓我有機會與其他許多人分享我在這個主題上的見解,承擔雄心勃勃的研究項目去考察在經濟發展中尚未解決的挑戰,並揭示貧困地區經濟起飛或發展滯後的原因。
這確實是一份我無法拒絕的有趣工作。我申請一週的時間以考慮在華盛頓工作對我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的意義。同時,從北京大學離職並為我的博士生和繼任者做出安排也需要時間。我已經準備好接受挑戰。
在非洲勾起的奇特童年記憶
二○○八年六月,我任職一週後就飛往南非、盧安達和衣索比亞。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去非洲大陸,但在很多方面,這的確是一次開創性的旅行。我的第一次正式訪問為什麼不去拉脫維亞、墨西哥或者尼泊爾呢?
為什麼是非洲?或許是因為我將這片大陸看做是發展經濟學的最後前沿─新知識與新的解決方案可以產生最大回報的地方。由於總體經濟政策大獲改善、大宗商品價格提高,以及國際援助、資本流動和匯款的大幅增加,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經濟成長率從二○○○年的三.一%加速到二○○七年的六.一%。同樣,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已經從一九九六至二○○一年的每年○.七%增加到二○○二至二○○八年的每年二.七%。非洲人口每天不足一.二五美元生活費的比例已經從一九九六年的五八%下降到二○○五年的五○%。致命疾病(如愛滋病)的患病率已經穩定,甚至在某些國家出現了下降。六○%的兒童可以完成小學教育,許多國家的兒童死亡率也在下降中。
不同背景的發展機構、學術機構和主要經濟學家所做的新一波實證研究甚至表明,某些非洲經濟體正臨近前所未有的起飛階段。在過去二十年間,許多國家強勁的經濟表現與反彈並非偶然,而是它們持續努力的必然結果。至少有五個根本性的變化正在發揮作用:更民主和更負責任的政府;更明智的經濟政策;債務危機的結束;與捐贈國的關係持續改善;新技術的擴散;以及新一代的政策制定者、行動家和商界領袖的湧現(Radelet, 2010)。此外,安全形勢也在改善之中。1
誠然,發展的挑戰仍然是巨大的。許多非洲國家自獨立以來表現出的結構轉型跡象仍然非常有限,反映了其緩慢的經濟進步。一九六○年該地區主體是農村,農業大約佔GDP的四○%和勞動力的八五%。雖然農村人口比例在過去五十年間穩步下落,但在二○○○年仍然達到六三%,明顯高於世界其他地區。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指出:「經濟成長沒有伴隨著就業的增加,特別是每年有七百萬至一千萬非洲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更加惡化了問題。技能的不足阻礙了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以及非洲企業家的機會,尤其是女性,由於在獲取足夠的資訊、創新和工具等方面受到限制,因而難以創辦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因為高度依賴雨養農業,非洲很容易受到諸如加速沙漠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更頻繁的旱災等極端天氣的影響。非洲可能是氣候變遷受害最嚴重的大陸。基礎設施服務仍然無法為窮人所享受─學校老師經常缺勤,資金往往也難以到達一線服務提供者手中。」
非洲大陸在政府治理指標上表現也不好,在交通、道路、水、電信和能源上的大量赤字,導致基礎設施發展滯後。由於非洲大陸的基礎設施不足和企業管制,私人投資平均只佔GDP的一五%。非洲在全球出口中的市佔率從二○世紀七○年代的三.五%下降到現在的一.五%。此外,緊隨二○○八年糧食和燃料價格危機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也給來之不易的發展進步帶來威脅。然而,我仍然覺得有理由對非洲經濟的未來持樂觀態度。我有一種預感,只要能尋找到解決目前複雜困難的辦法,希望就會到來,而且也許只要稍微推動一下良好政策的實施,就能帶來像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那樣積極的效果。
我開始我的南非實地考察旅行,目的是去參加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從事發展問題的學術與政策研究人員齊聚一堂。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為這次會議揭幕,大約有八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參加。我根據我的馬歇爾講座,在開普敦大學做了一次演講。我認為,減少貧困、實現動態的包容性成長的最好辦法,是把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作為其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這會使得經濟體最具競爭力,且為窮人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南非財政部長特雷弗.曼紐爾(Trevor Manuel)主持了會議,對我的演講做了評論,並成為我的朋友支持我。
之後我去了盧安達,考察該國經濟成長潛力的限制與機會,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在東部省分,我參觀了農業合營、蘑菇生產與技術推廣的農民合作社。我還會見了一些政府官員,包括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一位嚴肅的前軍官,身材高大、舉止平靜、聲音洪亮。我們討論了盧安達的農業現代化,特別是灌溉問題。我認為雖然動員國際資金與捐助興建小水壩很重要,但是動員每個農民利用非農忙季節在他們的家庭農場附近自建小池塘,來收集雨水同樣也很重要。他們可以購買小型柴油機或電泵機抽取地下水,變雨養農業為灌溉農業。從裝配和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國家可以生產泵機來服務農村市場。總統對這個簡單的建議很感興趣。他大概想到了一句非洲諺語:「殺死一隻蝸牛不需要使用劍。」其精髓很類似一句中國諺語:「殺雞焉用宰牛刀。」
在衣索比亞,我最初幾天是在拿撒勒和裂谷地區度過的,我在這裡舉辦了研討會,與農業推廣人員和女性農民展開討論,並訪問了出口農業與合作聯盟的成員。在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衣索比亞首都)我見到了商界領袖、學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我還會見了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另一位思維敏捷、求知欲旺盛的前軍事領導人。
在我們三個小時的集體研討會前,我已經收集了在海外生產並在當地商店出售的一系列簡單普通物品,其中包括尼泊爾生產的一盒火柴和中國製造的一個塑膠電開關,以及其他簡單物品。在討論了諸如:通貨膨脹和平衡國際收支逆差等總體經濟穩定問題並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後,我向他展示了我在當地市場購買的物品,問他為什麼衣索比亞─一個大約有八千五百萬居民並具有古老而又成熟的商業傳統,在其悠久的歷史中抵禦了各種各樣的外國侵略,卻從未被任何外國勢力取得殖民統治的值得驕傲的國家─到二十一世紀仍然需要進口這樣簡單的輕工業產品,包括來自尼泊爾,一個貧窮內陸小國的火柴?至於「中國製造」的產品,幾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和技術,但仍然被衣索比亞進口。我指出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很自豪地看到我們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中佔據支配地位,即使是非常基本的商品。但作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以及作為一個關心衣索比亞減貧事業的世界公民,我對這些進口產品所代表的許多寶貴機遇的錯失感到困惑。
除了使經濟體損失大筆可以用來購買至關重要的資本品、新技術或尖端藥品的外匯之外,這個國家的發展策略導致了更高的就業不足與更嚴重的貧困。我建議政府除了努力促進出口外,還要鼓勵替代進口品的簡單工業製成品產業。這樣做的潛在收益是顯而易見的:從進口替代中獲得的外匯節約與從出口促進中賺取的外匯會產生同樣的效果。此外,進口替代產業將為窮人創造就業機會,並為更進一步的工業發展訓練企業家。關鍵在於設計並推出一種策略,避免政府介入與衣索比亞比較優勢不一致的產業而浪費公帑,這種產業不具有競爭力和自生能力,並且代價高昂。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這三個非洲國家旅行,到處都可以看到我童年所看到的畫面。農民非常渴望改善他們現在的生活,並為他們的孩子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這讓我深受感動。他們的眼睛讓我想起了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在台灣所看到的農民,以及一九七九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時所看到的農民。在訪問這些遙遠的地方時,我似乎有一種回到了我的祖國那個年代的奇特感覺。給我印象最深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國家領導人對他們國家未來的信心,以及對理解和學習其他國家經驗的渴望,還有年輕的從業者、學者、學生和商人對知識的熱切和渴望。他們每天所面對的困難似乎並沒有減少他們共創美好未來的熱情和信念。
盧安達、衣索比亞甚至南非從某些方面來說,在它們當前的經濟與社會政治生活中都帶有一種古老的亞洲味道:人口密度、傳統農業、弱小的工業部門、普遍貧困、強有力的政府以及穩定的社會,和到處都是勤勞的人民,正如上一代的東亞一樣。
在非洲之外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在接下來的年月裡我去了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讓我想起了幾十年前的亞洲,當他們與貧困、低效治理和微薄的能力對抗的時候,被許多頂級經濟學家認為是毫無希望的。是的,我總有一種似乎回到了童年的奇特感覺。那打動我的一幕幕場景,積極而樂觀的人民,還有與不同的發展利益相關者的多次交流,這些都讓我堅信:透過良好的理念、正確的發展策略以及一些金融手段,這些窮國在未來幾十年將能實現亞洲式的經濟成長,成為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透過與政策制定者們的交談,我很快發現我的責任就是借鑑世界歷史與其他國家的政策經驗,利用經濟分析幫助他們制定出充分考慮他們的願景、優勢、限制和目標的合適策略。
擁有堅定信念與謙卑,這必須認識到每個地方環境與發展潛力的差異性。正如歐洲、拉丁美洲或亞洲一樣,非洲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多樣化的大陸,有超過五十個不同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優點和缺點。著手經濟發展的政策制定者們應該記住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九八五年對迦納總統傑瑞.羅林斯(Jerry Rowlings)所說的話:「請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如果說中國有什麼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畫。」(Zoellick, 2010)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
為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策略勾畫出一個路線圖。
這本書回顧了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總裁四年中的經驗、觀察和所思所想,並以淺顯的語言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理論和政策思考。原文以英文寫成,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二○一二年九月初在全球出版發行。中文版則由華中科技大學的張建華教授主持翻譯,分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對張建華教授和北大出版社與台灣時報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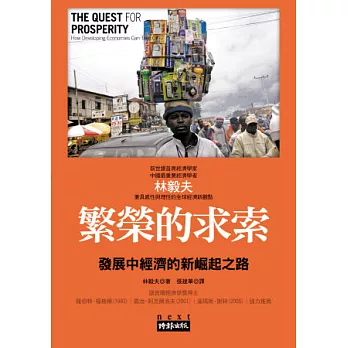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