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人自1983年大學畢業,正式從事翻譯工作以來,已經三十年了。在此之前,在大學期間(1979-1983),就對翻譯產生了濃厚興趣,翻譯了不少短篇小說和詩歌,屢屢投稿,屢屢不中,直接「打擊」的對象就是當時在譯壇中位居高位的《世界文學》。大約是我的持之以恆感動了他們,在讀研究所(1986-1989)期間,他們寄來一篇美國小說原文,標題是“Theory of Sets”,囑我試譯,我就試了。這是我有史以來發表的第一篇翻譯小說,即《組合之道》,登在1987年《世界文學》的第四還是第五期上,我已經不記得了。
1991年4月,我辭去武漢大學教職,去澳大利亞墨爾本讀博士,把剛剛譯完的《女太監》交稿,就離開了。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其間以口筆譯為生,陸陸續續地出版了幾十本譯著,還從事英漢雙語的詩歌、小說和非小說寫作,前前後後加起來,等於是在兩種語言裡摸爬滾打了小半輩子。
我所譯書的內容,範圍相對較廣,有小說、詩歌、戲劇、雜文、遊記、藝術評論、文學評論、醫學文獻、商業文件……等,又因我還從事口譯,涉及法庭、警事、政界、醫院、學校、工廠、公司等幾乎應有盡有的領域,說我龐雜紛亂,一點也不過分。我以自己為例,向學翻譯的學生指出,要翻譯必須有字典,因此工具書極為重要,是翻譯成功的關鍵之一,本人長期收集的各種字典就不下百部。
要從這樣一個龐雜紛亂的翻譯生涯中,整理出一個清楚的頭緒來,真是談何容易。我曾想完整地寫一本談翻譯的理論著作,但翻譯工作本身把我的念頭時時打斷,令我難以為繼。我也曾想系統地寫一本翻譯的經驗之談,但苦於找不到寬裕的時間和持續不斷的能量,也沒有一種合適的文體供我發力。直到最近幾年看古人的筆記小說,忽然發現,這種前現代的東西,反而
具有後現代的魅力,似乎特別適合我們這個「車」馬倥傯、時間被生活肢解得七零八碎的時代。
自此,我開始寫作《譯心雕蟲》,逐日遞進,有感而發,所有譯例無不來自我的數十本翻譯筆記(每譯一書,必做筆記),我的日常翻譯工作和我在翻譯教學,廣泛閱讀對比譯作譯著,大量流覽翻譯史書等中所獲的心得體會。我發現,沒有什麼比筆記小說這個文學樣式更能全方位、多角度、多向度、多層次地沿著縱深和細節的脈絡,表現、描述、記錄我日常流程中的「多」孔之見,儘管筆記小說的「小說」二字令我鬱悶煩惱,畢竟我不是在面壁面「屏」虛構編造,而是如實求是地在翻譯的雕蟲小技中一筆不苟地翻譯。也許,把這種寫法叫做筆記非小說更合適。
實際上,我從1999年寫到2007年才發表的一本英文著作,On the Smell of an Oily Rag: Speaking English, Thinking Chinese and Living Australian(《油抹布的氣味:說英語,想中文,過澳大利亞生活》)就給我提供了第一次杜撰這樣一個新詞的機會,而且是在英文裡,即“pen-notes nonfiction”(筆記非小說),儘管英文中連“pen-notes fiction”(筆記小說)這個詞根本就不存在。該書出版後,我開始嘗試用中文來入侵改造這個文體。《譯心雕蟲》一書,就是一個見證。
長期的翻譯實踐使我意識到,任何一種翻譯理論都不能全面而又精微地概括,甚至不能有效地描述翻譯中的博大精深或細緻入微處,關鍵問題在於,從事翻譯理論工作的人,往往是拙劣的譯者,甚至是不從事翻譯的太監,而譯者中的達人,又極少關注理論,甚至置理論於不顧,兩者的關係,不是互相掣肘,就是井不犯河,導致在翻譯理論和實踐中少有建樹。比如,以我所見,在英譯漢和漢譯英這個領域,本應建立一系列新型學科,如比較翻譯學、翻譯文化學、翻譯心理學、翻譯語言學、口筆譯比較翻譯學、自譯學、創譯學,等。惜乎譯界目光短淺,以錢為綱,以翻譯字數的持續添零為生活之鵠的,導致新學科一片荒蕪,字數達標超標者歷歷在目,比比皆是,真正的明眼達人屈指可數。
我無意僅憑《雕蟲》一書,就空穴來風,拔地而起地建立一門學科,如翻譯心理學,這樣的工作,需要長期、艱苦、踏實、專心、團隊結合地去做,但進行這樣的研究,實在很有必要。譯者接到文稿後,並不像一台翻譯機器那樣,從一端把文字餵入,另一端就會暫態地吐出結果。他∕她有思想、有感覺、有情緒,還有生活其間的日常大小事體和不斷演進的英漢雙語語言無時不刻地影響著他∕她,左右著他∕她,十年前譯同一本書,就跟十年後不一樣,心境不一樣,態度不一樣,連譯入語都不一樣。原文品質如何,也直接決定他∕她的譯文品質。這一點,可能很多譯者都有感受,只是沒有行諸筆端。我譯休斯《致命的海灘》,就覺譯筆生花,精神振奮,原因無非是原文本來就寫得大氣湯湯,揮灑自如。當然,這也與我是過了55歲之後才譯該書有著直接的關係。這又牽涉到翻譯比較學,比如,把譯者20歲的譯文,與其50歲後的譯文做個比較。又比如,把同一譯本的台灣譯文與大陸或香港譯文做個比較,都不是沒有重大意義的事。
再如翻譯文化學或翻譯地域學,個人認為,若譯澳大利亞文學作品,譯者必須身在澳洲,並必須在澳洲生活多年,而且必須使用澳大利亞字典,其他國家當以此類推,不如此,譯出的東西肯定不到位,如澳洲所用的“battler (s)”一詞,熟悉澳洲文化的,就會譯成「老百姓」(台灣譯者的漢語肯定不一樣,下同),又如澳洲的“digger (s)”,就不是「淘金工」,而是「子弟兵」,等等。
從技術層面講,任何單一的手段或技法,直譯也好,半直譯也好,音譯也好,意譯也好,反譯也好,創譯也好,甚至不譯也好,都不能完全解決翻譯這個全息問題,這裡面牽涉到學科專業用語(如不能以詩歌的語言翻譯數學或化學的語言翻譯小說),年代間隔久遠的語言(如難以用19世紀的漢語譯19世紀英文寫作的作品),以及漢英本身尚屬神秘,未被揭示的倒反結構和其他具有可探討規律性的東西。僅以文學為例,如僅用魯迅宣導的直譯,就會把譯文弄得面目全非,難以卒讀,還不如乾脆徑直閱讀原著。如不顧事實,一味求雅地按照嚴復的「信達雅」來翻譯,又會因求雅而失信,導致原味盡失,還是不如乾脆徑直閱讀原著。如像葛浩文和當代許多白人漢語英譯者(書中已有提到)那樣,看不懂就繞開不譯,隨意發揮,隨意改寫,把原文當成自己重新書寫的素材,那還是不如乾脆徑直閱讀原著。
所謂翻譯,是一個總體工程(total project),這是我自己發明的詞彙,它需要採取一系列綜合手段來重新整合,一個英文段落譯成中文(中文譯成英文也是一樣),很可能同時需要反譯、直譯、音譯、意譯,甚至創譯等多種手法來應對,這用中文的殊途同歸一詞還難以盡言,而需要用我自創的多途同歸一詞來表述,即通過各種技法的多種途徑,來達到臻於完美的譯文。
進而言之,除了掌握各種技法之外,譯者不可能不同時又是一個作者,譯詩的須是詩人,譯小說的須是小說家,譯散文的也須是散文家,而譯哲學的,又還須至少是個喜歡哲學的人。
話又說回來,這本書不是教科書,不是理論著作,更不是為了浪費讀者時間而設計的某種娛樂讀物,它只是我根據筆記小說再造的一個適合自己寫作的新文體:筆記非小說,以好玩的心情筆之,以認真的態度記之,並以播種的方式撒之。若能成就一項學科的建立,比如翻譯心理學或創譯學,那我要將已故母親說的那句「我將死不瞑目」的老話,稍微改成這句:我死也瞑目了。
斯為自序。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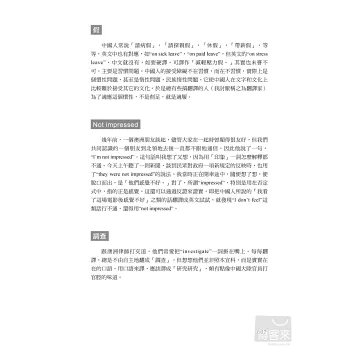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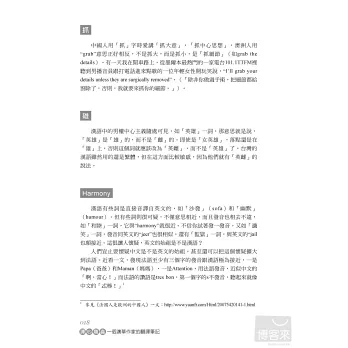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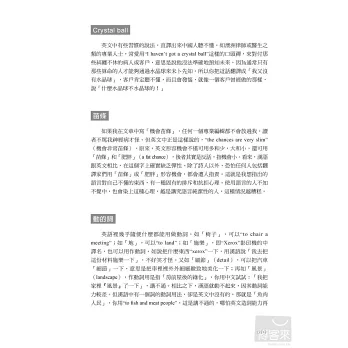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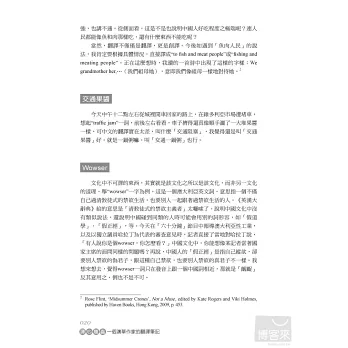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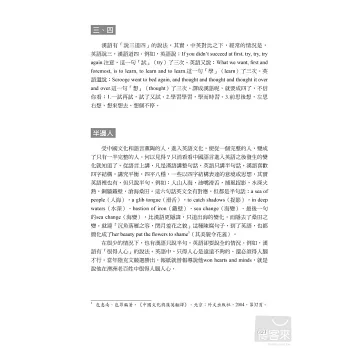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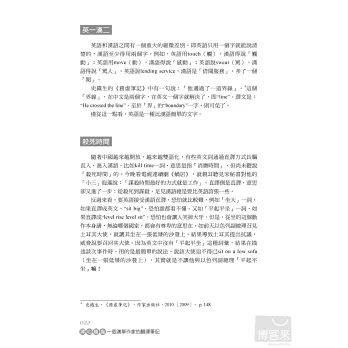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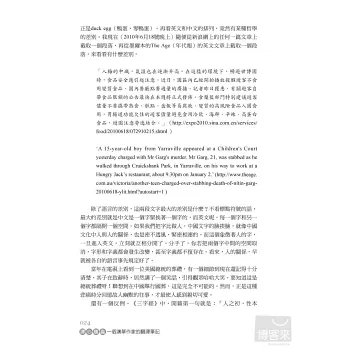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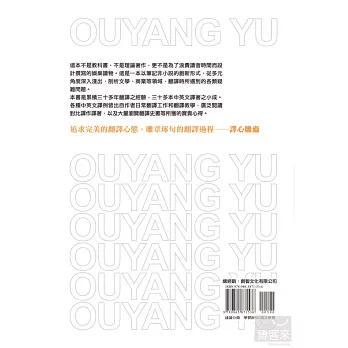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