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明銀教授序
若對博巴(藏族)的有識者詢問代表西藏的偉大思想家是誰時,幾乎不例外地立刻回答說:「薩.隆.宗.三(者)」(Sa gLong Tsong gsum)。也就是說,是薩迦派(Sa skya pa)的薩迦班支達(Sa skya Pa□□ita / Sa Pa□ Kun dga' rgyal mtshan 慶喜幢,1182-1251);寧瑪派(rNying ma pa)的隆欽饒絳巴.無垢光(gLong / kLong chen rab 'byams pa Dri med 'od zer / Tshul khrims blo gros戒慧,1308-1363);格魯派(dGe lugs pa)的宗喀巴.善慧名稱(bTsong / 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i dpal],1357-1419)三人。在藏族的心目中,這三位又是文殊菩薩的化身。這裡提到的宗喀巴在三人當中,是代表西藏特別重要的思想家。以後確立了達賴剌麻政權(1642),從格魯派內部產生達賴剌麻,乃至格魯派掌握政治、宗教上的實權,身為位居該頂點的思想中心人物,又加上政治上的支持與宣傳,宗喀巴被推舉到西藏最偉大的思想家之地位。
他是從十四世紀後半期到十五世紀初的人物,正當活躍於元朝滅亡明朝成立(1368),到達成祖永樂帝的期間(1402-1424)。在西藏從印度輸入的佛教,早已壓倒當地的樸素信仰,一般地廣為流傳,也經歷了九世紀的破佛及其後的復興與改革。然彼時代的佛教,漸漸再度導致淫靡之風習,是被稱作擁有懶惰凡庸僧眾的所謂舊教古派或半改革派。在此等佛教僧之中,如薩迦派法王援引蒙古族汗王與軍隊,進而掌握了西藏國土的主權。宗喀巴的出生是這主權崩潰之後的數年,帕木竹派(phag mo gru pa)的菩提幢(Byang chub rgyal mtshan,1302-1373)在1354年當上元的大司徒(Ta'I su tu),取代薩迦派同樣地掌握了政治的俗權之時(此即帕木竹派政權時代,1354-1641)。他幼年出家的佛教是如此的情況,及長越發了解其弊端,對此從正面堂堂的宣戰。也就是說,他對滔滔風靡世間的此墮落佛教,提倡嚴格的戒律生活、教團的獨身主義,如此終於樹立了新教改革派,所謂黃帽派(Zhwa ser ba)格魯派。因此,他身為宗教改革者常被比作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而加以介紹。
這宗教改革的事業,乃基於他的高尚人格與堅定的節操。誠如宗喀巴學修自傳詩云:「前期廣泛求學增知識,中期思化經論為教誨,後期日夜勤修實踐行,一切為教振興作迴向。」(《東北藏外目錄》,No.5275.Kha.52b6[52b4-55b1] )對我們而言,成就他的偉大性倒不如說是在於他的學者風範。其實自古至今,他是少見的學僧。比起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佛教國度的學僧,不僅無絲毫的遜色,能與他匹敵者亦寥寥無幾。他作為偉大的學者,當我們閱讀《菩提道次第論》與《了義未了義》等時,更能深切感到。再者,他的著作全集構成龐大的二十函(《北京版西藏大藏經》I.Ka-XX.wa),從其大部分是伴隨緻密的思索之學問著述亦能得知。他的思考方式與學風有邏輯、哲學上的正確性,甚至於時有科學的嚴謹性。例如:西藏譯大藏經中有中論釋的《無畏註》(Mula-madhyamaka-v□tti Akutobhaya只有西藏譯現存,北京版Vol.95,No.5229,pp.15-47,34a2-113b8),儘管自古以來它有被視為龍樹作之傳統,但是宗喀巴證明它是偽書而排斥之。如此否定《無畏註》,由其後的西藏佛教學僧全部加以繼承;而這些的學問態度與內容,總而言之,可以想像是印度的學問寺風尚大量地加以輸入、保存,且是藉由因明與問答辯證磨練了頭腦之賞賜品。儘管他繼承印度學風,卻達到了超越印度學僧的境地。十一世紀入藏的孟加拉人阿底峽(Atisa,982-1054)與十四世紀的西藏人布敦(Bu ston,1290-1364)等,都是著名的論師學僧,不過那些先前諸師的佛教學問,有如全部聚集、歸結給宗喀巴之感。這或許是因緣際會、時代造英雄吧!我們亦倣效奧伯米勒博士(E.Obermiller,1901-1935),應該稱之為「學僧(pa□□ita)宗喀巴」。
宗喀巴以阿底峽的噶當派(bKa ' gdams pa)教義作為佛教的正統,以復興此為目的。此同時在西藏亦意味著佛教改革。而且在阿底峽「經與咒」的合一是其根本態度。經與咒在宗喀巴依次是以《菩提道次第》(Lam rim)與《密宗道次第》(sNgags rim)的二大著作形態出現的。但是,同時這合一性,在《菩提道次第》的一論,其組織性亦可看出,蓋在論的最後簡單地附上當入密咒(《密宗道次第》)。這屬於顯教領域的《菩提道次第論》方面,是因明、阿毘達磨與律等的一切綜合,特別是將其主要力量放在中觀與瑜伽或文殊—龍樹與彌勒—無著的兩學系之統一綜合。即認為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站在如此的統一立場,是宗喀巴乃至格魯派的觀點。
如此《菩提道次第》的直接所依,是《菩提道燈論》。阿底峽的此一著作是由六十八頌構成的偈頌體,可以說是著者的主著之重要論書。《菩提道次第》則是詳細擴大它的。這在論初特別舉阿底峽及其《菩提道燈論》且禮敬之,該著者阿底峽及其著作《菩提道燈論》具有偉大性,故在此可以看出其態度在表白此《菩提道次第》就是正說。
然而更往上追溯時,此《道燈論》的教授即不外乎是《現觀莊嚴論》的教授(man ngag,upadesa),因此,說「故彼造者(至尊慈氏),亦即此之造者(阿底峽)。」從這樣的見解看來,現觀莊嚴論--菩提道燈論--菩提道次第論的一系列,正如宗喀巴本身以自己所相信的,是敘述無謬地傳承開顯同一正法的。
但是《菩提道次第》之成立理由及其基礎不是只有《現觀莊嚴論》。再者,不是只有現觀的、彌勒的法相。在那以上有依據中觀系統的思想。事實上,《菩提道次第論》的最重要的根幹之上士道(syes bu chen po'i lam),幾乎只有中觀者成為問題,可以說《菩提道次第》是站在中觀的立場(特別是月稱系統)。
如此地,《菩提道次第》在阿底峽方面也是如此,是站在中觀與彌勒之綜合的。此一事實從《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歸敬頌也能得知。即該歸敬頌,首先釋尊,其次彌勒與文殊,接著龍樹及無著,其次阿底峽,其次諸善知識,各以一偈表達敬禮。而且接著,「此中總攝一切佛語扼要,□攝龍樹無著二大車(shin rta chen po)之道軌。」(Byang chub lam rim che ba bzhugs so,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1992,p.3;法尊法師譯《菩提道次第廣論》,重慶,1936;repr.台北,華藏講堂,p.2)此不外乎是意指著,於此該攝有關般若經的二大車之宗教,即般若經之隱義與顯義。蓋西藏寺院的顯教學部之五學科,乃由
一、因明學-法稱的《釋量論》Dharmakirti,Prama□a-varttika。
二、般若學-彌勒的《現觀莊嚴論》Maitreya-natha,Abhisamayala□kara。
三、中觀學-月稱的《入中論》Candrakirti,Madhyamakavatara。
四、俱舍學-世親的《俱舍論》Vasubandhu,Abhidharma-kosa。
五、律 律-德光的《律經》Gu□aprabha,Vinaya-sutra。
所構成。這些在印度是比較後世的論師及其義學的佛教哲學之代表作。其中,第二的般若學當然是般若經之學,第三的中觀學亦宣說般若皆空,可以視為般若經系統的教學。因此,西藏佛教的教學可以說自始至終在般若學。事實上,對般若經的尊敬,比起別的經典更是絕對的。第二的彌勒《現觀莊嚴論》之般若學,被視為究明該般若經之「隱義」(sbas don,guptartha)的。而且那也是「道」,有關「悟入次第」的法相分類學。針對此,龍樹的《中論》及月稱對該中論的《入中論》之中觀學,是解明般若經之「顯義」(dngos bstan明說,mukhyopadesa)的。如此地,從般若經的隱顯表裡兩面全部加以學習的。此種觀點便是西藏佛教教義學的思想。也就是說,印度大乘佛教的兩大思潮之中觀與瑜伽行兩學派,於此是以般若經加以統一的。
綜合龍樹、無著,以阿底峽為所依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直接根據阿底峽以後的傳承,這在《廣論》的最後,由宗喀巴本身加以提及。即「謂依俄姓具慧般若(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譯《現觀莊嚴論》等)摩訶薩埵,彼之紹師精善三藏,正行法義,拔濟眾生,長養聖教,寶戒大師(dKon mchog tshul khrims),及因前代持律師中,眾所稱歎賈持調伏(Bya 'dul ba 'dzin pa,號精進然brTson 'grus 'bar,種敦巴的徒孫),彼之紹師智悲教證功德莊嚴,大雪山聚持律之中高勝如幢,第一律師嗉樸堪布寶吉祥賢(Zul phu ba dKon mchog dpal bzang po),並諸餘眾誠希求者,先曾屢勸。後因精善顯密眾典,珍愛三學,荷擔聖教無能倫比,善嫻二語大善知識,摩訶薩埵勝依祥賢(sKyabs mchog dpal bzang po)殷勤勸請。係從至尊勝士空諱(號虛空幢Nam mkha' rgyal mtshan),聞[阿]蘭若師(dGon pa ba,Ara□yaka,1016-1082,熱振寺第三任座主),傳內蘇巴(sNe'u zur pa,內鄔素巴,1042-1118)及慬哦瓦(sPyan snga ba,1038-1103)所傳道次。又從至尊勝士賢號(名法依賢Chos skyabs bzang po)聞博朵瓦(Po to ba,1031-1105)傳霞惹瓦(Sha ra ba,1070-1141)及博朵瓦傳授鐸巴(Dol pa,1059-1131)道次第等義。……以大譯師(具慧般若)及卓□巴父子(Gro lung pa yab sras即Chos kyi 'byung gnas法生與Chos kyi seng ge 法獅子,俱為十二世紀人)所著道次為本,並攝眾多道次要義,圓滿道分易於受持,次第安布無諸紊亂。雪山聚中闢道大轍,於無量教辯才無畏,如理正行經論深義,能發諸佛菩薩歡喜,最為希有摩訶薩埵,至尊勝士叡達瓦(Red mda' ba gZhon nu blo gros,號童慧Kumaramati,1349-1412)等,頂戴彼諸尊長足塵。」云云。(ibid. pp.812-813;法尊法師譯本,pp.559-560)以上,提到從虛空幢與法依賢二師傳持重要的兩個菩提道次第傳承,此二人對宗喀巴來說是重要的師父。虛空幢是宗喀巴最後之直接師父,他是洛札(lHo brag,雅隆地方)人,被稱為大成就者(grub chen),是屬於廣大行(唯識)、甚深見(中觀)的兩系譜之任一者,乃噶當派中教授派之傳人,但是達賴剌麻十四世認為他是寧瑪派人,有口傳(oral transmission),而且宗喀巴得自他的教說,很明顯的是基於寧瑪派大圓滿系統的獨特用語(Gyatso,Tenzin(Dalai Lama XIV)(1985),Kindness,Clarity,and Insight. New York:Snow Lion Publications,p.230)。後者法依賢為扎廓(Bra gor)寺堪布,為噶當派中教典派之傳人。宗喀巴對這兩位師父都有製作讚歌(《全集目錄》Ⅲ,10.繼此有法依賢的讚)。其中,阿蘭若師是阿底峽在康區(Khams)的弟子,從他到內鄔素巴的系統是屬於所謂廣大行派的道次第。再者,被稱作慬哦瓦者有數人,這裡提到的是種敦巴的弟子慬哦瓦(1038-1103,本名戒然Tshul khrims 'bar)。其次,博朵瓦到霞惹瓦是所謂甚深見的道次第,博朵瓦同樣是種敦巴的弟子。
宗喀巴四十六歲時(1402),在拉薩北方的熱振寺(Rwa sgreng)勝者寂靜處(阿蘭若)的新院(yong dgon)獅子崖下的山中(brag seng ge'i zhol gyi ri khrod)著《菩提道次第廣論》(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 □ che ba,以下略作《廣論》)。有名的三士道由阿底峽的噶當派所提倡,宗喀巴繼承之;在阿底峽之前的舊教寧瑪派(rNying ma pa),也有以聲聞.獨覺.菩薩的三乘為顯教,不過內容上稍微有異。上中下的三士顯示向菩提(覺)須要前進的修道階梯。下士道(skyes bu chung ba'i lam,adhama-puru□a)相當於所謂的人天乘,為了後世的安樂而修行。該內容是觀察死無常與惡趣苦。針對此,宣說須皈依三寶,思業果理與十善業道。其次,中士道(skyes bu 'bring gi lam,madhya-puru□a)相當於聲聞.獨覺,四聖諦中的苦諦與集諦成為主題(聲聞),與觀十二緣起的理法(獨覺),這裡宣說生死過患與厭離此世、業與煩惱,特別強調律儀戒等。以上二道[教]大乘未必厭惡或輕蔑,只是應根器被稱做下士、中士,故亦為大乘所承認,因此稱之為「共」的下士、中士。
與二乘不共的大乘獨自的教法之上士道(skyes bu chen po'i lam,uttama-puru□a),是全論的核心,菩薩的大乘道次第成為主題。大乘首先要發菩提心,在格魯派這發心與戒律及空觀一道被視為三大原理。其後進入大乘的一般學習。大乘菩薩學道的對象,於此收攝為六度(□a□-paramita)與四攝事(catvari-sa□graha-vastuni)。布施等的六度於此被視為自佛法成熟(sva-buddha-dharma-paripaka)的行(自利),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四攝事被視為有情成熟(para-sattva-paripaka)的行(利他)。以自成熟與他成熟稱呼自利.利他二行,為《菩薩地》與《經莊嚴》所熟悉,於此它被分配到六度與四攝事。上士道一旦結束,特別提出六波羅蜜中的最後禪定與般若加以強調。即禪定波羅蜜等於止(samatha)的修習,般若波羅蜜等於觀(vipasyana)的修習。《廣論》最高、最重要的部分是上士道,於此所修的六度中,觀(毘□舍那)的般若波羅蜜構成全論的核心,占有全體的約三分之一。止的學習與觀的學習各自進行,最後個別進行無效果,故強調止觀雙運(samatha- vipasyana-yuganaddha)。以上大乘學習的解說終了,最後略說金剛乘(密教),乃銜接另一部主著《密宗道次第廣論》(sNgags rim chen mo bzhugs so)。
如上,《廣論》的止(奢摩他),特別是觀(毘□舍那)的論述是樞要中的樞要。而且稱為「道次第」欲給與顯教的學習次第乃至該階梯,這一般可以看出其瑜伽行的性格。如前述者,彌勒的《現觀莊嚴論》於此仍舊是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也具有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性格。然而至此「觀」的修習,自始至終完全是中觀的空觀。論初雖只舉《現觀莊嚴論》的名稱,但是實際上是按照《入中論》宣說此毘□舍那的「觀」。即使一般地視為瑜伽行的,但是透過全論比起《現觀》,《瑜伽師地論》的引用甚多(計103回,長尾雅人著《西藏佛教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54;repr.1978,p.85)。
護法等在瑜伽唯識學派之進步思想,由玄奘引入了漢土,不過與之匹敵的中觀學派見解,特別是到了後來也把瑜伽唯識思想合併到自己之中的中觀思想,終於未被傳入漢土,以往完全不為所知。然而該後期中觀的傳統,針對否定與安立之根本態度、有與空的根本論爭點,有闡明中觀哲學如何發展(例如:瑜伽行中觀學派在後世很發達)的情形。要之,那些問題,歸結問題的重點於西藏佛教主張的自續派(Rang rgyud pa,Svatantrika)與應成派(Thal 'gyur ba,Prasa□gika)之抉擇。宗喀巴的教學,與漢傳相反地,這些不光是成為重要的課題,那些思潮之大體上在十五世紀以前的歷史,是直接、間接地能夠窺知的。如此的西藏佛教,不可能單單以西藏佛教的地方性意義來處理。它是要求從更廣泛地印度學的、或從佛學全體的立場之考察與斟酌的性質的。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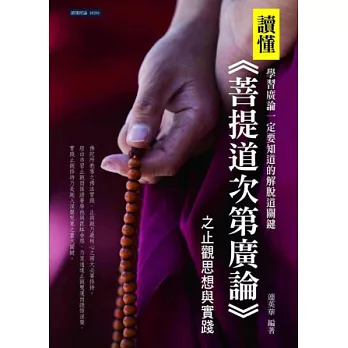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