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節錄)
一跤絆到邏輯外——談王爾德的《不可兒戲》(節錄) / 余光中
中文讀者裏面,不少人知道王爾德是《少奶奶的扇子》的作者,也有人看過他的《朵連‧格瑞的畫像》。可是他死後八十多年,論者幾乎一致推崇《不可兒戲》為他的代表傑作,或稱之為無瑕的喜劇,或譽之為無陷的笑劇(farce)。這部戲的情節和骨架,和十九世紀許多笑劇相近。溯其淵源,則同胞兄弟小時分散到快要結婚時又重逢的故事,早在泰倫斯和普洛特斯的羅馬喜劇裏已經有了。這種情節,莎士比亞在《錯中錯》和《第十二夜》裏也利用過。至於一位男子為了追求情人而假冒別人,因而鬧出笑話,就在英國也舉得出法克爾的《好逑計》、哥德斯密的《屈身求愛》和謝利丹的《情敵》等前例。
至於劇情的處理,則是採用所謂「善構劇」的手法,務求結構單純而多重複,發展緊湊,高潮迭起,危機四伏,誤會叢生,而如果人物的變化或情節的演進不夠機動,就乞援於再三的巧合,總之要一氣呵成,必使觀眾應接不暇,直到劇終才群疑盡釋,百結齊解。這些原是劇場的老套,如果作家技盡於此,就難掩機械化浮濫淺俗的毛病。例如在《不可兒戲》之中,兩位俏黠惑人的少女怎麼會同時立意一定要嫁給名叫任真的少年;勞小姐怎麼會粗心得誤置嬰孩和手稿;失嬰怎麼偏會給一位善心的富翁揀到;而最後,失散多年的兄弟怎麼偏就會在兩不知情之下成為好友;凡此種種,當然都經不起理性的分析。
這種巧合如果讓小說的讀者邊讀邊想,也許難以過關;但是對於臺下集體的觀眾,只要能夠聯串情節,帶動對話,根本無暇細究,反而覺得誤打誤撞,絕處逢生,熱鬧得十分有趣。千百人坐在劇院的陰影裏,凝神觀照燈光如幻的劇臺,最容易如柯立基所說「剎那之間欣然排除難以置信的心理」。劇中少女關多琳說得最好:「我對這件事疑問可多了,不過我有意把它掃開。目前不是賣弄德國懷疑論的時候。」千百人坐在臺下,期待的心情互相感染,什麼奇蹟都願意相信。在《不可兒戲》首演前夕,王爾德接受洛思的訪問。以下是訪問記的一段:
問:你認為批評家會懂大作嗎?
答:但願他們不會。
問:這是什麼樣的戲呢?
答:這齣戲瑣碎得十分精緻,像一個空想的水泡那麼嬌嫩,也有它自己的一套道理。
問:一套道理?
答:那就是,我們處理生活的一切瑣事應該認真,而處理生活的一切正事,應該帶著誠懇而仔細的瑣碎作風……第一幕很巧,第二幕很美,第三幕呢妙不可耐。
說穿了,這劇本根本沒有什麼主題或什麼哲學,也不存心要反映什麼社會現象。為了語妙天下,語驚臺下,他不惜扭曲常理,顛倒價值,至少在短短三小時內,把觀眾從常理和定規的統治下解脫出來,讓他們在空中飄遊一晚。巧合嗎?那原是藝術的特權呀。王爾德原就認定:不是藝術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藝術。劇中人物原就半真半幻,尤其是那些女人,在陽光之下絕不可能那麼反話胡說,而又胡說得那麼美妙,令人驚喜。才發現每一次驚是虛驚,喜是真喜。觀眾明知其假,卻正在興頭上,寧信其真。
有一次,一貴婦觀賞英國風景大師泰納的作品,提出異議,說他畫中的落日她從未見過。泰納答道:難道我們不願意落日像那樣嗎?李賀說過:「筆補造化天無功」。王爾德和泰納,也是這個意思。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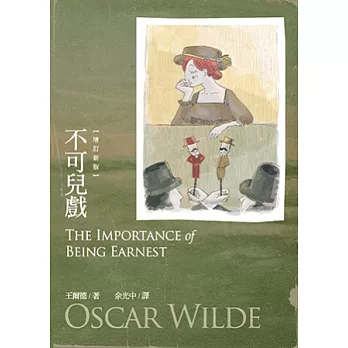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