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山居地圖》代序/張錯
前言
《山居地圖》是我的詩與散文的合集,出自2001年詩集《流浪地圖》及散文集《山居札記》。這兩本書的河童出版社是女詩人葉紅一手創辦的,自從她逝世後,事隔多年,讓我興起再版並且改正書中錯字的念頭。這次又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蘇氏兄弟俯允印行,以及張麗芳小姐協助,重新打字,重新校對,有如浴火鳳凰再世重生,十分高興。
披閱舊稿,前塵往事歷歷在目,有如過眼雲煙,然而雲煙又聚合歷久不散,我想這就是所謂滄桑吧。我與葉紅只一面之緣,不久即聞她在上海因憂鬱症的噩耗,多年來心中惆悵莫名,後來寫有散文〈葉紅花凋〉一篇,如今拿來代序,亦算是紀念故人的一番心意吧。
葉紅花凋
(一)
加州有一種日本小葉紅楓,秋天葉枯,春天葉紅,纖指秀麗,風姿綽約,其紅如血,因而頗見珍貴。小葉紅楓其樹不大,不若秋黃巨碩橡樹,巴掌大葉,風光處處,風過落葉遍地,雜亂無章,圓型果實更有刺如蝟,滴溜溜、毛茸茸,一不小心,指破血流。
小葉紅楓有小花,花季後,以葉取勝,由青變紅,轉眼間一樹紅葉,層層華蓋,有如彩雲疊疊,掩影依稀,無花勝有花。葉壽頗長,由春入夏,直至秋涼,方始枯黃萎落。以葉為花者,以此樹至勝。
南加州大學校園除了遍植乳白如蓮的木蘭花樹,還有一種我呼之為「紫燈籠」(Jack O' Lantern)的花樹。此樹入春,先聲奪人,先花後葉,有如無花果般先果後葉。一旦花成,但見滿樹紫氣繚繞、氤氳迷人,花落處,一朵朵有如盞盞小紫燈籠飄降,落花沾衣,黏人深情不放,令人神為之奪。然而花期不長,轉眼入夏,花落凋零,又是綠雲成蔭,恍似春夢一場。
小葉紅楓先葉後花,紫燈籠先花後葉,終是葉紅見勝,葉期悠長,春夏紅艷。
台灣有一個曇花一現的女詩人叫葉紅,數年前因憂鬱症自盡於上海。雖與她僅一面之緣,物傷其類,劫後傳述,至今仍有抑鬱不平處。今季小楓初紅,於紅葉處思葉紅,有無限感概。以葉代花的草木不多,除熱葉植物及仙人掌科外,就以小葉紅楓了。葉葉赤紅有如顆顆熾熱紅心,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朝朝夕夕,入世的投入,傷心的滴血,斑駁葉紅。
相知不深,但看來是個性情中人,覺得倒似先花後葉的紫燈籠,不喜煩文俗套,想開一樹的花,不喜在綠蔭下等待成長,有花就有樹,就有一樹華麗。
葉紅有詩名「相遇」,寫得很好,最後兩句為「希望遇上你/在遙遠的地方」。
所謂希望相遇,宛是一種亟念,也是一種渴切,更是一廂情願;近如在窗邊,遠如在渡頭,碰上就碰上,或永世不相遇,那就不相知。或許天可憐見,在一個細雨連綿、愁思如繭的日子裡,兩個同在天涯淪落的避雨者,命運線交織在一個屋簷底下,終於遇上了。可惜這種情境多是電影情節,並非真實人生。
按照基督教義,冥冥中天意安排,兩個人的一生,就只這一生,相遇相識,沒有來世,至是難得。按照釋家義理,那又是多少來世今生的緣份牽纏,多少的執著難捨,多少的年代謬誤錯過,多少的重覆等待追尋?最終方得在窗邊、渡頭、或簷下相遇?
然而一切的一切,無心勝有心,在一個遙遠的地方,遇上了。它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夢,一個高蹈理想,或甚至是,從末想到會碰到、或遇見的一個驚奇,及繼之而來的驚喜。
就是這種無所謂或一無所知的心情,人們像行旅者一般活在世上,千帆過盡,是也不是,均無所謂。也沒有什麼預設非得要發生的,或不發生的,或準備發生的。人生就是那麼一無所知,我們以為知道的都不是知道,以為不知道的比不知道更不知道。日復日,年復年,所謂青春,就是這樣一路追尋。
然而,心底依然是那種終極渴望,還是希望在能夠遇到,從近在眼前到遠在天邊。「你」,似乎並不那麼重要了。相遇,那才是生存意義的唯一。
(二)
我遇葉紅於2001年5月17日中壢。長談竟日,快慰生平。她送我兩本詩集,其中一本內題:「美即生命,活著真好」。
像倖存者的話,她應是在遙遠的地方,還在不斷一路追尋,只不過最後一次越界,樂而忘返,越走越遠,踏入人間見觸不到的境界。
幾乎已不在乎聽到或聽不到其他人的呼喊聲了,那是一片寧靜和平,沒有人間的虛偽欺詐、兇惡嘶叫。善良、坦率、而勇敢的人,葉紅即紅葉,在葉子最紅的時候自我飄落,輕輕的,不發出任何聲息。如果你遇見,正好。如果錯過,也無妨。
是的,似乎開始明白什麼叫「活著真好」,如果活在一種希亟,那是幸福。不斷努力,自希亟中尋求兌現。不斷希亟,不斷兌現。從每天早晨第一杯咖啡或茶、第一張早報開始、開工、閱讀、思考、寫作、授課、休息。然後又從另一個早晨另一杯咖啡或茶、另一張早報開始、開工、閱讀、思考、寫作、授課、休息。重覆每日活在當下,成為另一個昨日,或另一個明天。
只是在無垠寂寞,那是憂鬱者最著迷與恐懼的矛盾,無法言語,無聲與無對話的孤獨,清風拂過一些欲言又止、欲說還休的語言崩潰,純粹的寂靜,純粹的封閉,沒人敲門,沒人詢及,偶爾自己一聲嘆息,像雨後輕雷。
無法言語不是沒有話說,而是沒法與某些聆聽者說,西方人可憐而寂寞,需要找一個分析聆聽者說,盡傾所訴後就心安理得,如釋重負,自欺欺人。東方人是語言的挫敗者,在一個有理說不清的語言世界,少說無益,多說徒然,不然不說。然不說只是無聲,並非無言。多說亦不過重覆又重覆一個悲哀故事,亦是徒然。
對世情反覆也沒有希亟。人是善變的,善變為惡,惡變為極惡。想不到的竟然發生了,發生了的竟無法轉圜了。葉紅花凋,一切皆是無法改變的注定,分別只在於先後,先花後葉,或先葉後花。
想碰到感到愉快的人就能碰到的麼?就算碰到就一直感到很愉快麼?人隨著環境歲月而變化,少小成長,長大氣盛,怎會想到一手撫養成人,一旦色變,翻臉無情?車子隨著公路漫然伸展,手撫著心,心裡好疼好疼,像絞心痛,好漫長無奈的疼痛。沒有憤怒、悲哀、或不捨,只有濃郁憂鬱與沮喪,像一杯烈酒,一飲而盡,嗆喉,胸口火辣。
黃埔灘頭夜上海,周璇那般回味著,換一換,新天地,如夢初醒,想不到夜上海隨著轉動的車輪,復活在廿一世紀。那麼顛顛跛跛、跌跌撞撞走過一年多,從春到夏,秋天夜裡無窮的孤獨晚餐。流浪者在選擇的異鄉,甘心情願終老的異鄉。在小飯館強掩抑鬱,低頭喫飯,飯是鹹的,因有淚。夜是寒冷的,因為孤單。這是卡謬筆下陌生人的世界,不是異鄉人,也不是異鄉語言的隔閡。
常常自豪於本土與異鄉語言之餘,就算碰到感到愉快的人又如何? 會知道麼? 會相識麼? 向一個陌生人搭訕,會可能麼? 難道真的如此巧遇,他就是燈火闌珊的那人麼? 低頭撥飯,翻眼覷看週邊的人,許許多多的人,都是陌生人,互不相識,不打照面。
回家頹然倒在椅子暗裡,視線落在牆上一張歡樂照片,用目光把離棄的一個一個劃掉,連忠犬都死了,那是死忠。賸下另一隻老去的小狗,老去的中年。
目光劃掉不等於心中劃掉,心中劃掉不等於記憶劃掉,記憶劃掉不等於現實劃掉。希望是一個夢,但卻不是夢,曾經發生的依然已經發生,沒法磨滅的依然沒法磨滅。像一種癬,要抓到出血才停止癢,沒有快感,只有漠然。 那天練完琴,出外辦事、購物,在江邊漫步,看著江水粼粼東流,目光越遠想得越遠,沒人知道,像普通人,寒喧、揮別、上車下車、開門關門。看著別人一家,孝順兒女攜著老太太上館子,一切都像正常人,只自己知道自己神智不清明、不集中。
(三)
網站上看到耕莘文教院給她設了一個「葉紅女性詩獎」,獎勵女詩人創作,順便瀏覽了相簿十八張照片,對她一無所識一無所知,似乎一個人的一生就在十八張相片內(只辨識白靈在內 ),其實何止? 耕莘是她一生辛苦耕耘的一塊心田,自有福報無限。從耕莘想起那些Jesuits,李達三到陸達誠 ,還有丁松筠丁松青兄弟。甚至早年台大的Father O'Hara,還有華仁書院那些耶穌會神父,Toner, Moran, Sullivan, Kennedy, Finneran, Hyden, O'Neal, 都是愛爾蘭人,一一都作古了,像喬埃斯「死者」內的Gabriel, 都柏林大雪夜裡獨坐沉思,雪在窗外不斷下著,死者已矣,但那唱The Lass of Aughrim 的年青人多年來依然活在妻子的心裡,其他人將一個一個離開。
悲苦就是修行,唯苦修與苦行方成正果。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聞二百億」故事內,佛祖勸說那個勤於修行、力求果證以致雙腳流血的出家人,足以為憂鬱者戒。世間事沒有絕對黑白對錯。刻意與隨意間,自有一種節奏,該緩則緩,應急則急,像清風良夜,君子倚石撫琴,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以此為喻,弦急則聲不合韻,弦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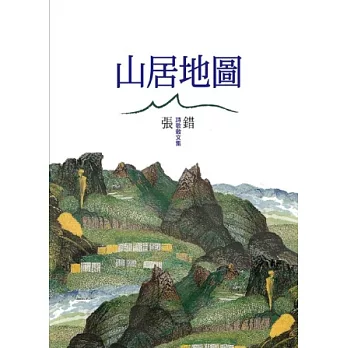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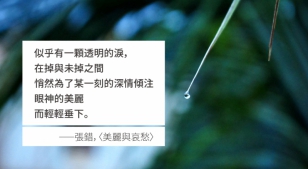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