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第二隻長頸鹿
……幾千年來,你被追捕獵殺,只為了你的肉與象牙。但在文明時代,人們開始將殺戮當成娛樂和功勳,似乎透過殺害地表上最雄偉生物這種病態的方式,能減緩我們身上所有的恐懼、挫折、懦弱和不安全感,這肆無忌憚的行為為彷彿能為我們的生殖能力打上一道奇光,彷彿能夠讓人重新壯陽起來。
那當然、還有一些老說你沒有用處,說你毀壞田裡作物、讓飢荒加劇,說人類已經有夠多問題、自顧不暇、哪有辦法為大象著想的人,他們實際上的意思是,你是奢侈,我們無法負擔,這跟那些極權主義者提出的論述完全一樣—— 無論是史達林、希特勒或是毛澤東,他們以此佐證,宣稱進步的社會無法負擔「個人自由」這樣的奢侈。人權如同大象,如同提出異議、獨立思考的權利,如同反對和挑戰威權的權利,經常被以「必要性」輕易地質疑並加以扼殺、壓抑。
─節錄自羅曼.加里〈親愛的大象先生〉
羅曼‧加里 於一九四○年駕駛飛機從法國投奔北非的自由法國空軍,在阿比尼西亞、利比亞和比利時等地作戰,與死亡擦身之際,同大象相視而臥,在很多年之後的一九六七,他將這件事寫進了〈親愛的大象先生 〉,一封給大象先生的情書。最懂大象的緬甸人相信,象的記憶長過生命,能夠記得前世的事情,其實大象並不需要讀信,象早就甚麼都知道,甚麼都理解。這封信在人類編輯發行給人類看的《生活 》雜誌上刊登,表示這是文學家想對人類說的話。
我是最不願意一開頭就提到死亡的。
死亡、或是諸如此類的話題,總會讓人想要別過頭去或是閉上眼睛,因為那些畫面對於愛護生命的心靈來說太過醜陋,但遠方一隻長頸鹿的死提醒我,所有對生命的愛護都應該包括面對死亡。
二○一四年二月七日,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動物園裡,飼養員使用電擊槍,乾淨俐落地殺死了一隻長頸鹿,他們說這樣做能將死者的痛苦減到最低,且不會使動物遺體內有毒物殘留,是大部分先進的電動屠宰場採納的方式。
這隻長頸鹿是跨國繁殖計畫的一員,十八個月大,雄性,沒有生病,沒有遺傳缺陷,但由於他的基因與多數長頸鹿太過接近,無法確保未來不會造成近親交配,再者,長頸鹿有雄性獨佔的天性,園方即將迎接新來的雄性長頸鹿以利繁殖,兩隻雄性長頸鹿將無法和平相處。他們自認已盡所有力量為這隻長頸鹿尋找新的住處,但沒有一處適合,沒有人能夠保證長頸鹿一生幸福快樂,與其面對可能受苦的未來,不如現在就赴死——動物園的科學總長挺身面對質疑,對科學與基因優化的遠大前程深信不疑,公開邀請大人小孩到現場觀看長頸鹿之死,長頸鹿倒下之後,獸醫開始對這隻大動物進行解剖、採樣、說明構造,最後工作人員將遺體分割成塊,投餵給園內的獅子,在獅子大快朵頤新鮮肉品的時候,長頸鹿染血的斑紋歷歷在目。
我知道所有的生物都是食物鏈的一環,包括我自己,但這片人為重建的自然食物鏈令我疑惑,比起我的疑惑,保育人士的憤怒更加直接,在長頸鹿被處死之前,網上已有超過兩萬人連署反對、示威民眾在園外舉牌抗議多日、園方人員甚至收到死亡威脅。
比起死亡更加難聽的就是錢。
但所有動物園的問題,都是錢的問題,一窩不能容納兩隻公長頸鹿,難道不能讓他另外住、不繁殖、直到終老嗎?養長頸鹿,要花錢的,一隻長頸鹿一天要吃五十幾公斤的糧草,還要一百四十平方公尺以上的空間,加上全職的專業飼養人員,有錢的話,當然好,但現實則是預算過低、場地不夠、人手不足,所以長頸鹿必須死。當然並不是給錢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有一些不能為錢放棄的原則:曾有幾處野生動物園表示願意接收長頸鹿,另有一位私人買主願以五十萬歐元購買,但園方以對方無法維持飼養長頸鹿的標準條件而拒絕,這難道不是正直的表現嗎?
正如很多人想像的,歐美先進國家擁有非常完善的動物福利法,但很少人知道,究竟是怎麼個完善法。根據《國外動物福利管理與應用》一書,保護動物不只是確保其生存,也包括如何「好好地死」:歐盟和美國當今的動物福利法,以「減少動物不必要的痛苦」為原則,在運送、圈養、宰殺方式和屠宰資格上,有非常細緻的規範,單就電擊法來說,必須確保電流通過動物的腦部,且在電擊前先確保動物已經昏迷。我敬佩所有真心熱愛動物,並且願意觸碰死亡議題的人士,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高功能自閉患者、動物行為科學家坦波‧格蘭登 教授,她長期致力於改善畜牧業及屠宰場環境,不但能夠減少牲畜死前的恐懼和痛苦,還能有效提升產業效率,熱愛動物和改善肉品業是否衝突?格蘭登教授的科學心靈異常理智清澈,她很清楚只要我們還身為食物鏈的一員,世界上的肉品產業就不可能消失。
同樣在長頸鹿被電擊而死的那個陰天裡,全世界約有三十萬頭豬被宰殺,他們的肉、皮、組織都被徹底利用,製成各種食品、用品,在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在同樣的廿四小時裡,還有大約五千隻老鼠死於各種不同目的的科學實驗。據說豬和老鼠的智商較高,對痛苦的理解更深,但他們的死亡卻無人聞問,難道長頸鹿的命比較重要,只因為他比較高大、斑紋美麗、睫毛捲曲、眼神俏皮、柳葉狀的大耳朵豎直在臉側、他的嘴角微揚,看起來就像在對人微笑,這張臉讓長頸鹿經常擔任保育海報的最佳主角,有時候覺得這樣真的對嗎,難道動物生命的權利是來自人類的喜愛嗎?有時候是,但在這件事情上,決定生死的是基因組合。
這跨國繁殖計畫的陰暗面──殺死動物,其實一直都在,經常發生,歐洲人工繁殖計畫的原則是以推進生物多樣性為最高目標,是以基因組成的稀有程度成為衡量動物生命價值的標準。
而那一隻被公然處決的長頸鹿,牠跟那千萬死去的豬仔不一樣,牠是有著自己的名字的:馬略 。馬略這個名字來自古羅馬的軍事家,曾經帶領戰敗的羅馬重返輝煌,最後成為獨裁領袖,不法連任了七屆執政官,直到病逝。長頸鹿當然不可能知道這個名字的來歷,就像牠不可能理解毫無病痛的自己為什麼突然就死了。為長頸鹿命名的人,同樣也是決定他死期的人,長頸鹿馬略在一個寒冷的丹麥早晨被電擊宰殺,現場容許觀者拍照錄影,那些影音被大量轉載,媒體儘管一直渴望這樣有血有肉的好料,卻還不忘加上警語:「請注意:本則新聞包含血腥畫面」,怎麼動物的生肉就是血腥的了?
我童年時期經常在農家度過暑假,在那裏飼養的動物都有各自的宿命,即便是親如家人的那隻小狗,也有守衛家園的責任。餐桌上的食物不是平白得來的,我從那裏認識了許多動物的本性,也很早就理解家禽家畜終將面對死亡,我滿十歲以前就已看過多次殺雞流血的場面、幫忙清過鵝肉上頑強的毛根、有時還會聽到隔牆豬仔被拉走的慘叫,雖不算愉悅,但也沒有留下陰影,我認為不讓孩子認識死亡不是好事,問題在於地點——動物園不是屠宰場,即便宰殺的過程百分之百符合歐盟規約,「在動物園殺死健康動物」這件事情不應該合理化,當「基因過剩」成為殺戮的正當理由,動物園原本就很脆弱的立足點也就開始動搖、嚴重地動搖。
一件事可以有好多講法,光是殺死長頸鹿一舉就有好多說法:單純描述這個動作的詞是「殺死」或者「射殺」,若動物生病,大可以使用自我感覺良好的「安樂死」(euthanize),但是馬略年輕又健康,園方使用了「處理」(put down)一詞減緩殺氣、而媒體則大多順從群眾好生之德,以「宰殺」(slaughter)譴責之,而科學修辭的最高境界則是「撲殺」(cull)或者「移除」(remove),這些動詞讓殺戮變得乾淨明亮、充滿遠大理想,哥本哈根動物園的科學家是理想主義者嗎?他們寧願抵擋千萬人哀慟與威嚇,也要貫徹對研究的熱忱嗎?他們是不是想在這鄉愿的世界面前,展示刺眼的真理?科學總長正氣凜然地說:「科學家的責任是有時要做一些不那麼美好的事情,以確保更加美好的未來。」
科學追求理智,而理智到了盡頭都會變得殘酷,科學家經常抱著最純淨的心靈走上最殘酷的道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達爾文主義被曲解成為種族主義、日軍七三一部隊以醫學研究之名在中國進行人體實驗、納粹以優生學為藉口、以民族優越感為助力,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當第一個「不值得活」的人被殺,而無人質疑,其後便會有第二個人被殺,有第二個人被殺,就可能會有第六百萬個人被殺。
長頸鹿馬略死後幾天,丹麥的另一處動物園宣布,為了迎接一隻母長頸鹿到來,避免原來兩隻雄性為爭地位打架,可能將要宰殺其中一隻公鹿,那隻長頸鹿七歲,也叫做馬略。第二隻叫做馬略的長頸鹿若被殺死,將不只是兩隻長頸鹿的死亡而已,將死亡當作功勳,無論以科學之名或是道德之光,那絕對不可能是正確的事情,馬略二號後來逃過一劫,但不是因為洪水般襲來的輿論壓力,而是他的基因「比較稀少」,因為基因而逃過一死,我要繼續挑剔這樣的理由還是很殘忍,還是只要他活下來了就好?
我經常走在往動物園的路上,這讓自我辯證成為一種常態,到了最後我經常還是沒有答案,但我相信這個世界的正解不只一個,而找到正解也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維持清醒,捍衛思考不被激昂的感情左右,不被那廉價的同情與自傷牽絆,不再因為遠方長頸鹿的死而遷怒,有些事情現在可以馬上就做到,比方說:動身前去探望一隻離家最近的活長頸鹿,或是任何一名你喜歡的動物──包括人類。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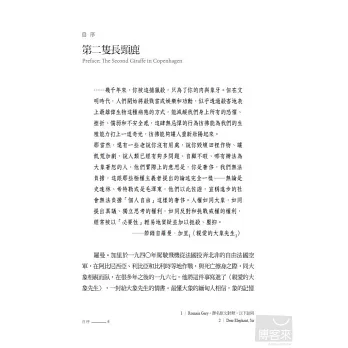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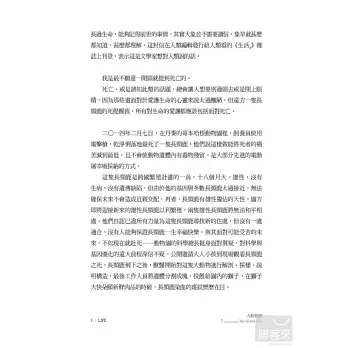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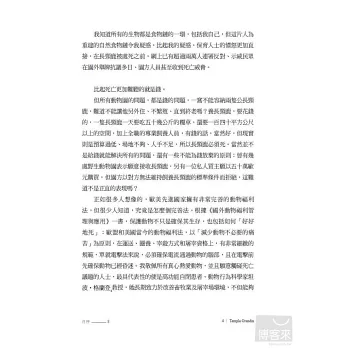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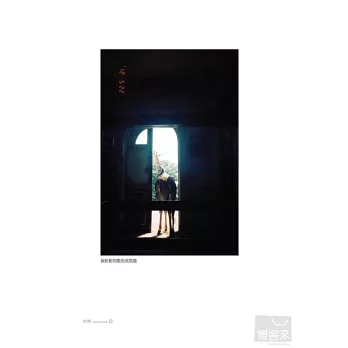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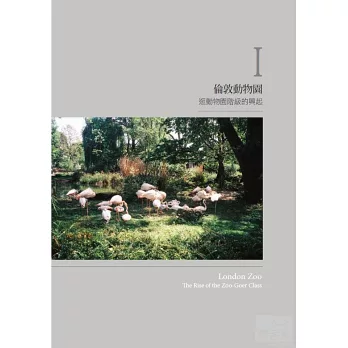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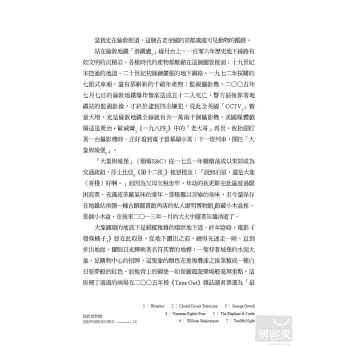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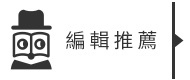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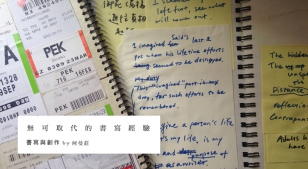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