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細沙
為什麼要去越南追蹤移工返鄉之後的情況,走一遍他們回家的路?
如果不是這本書,我應該不會打開越南地圖,搞清楚河內和北寧、廣寧,還有下龍灣是在哪個相對位置;還有我們以為是越南門面的胡志明市和這些處在北越的城市有多麼遙遠的距離。沒錯,越南是我們生活中最近身的陌生人。GOOGLE地圖裡可以簡單的設定河內東英到海陽的路線規畫,電腦世界裡開車一個半小時就可以抵達,但是現實世界中顧玉玲和阿海騎機車飛馳四個小時,撲天風沙中才得以抵達,只為了要參加從台灣返回越南家鄉的「失敗者聯盟」工人聚會。
這些在台灣人眼中的移工是為淘金逐夢來台:他們在台灣賺了錢回家蓋樓翻身,甚至可以請幫傭自己換當少奶奶……,在這種簡單制式化的描述裡可以省略和合理化了:「對,我們台灣人真的苛刻了他們」的事實,因為來台灣打工讓他們有了機會翻身致富。顧玉玲的前一本書以「我們」來描繪因為移動而牽引交織、跨越國籍的自身認同眼界,出版至今已有六年,但是移動中他鄉和返鄉是線的兩端,另外一端的世界又是如何?跟移工一起回家變成一個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探究因為在台灣的勞動造成與家人兩地隔離,被迫中斷家庭生活三年、五年甚至九年的,返鄉後的家還是可以回得去的家嗎?帶著在台灣的傷害回到越南的生命難道可以自然癒合無縫接軌?不能說出祕密的阿蓮、手掌截肢的阿海、永遠失去文遠的阿清,他們的生命因為在台灣的工作而有了巨大的轉變,後來呢?身為運動者、書寫者的雙重角色,顧玉玲若沒有再追回去越南,實地延續這些生命回家種種,實際情況永遠不會出土,屁股坐在台灣電腦前的我們更不會知道。
我好奇書寫《我們》和《回家》有什麼差別?這兩本書的敘事都非常豐富流暢,似乎沒有任何阻滯闇澀。沒想到顧玉玲卻回應,《我們》是現在進行式,在工作中找零碎時間書寫,幾乎可以一落筆就寫,打開電腦就能開始編織這些內容,但是《回家》則完全不能,落筆艱難,刪修改寫多次。當她離開台灣踏上越南成為異地來的外來者,越南對移工而言是故鄉,對她而言卻是異鄉,時空身分完全易地而處,當然她在越南的不安比移工在台灣的處境好太多了。但是面對全然不同的越南社會,眼見的是什麼?眼見就是真的嗎?怎麼樣寫才不致誤解或是扭曲?讓她在當地拚命的做筆記希望自己能夠儘量保留現場的紀錄,回到台灣返返復復的思索如何重新整理才能下筆成書。這讓我聯想到自己拍攝勞工紀錄片的經驗,同樣的一個罷工行動,相同的反外包抗爭解雇案件,同在其中的勞工也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和記憶,甚至是矛盾的訊息和關係,而這些矛盾和差異應該是真相的一部分才是真實;而我們永遠都踩在這個不安和一再的思辨中完成我們在運動中的創作/紀錄。
這個書寫計畫,顧玉玲分別在二○○九年底至二○一○年赴北越停留兩個月,以及二○一三年九月到十月再度回訪,其中包括到北寧替阿蓮盡孝道彌補她無法參與父親喪禮以及撿骨儀式的遺憾,包括回到台灣幫忙討回文遠已然作廢的護照,全數提領逃跑廠工阿勝的強迫儲蓄金,以及小雪存摺裡的血汗錢,幫忙送給有情無緣人的草藥……,最後,用二十萬字要寫下這一代越南來台移工的面貌。但是,這些書裡的移工如同十粒、二十粒、三十粒遙遠越南的紅河細沙,淘洗漂流在浪潮中的生命故事,能夠留住台灣人目光嗎?他們的愁悵悲歡能夠成為我們心中的小波折嗎?這些比台灣工人更無名的無名英雄,二十萬字的書寫卻是顧玉玲一減再減不能割捨的,因為,如果沒有為移工留下這些故事,應該就不會再有其他人為他/她記言記行記情,立書留傳。而刻意從第一批來自北寧鄉村的阿草和五姊妹寫起,這六位比較年長的女性越勞,到後來年齡愈來愈輕,學歷、能力和主動性愈來愈強的工人樣貌,見微知著的反應了近十五年越籍移工的改變,他們不同時期的生命利害選擇的思考,還有近年來越南社會的改變,從半套的衛浴設備、只有電腦不能上網未完成的數位化,全村只有兩線電話,在四年後跨入全套設備和人人都有手機的轉變,似乎經濟的步伐變得快,但是回到越南的工人仍然在命運和機會中拚搏。回家之後仍是一個經濟戰爭在等著他們。
這本書留下移工在遷移與返鄉的人生中的片刻瞬息,記錄這一代從越南到台灣再返回越南的工人拚搏甚至殞落的樣子,如果因為此書在台灣人心裡留下一個印象,這已經不是掛零的空白。
郭明珠
‧本文作者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紀錄片導演
序
海內存知己,天涯共比鄰
從事移工服務已將近三十年,在這個過程裡,我見到台灣社會最不堪的一面,同時也看到了這社會存有真、善、美、聖的人情風景。若你曾經關懷來自東南亞國家藍領移工的生活處境,便能夠體會何謂不堪的面貌,面對這些不堪的現實,你可能會懷疑這是否真的是台灣的一部分?然而,若你有幸在理解底層社會的旅程裡尋獲知己,你就會體認到自己是個多麼幸運的人,畢竟在這孤獨而清醒的旅程中,有那三兩人們,與自己有著一樣的心情。進而你將在過程裡產生自我衝突、陷入無邊際的懷疑、然後在不遠的轉角處,愕然發現一種全新的人生體認,那更真實、良善、美好、並且神聖的價值。顧玉玲小姐便是我這段路上難得知遇的伙伴,我們一同歷經最惡劣的環境,並且分享著這段旅程的美好。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便因為不願成為越南政權下不自由的奴隸,而離開掛念的故鄉,選擇流亡。在那段逃亡的日子裡,我亦曾經是玉玲筆下,某一段艱辛故事裡的主人翁。因此,我當然深刻的了解身為一個越南人、海外難民、流離移工的風險與困境。二十餘年的旅台生涯裡,因為我了解越南人隻身在外出賣勞力的辛苦及需求,因此我在聖高隆會、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的支持下,成立了「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VMWBO),以協助移工、新移民為宗旨的專業非政府組織。辦公室自二○○四年成立至今,從沒時間去細算我與辦公室的伙伴們服務過多少個案,從每日接應不暇的申訴案件來看,二十多年來台灣境內移工的遭遇雖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困境是未曾褪去的。
越南移工的共同困境是什麼?它來自於貧窮的農村子弟,受到越南當地的企業主與越南政府聯手剝削的厄運。貧窮的農村子弟本不具備足夠的社會資本,為了脫離貧窮必須選擇涉險,離鄉到台灣工作,接受最低的勞動條件,賺取當國最基本的報酬,再透過兩國貨幣的匯差,以相對富有的態勢返回母國。而在這一整個過程裡,越南當地的企業主化身為仲介的角色,藉由國家政策覬覦這些農村子弟的勞動報酬,巧立名目在規費、服務費上大肆收刮,他們坐享其成吸吮著農村子弟的血。身為移工接收國的台灣政府並非不知越南移工處境的惡劣,卻屢以外交弱勢、司法管轄權等理由,放任這種剝削存在。再加上台灣政府重視大型企業而輕忽中小企業的勞動環境,使得台灣國內勞資爭議、職業災害、以及不當對待的事件層出不窮。你可曾看過某個勞資爭議協調會的場景:企業主每小時短缺給付二十五塊錢工資,還一再強調自己是如何善待移工……那種無俚頭的肥皂劇情。這不是刻意的諷刺,而是我辦公室的伙伴們每天都在面對的問題,這是深刻的台灣問題。
這幾年我偶爾聽見玉玲請長假遊歷越南,說要探視一些曾經一起經歷過坎坷故事的移工,想看看他們回家後的情況,試圖理解他們的想法,記錄他們的境遇,並捎回許多相片與我們分享。令我訝異的是,許久未見後的某一天,她告訴我說,這些片段旅程與種種經歷已經撰寫成冊。它是一個寶貴的文化記錄,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溫暖。我看到這些曾經經歷過台灣移工生活的孩子返國後,過著各式的生活悲喜,情緒總激昂久久不能平靜。若不是現有越南政權對社會的撕裂,我也應該回到越南與兄弟姊妹們共築夢想啊!
我推薦這本書,因為它深刻的刻劃這一代越南移工的真實命運。
阮文雄
‧本文作者為越裔澳籍神父,來台傳教後創辦VMWBO
序
尋找一株開花的樹
小時候,我家住在胡志明市的一條小巷子裡,有幾戶潮州人、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很多越南人,有一些有孩子卻沒有丈夫的越南女人。那時是一九七五年之後,越南結束最後一場對抗殖民戰爭,實現了共產黨統一全國。然而,飢餓並沒有隨著和平降臨而消失,即使在一九八六改革開放後的好些年,人們仍得拚力度過每個物質匱乏的日子。
細瘦、黝黑的鄰居女人們,清晨四五點鐘去菜市場採買食材,紅豆、白豆、花生、蛤蜊、血螺、毛貝等等,七八點鐘蹲在自家廚房門口仔細整治,吃過粗淡的午餐後,一肩挑起鍋碗瓢盆及各色食物,步行至一處空地擺賣午後點心,直到黃昏才收攤回家。日復一日,她們辛勤養家餬口,不時打罵孩子。她們之外,還有無數婦女在炙熱的陽光下挑著扁擔或側手抱著大竹簍沿街叫賣,偶爾看到幾位大姊在臉上塗抹白白的面霜,出門至夜晚才回家,她們做什麼,鄰居皆心照不宣。
這些女人忙碌的身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啟蒙了我關於生存、命運以及母性的感受。
越南中小學的文學課常常講授《金雲翹》,那是一篇十八世紀的敘事長詩,講述女子割捨青春愛情、賣身救父的孝順事蹟。越南還有許許多多優美且帶著淡淡傷感的歌謠,感激媽媽、姐姐的忘我付出。
我被教導,也衷心尊敬,女人的無私奉獻。
後來,我移居到台灣,漸漸發現,台灣女人能做的事情很多,她們當教授、律師、心理醫師等等,學養豐富且聰慧美麗,在講堂裡或電視上侃侃而談。甚至,有些女人投入社會工作,為環境安全、為勞工、為外籍配偶等等爭取權益,能量強大,其中有顧玉玲。
二○○八年,《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出版,顧玉玲以細膩的筆觸書寫她陪著菲律賓勞工在台灣社會掙扎奮鬥的過程,故事說得節制,但深沈地扣問何為「他者」而誰又是「我們」。那年讀完新書,我念念不忘怎麼會有人,一方面能夠向政府和淡漠的主流社會強悍抗議著,另一方面卻擁有柔軟的文心及動人文采。顧玉玲觸動了我去思考關於女人的社會成就。
六年後,顧玉玲更進一步地踏進移動勞工們的原鄉,記錄越南勞工結束了海外打工之後的返鄉生活,寫成《回家》。在幾趟探訪北越的旅途中,作者幾乎張開所有感官去捕捉當地的種種情貌,貼近再貼近,而書中關於越南女工的描寫,勾起我無限回憶。
改革開放至今將近三十年,越南女人們的生命情境和我童年所看見的相差未遠,她們依舊努力為貧困的家人精打細算、謀求出路,只是方法從下田耕作、沿街叫賣改為飛往異國當女工、幫傭或看護。然而,四處告貸出國的她們,有多少人衣錦還鄉且真的改善家庭生活了呢?數年遠行在她們的生命裡會烙下哪些印記?書中以北寧鄉村的阿蓮為起點,步步捲纏展開多位曾經在台灣打工的女人故事。阿蓮先是合法工作,後因故逃跑,差點被同鄉騙入色情場所,好不容易找到各種零工度日,捱到自首返鄉之時,不幸被警察當局叫去指認人口販賣疑犯,她被迫多滯留八個月而錯過了父親的撿骨儀式。幾番折騰後,總算回得了家,阿蓮卻陷入懷疑丈夫外遇的精神折磨裡,她四處向鄰里哭訴,多次高調自殺,起伏不定的情緒牢牢地將她和家人綑綁近乎窒息。如此戲劇化的阿蓮卻是我相當熟悉的一種越南女人類型,她們承擔太多苦難,又驚恐自己的犧牲終將付諸流水,故而常常失控。
有時候,我會想,付出可以是一種選擇,但女人的忘我付出不應該是社會集體的唯一選擇,什麼時候越南女人才能出現其他新的可能?在第一屆台灣移民工文學獎決審會場裡,顧玉玲認為,移工的結構處境固然悲慘,然而她們(及他們)個別的勇氣是值得珍視的。書中的金燕正代表著這份難以言喻的勇氣,力求突圍。金燕有主見且堅定,年紀輕輕為愛結婚生子又果斷離婚,恢復單身的她千里迢迢來台灣打工,經歷過逃跑、車禍重傷、輾轉來到天主教庇護中心、被醫院追討醫療費用等等,她的中文變得很流利,也協助庇護中心援助其他個案。金燕在庇護中心學到了組織運動的方法,回越南之後,她積極串聯返鄉勞工彼此互助,又陪伴被當局冷落的工殤家屬爭取賠償,甚至也幫助農民反抗蠻橫的欺壓等等。充滿膽識與活力的金燕讓越南政府感到焦躁,可是她很勇敢,她以行動顛覆了越南長久以來加諸在婦女身上的固定角色意象,她不再是歌謠中溫柔而苦情的媽媽或姊姊,她是現代的社會實踐者,豐富了越南女人的生命類型。
除了阿蓮、金燕及其他女人之外,《回家》連帶記錄這些女人的丈夫及家庭情況。當太太們出國工作之後,無論順利與否,她們畢竟都開了眼界,而留在故鄉的先生們是怎麼樣去面對傳統的家庭分工模式被裂解或顛覆?
二○○七年初,我去參加兒時朋友的婚禮,其中一部分儀式在鄉下舉行,按照習俗,父親要親自為女兒選一株芭蕉樹立在于歸之門邊,朋友的父親拎著陳舊鐵刀砍下一株碧葉亭亭,慢條斯理的整理著。圍觀的小伙子七嘴八舌好奇探問:「老伯,你怎麼不挑有蕉串的那棵,好讓姐姐多子多孫?」伯父突然斥喝:「什麼多子多孫,你要苦死我女兒啊?」酒席在自家庭院擺設,請來廚師只負責燒菜,其餘雜務全由女人包辦,輩份最小的幾個女孩蹲在屋外刷洗堆積如山的碗盤,晚宴過後,男人們又要求下酒聊天的小菜。第二天是迎親日,女人們大清早就出門化妝盤髮去了,男人們醒來發現廚房冷清、爐灶空空,紛紛抱怨沒有早餐,朋友的媽媽終於忍不住爆怒:「我們每天從早到晚伺候你們還不夠嗎?我們這輩子能有幾次好好打扮漂亮?你們還好意思開口要早飯?」素來溫柔的伯母情緒狂飆,痛快數落著家中小叔、姪兒、外甥們,伯父靜靜在一旁任由妻子發洩,最後吆喝男人們自己去煮飯,那是他支持妻子的隱諱方式。
然而,伯父的體貼有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和伯母鶼鰈情深。在越南的農村裡,無論南方或北方,傳統男尊女卑觀念根深柢固,一旦雙方的關系被突如其來的全球化經濟所擾動,我們看到在《回家》的描寫中,男人們的反應各有不同,有的男人發現女人轉變了,願意諒解配合,雙方一起為將來打拚,有人不甘心或恐慌,紛紛墜入酒隱、毒癮及外遇,還有人反過來被妻子嫌棄……
《回家》詳實的田野記錄,企圖立體地呈現個別返鄉勞工的真實處境,而這樣的筆法早已深入文學範疇去了。於是,透過閱讀,我不只能看到越南女人現在好些了嗎,還能看到越南男人現在怎麼了。事實上,女性遭遇只是我因為兒時啟蒙而產生的閱讀偏向,顧玉玲想要呈現得更多,更多關於卑微人們的掙扎、拚博,因此也提供了男性勞工情況,例如阿海、阿山、阿勝等等。
眾多勞工的返鄉生活是主線,其間鑲嵌著顧玉玲慣有的敏銳反思,她住進勞工朋友家裡,用心聆聽,誠心融入,又屢屢參照台灣和越南社會之同與不同,直指結構性的壓迫與不平等。另一方面,顧玉玲是好奇且勇於嘗試的,北越鄉間的紅磚矮房、稻田、溝渠、糯米團、野生茶、如咖哩粉的木屑、鮮辣的木材氣味、風沙撲面的道路、馬路邊的彩券攤、熱帶豔陽和午後暴雨等等,都一一寫進書裡,這些細筆描繪讓《回家》變得層次豐富且更有味道,倘若不是作者先釋放了感性去體會去同理,又怎麼能夠翻轉出理性的了解和批判?《回家》的筆調收斂而情感至深,與先前的《我們》風格保持一致,只是《回家》的文字更為輕盈好讀。
生存不容易,當全球化趨勢看來暫時無法逆轉之際,保持樂觀是有必要的。即使前途未卜,即使必須浪跡天涯打工賺錢,借用唐諾的一句話—「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因為相信,故而心心念念尋找一株開花的樹。
羅漪文
‧本文作者為越南華裔,十三歲定居台灣,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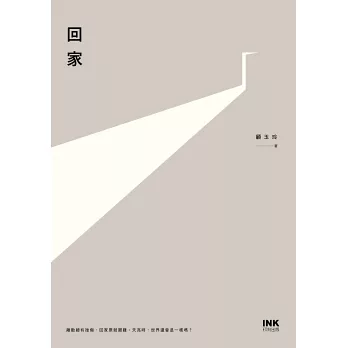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