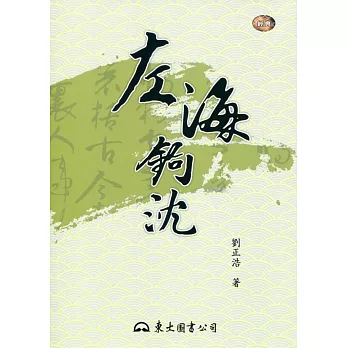自序(節錄)
《左傳》是一片蘊藏豐富的大海,潛游其中、浸淫成癖的學者史不絕書。雖然獲致瓌異,滿載而歸的大有人在;但是仍有無盡的珍寶淹沈海底,有待後學鉤取打撈。
這本小書,選集十篇單篇論文而成,是我多年來《左》海鉤沈的所得。有通論性的,也有專門性的;有白話的,也有文言的。各篇目仍存其舊,內文皆作了些許必要的修訂。為求內容的聯貫,不以發表的順序為先後。
〈《左傳》導讀〉,本為康橋出版事業公司(已歇業)出版《國學導讀叢編》中的一篇。希望以個人長久摸索的心得,對研《左》的朋友在《左傳》的緣起、作者、性質,以及《左傳》解經的模式、《左傳》的價值和研讀方法等景點,作直捷正確的導遊,免於才上路就陷入古今文之爭的迷山霧海之中,虛耗了光陰與精力。其中我對「左丘」一名所作的解釋,後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裏,「有人」作了相同的說法;論左氏解經的模式,徐復觀〈原史〉一文中,也見到近似的陳述;所見略同,令我感到莫名的鼓舞。
〈試揭《春秋》神祕的面紗〉,發表於師範大學文學院院刊《教學與研究》第十一期。《史記‧太史公自序》載上大夫壺遂問:「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史公引用董仲舒的議論為答。這番話,王應麟以為「深得(《春秋》)綱領之正」;黃澤以為「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本文就董說作深入的闡釋與商榷,以明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和目的。用史體作《春秋》的緣故,及《春秋》大義之所在、《春秋》意旨廣博而歸本於正名等等的問題,以補前文偏重《左傳》的不足。
〈孔子「正名」考〉,發表於《孔孟學報》第三十六期。此文專論「正名」的問題:先就前儒對「正名」分歧的舊解,分門別派,作全盤的檢討;次據桓公二年《左傳》,推論「正名」思想源起於周宣王時的晉大夫師服,並不始於孔子;再次將師服、孔子論名的言詞,逐句作對比的研究,糾正許多舊解的錯誤。於是孔子名正言順的理論,《春秋》正名的宗旨,都有了確切不移的解釋。
〈左氏前傳釋義〉,發表於師大國文系《國文學報》第二期。左氏附益於《春秋》經文之前的一小節傳文,世稱「前傳」。解經而附益於經文之前,其重要性不問可知;可惜事關國恥,丘明隱約其辭,司馬遷既歿而大義失傳。本文據《史記‧魯世家》述前傳之辭,推尋傳文本意,乃知鄭、賈、征南說經之非,並了然於《春秋》始隱之故。
〈孔聖無二憂〉,七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師大文史教師學術研討會中提出,會後意外被推薦連載於八月二十六、二十八日《青年日報》副刊,旋又編入國教會叢書《憂患意識的體認》。本文主旨在於說明:孔子基於當時社會名實紊亂、將陷於國破家亡的憂患意識而作《春秋》,終身以世人不能堅守名分為己憂。並比附《大易》易簡、變易、不易之三義,舉例說明《春秋》一經所表白的,正是王道人事簡易、變易、不易的大道,君臣父子應守的常分。此文所論,可補上列諸篇考述《春秋》之不足,使《春秋》的本質和大義更加昭著。
〈「齊桓公正而不譎」考〉,原刊於八十三年《紀念程旨雲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桓公正而不譎的事實,自馬融以《左傳‧僖公四年》侵蔡伐楚事當之,迄無異說;但細讀僖三、四年傳,桓公實為掩飾侵蔡的醜行而伐楚,絕不可謂之「正而不譎」。幾經探索考證,發現《左傳‧僖公九年》載齊桓葵丘之會下拜受胙一事,足以取代,解決了這宗千古疑案。
〈「民可使由之」章經義復始〉,刊載於《國文學報》第二十四期。《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漢魏以來,學者非唯在注釋上不得共識,句讀上也有四種歧異。本文先將歷代注釋,分漢魏學派、宋學派、近代學派,廣為蒐羅,慎加研究,知其十九不合經義。及讀《左傳》,昭公六年,鄭鑄刑書,叔向與子產書,力陳人民熟習法律的弊害,強烈反對;二十九年,晉鑄刑鼎,孔子持完全相同的理由,嚴辭批評。乃悟〈泰伯〉此章,當為時人「法律應否公布」的問題而發,句中兩個「之」字,都指法律而言。法律政令皆緣禮義而生(參見上文〈孔子「正名」考〉),當政者重法律而輕禮義,是衰世捨本逐末的病象,所以古聖先賢一致反對。這是很值得我們省思的。
〈《左傳》中一則「推理小說」的研究〉,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大學中文系暨美國史丹福大學中華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第一屆《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後刊於《國文學報》第二十五期。《左傳‧閔公二年》記「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一事,白文五五八字,內容曲折,具有近世西洋推理小說的風趣;而文筆雄奇變幻,不能以常格分析,極難理解;故本文首引原文,次述背景;然後將原文分段語譯以為脈絡,各別解讀析賞,另加「尾聲」、「注釋」以補不足。希望經過處理,此一奇文能為大眾所欣賞,共仰左氏超時代的文華;並試圖以此創新的體例,鎔義理、考據、詞章於一爐,作為賞析其他傳文的模式。
〈從《趙氏孤兒》揣太史公的悲情〉,原載《國文學報》第二十六期。《趙氏孤兒》是元人紀君祥本《史記‧趙世家》改寫的雜劇,但〈趙世家〉所述,與《左傳》、《國語》所載多有未合。學者於此,或斥其述事妄誕而違實,或疑其雜采軼聞而失考,惜皆語焉不詳,難成定論;是以重加推考,撰為此篇:首述趙孤本事,以明其情節悲壯曲折,及給予廣博觀眾之印象。次錄〈趙世家〉原文,分事實、人物兩方面與《左傳》比對,就諸多顯而易見之差異,確知故事出於虛構。再次由史公慘遭李陵之禍,想見其切齒腐心的悲情,從而揣獲其杜撰故事、且不掩疑竇的本意;並點出他撰述伯夷、伍子胥、屈原、刺客、循吏、酷吏、游俠、佞幸、滑稽等〈列傳〉的心理背景,供學者日後作深入研究之用。
〈氏族制度考源〉,原載《國文學報》第十一期。上古王者審查群臣的德業,以賜姓命氏、封建諸侯的方式,表彰其功德。至於周代,配合當代宗法制度,諸侯亦得賜族予大夫。於是枝布葉分,一姓析為數氏,一氏歧為數族,凡分三級的氏族制度,於焉建立。這種制度,隱公八年《左傳》有魯大夫眾仲述其梗概;然秦廢封建宗法之制,後儒莫知其詳,曲解流傳至今,諸如死後賜族、以國為氏、以王父字為族等,不一而足。本文則遍考經傳,據當世實況,一一諟正,以為孝子賢孫尋源討本之助。
研習和講授《左傳》,垂四十載,不覺已屆古稀之年,謹以零星鉤沈所得,獻曝於大方之家,敬請指教。並奉獻給
慈父劉剛中守光先生、慈母張淑涵女士在天之靈,感謝生鞠的宏恩。
最後,錄出二十九年十二月刊載於重慶《東北論壇》兩篇悼念先父的文章,以誌無盡的哀思。
《左傳》導讀
一、《左傳》的緣起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省稱,而《春秋左氏傳》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它的原始名稱叫做《左氏春秋》,所以漢人時常省稱《左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載:「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最早提到《左傳》緣起的文獻。這段文字,詞句簡約,義蘊豐富,我們可以分成兩節來讀。
「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講孔子作《春秋》的緣起,是說:
孔子在明達王道以後,求見過很多國君(七十是誇大的虛數),沒有人能任用;所以從魯國到西方的王城洛邑(今河南省洛陽縣西北)去遊歷,閱讀了許多王室收藏的史料(「史記」是史書的通稱),和得自舊家世臣的傳聞,回國後便以魯史為基礎,以魯國為中心,慎加論述,作成了《春秋》經。上從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記起,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西元前四八一年)獲麟的那一件事為止。精簡了史記之文、舊聞之辭,刪除了煩瑣、重複的資料,制定一種「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漢書‧藝文志》語),義在言外的義法。於是《春秋》之中,無論是王者平治天下的大道,還是人情事理的法度,莫不齊備。
太史公把孔子作《春秋》的動機,所用資料的來源,撰寫《春秋》的原則和方法,以及《春秋》的起迄與內容的博大精深,用寥寥五十七字和盤托出,真是無與倫比的大手筆。
「七十子之徒」以下,講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緣起,是說:
《春秋》只是一冊以魯國現代史大綱(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的形式,藉歷史人物以道名分的經典,其細節和寓意,孔子用口授的方式,傳給他的學生;因為所品評的都是些有威權勢力的人,那些有褒貶譏刺意味的話,和必須加以隱諱的事,都不可以明寫出來。魯國的君子左丘明,唯恐孔門弟子記取不全,將來抱殘守缺,各走異端,人人固執己見,而失去事理的本真,所以拿孔子的《春秋》大義為綱領,列國的史記為資材,具論其語,作成了《左氏春秋》。
對這一節敘述,我們暫且先注意兩件事:一是聖人基於義不訕上,智不危身的道理,而以「微言」(隱微之言)寄託「大義」(褒貶之義),著為《春秋》的苦心;一是丘明欲以舊史之詳,補《春秋》之約的孤詣。至於左丘明是怎樣一個人,《左傳》和《春秋》的關係是否如史公所說的那麼密切,以及《左氏春秋》何以即是《左傳》等問題,留待下面討論。
二、《左傳》的作者
自《史記》言「魯君子左丘明」作《左傳》,西漢末年的劉向、劉歆,東漢時代的桓譚、班固等從之,並且以為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更無異議。但是到了唐朝,趙匡開始懷疑左氏與孔子同時的說法;宋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又收錄一個「左邱(同『丘』)」怪姓,以為《論語》裏的左邱明姓左,作《左傳》的左邱明姓左邱。鄭樵的《六經奧論》,以為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推斷他是楚國人;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上卻明言丘明為魯國的太史。於是左丘明的時代、姓氏、國籍、身分,都成了擾人的問題。
(一)左丘明的時代
由於孔子說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見《論語‧公冶長》篇)的話,所以劉歆認為作傳的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趙匡卻持不同的看法,他說:「邱明者,蓋孔子以前賢人,《論語》云左邱明恥之,某(古人避孔子諱,讀『丘』為『某』)亦恥之,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邱明為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邱明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為《春秋左氏傳》是邱明所為。且遷好奇多謬,故其書多為淮南所駮;劉歆以私意所好,編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後世遂以為真,所謂傳虛襲誤,往而不返者也。」(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第五》引)《論語》左丘明非作傳左丘明之說既出,於是宋儒王安石的《左氏解》、葉夢得的《春秋考》、鄭樵的《六經奧論》,群起響應,但他們都以為作傳的左氏是戰國人,在孔子以後,非孔子之前。
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語氣上看,很容易使人想到丘明是「孔子以前賢人」;縱使二人同世,丘明也應該長於孔子,或至少和孔子相近。可是《春秋》經、傳,雖同始於隱公元年,但《公羊》、《穀梁》二經、傳至哀公十四年(西元前四八一年)春「西狩獲麟」而絕筆;《春秋》古經(左氏之經)則終於哀公十六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夏「孔丘卒」,《左氏傳》則終於哀公二十七年(西元前四六八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事,更附載魯悼公四年荀瑤率師圍鄭,及趙襄子惎知伯等事。襄子是無恤的謚號,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西元前四二五年),後孔子五十四年。如果丘明與孔子同時,他就不大可能比享年七十又三的孔子多活五十多歲。何況《左傳》記事,猶有後於此者:如莊公二十二年載周史筮知陳敬仲的子孫將代陳而有國;襄公二十九年載季札觀樂,知鄭將先亡。後來周安王十六年(西元前三八六年)陳敬仲的後裔田和立為齊侯,果代陳而有國;周烈王元年(西元前三七五年)韓哀侯入鄭,鄭國果先列國亡;這已是孔子身後百年左右的事情,絕非「親見夫子」的左丘明所能預知的。這些事似乎都在支持左氏是戰國人的說法。
然而《春秋左氏傳》是一部十九萬六千八百餘字的鉅著,上舉寥寥數事,直其九牛一毛而已。據此少許可疑的記載,斷然把史公的原始記述推翻,顯然不能服人之心。所以元末的黃澤就認為「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趙汸《春秋師說》引)。清儒姚鼐也認為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吳起之徒屢有附益(見《姚姬傳全集‧左傳補注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各家於續傳之人雖不一其說,卻咸定作傳之左丘明即《論語》之左丘明。我們考察先秦典籍,知道鮮有未經後人附益的原本,就不會奇怪《左傳》也曾被人增竄;了解漢代傳經,有師法、家法的嚴格軌範,自然會理解史公所言必定有所承受,絕非「傳虛襲誤」之比。所以,在這新說愈多,是非靡定的情況下,我們作一折衷的了斷,說《左傳》成於親見孔子的左丘明,其中顯非丘明所能言者,均係後人所加,應該是很允當的。
(二)左丘明的姓名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既稱「左氏」,那麼丘明氏左,應是無可置疑的事。但是有些學者既認為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就想把他說成另外一個人,不讓他以左為氏了。
最初,有人要教左丘明姓「左丘」。因為他們見太史公既言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又在〈報任少卿書〉和《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彪〈史記論〉說:「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見《後漢書》本傳)《漢書‧司馬遷傳》贊本之,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以為歷代相傳,《左傳》、《國語》皆出左丘明,如果作者姓左氏,名丘明,按習俗講,就不該叫他「左丘」;反過來說,既然稱之為「左丘」,那麼「左丘」當是「公羊」、「穀梁」之類的複姓,其人名「明」,而非「丘明」。遂定《論語》中的左丘明姓左,作傳的左丘明姓左丘,把「左丘明」判為二人。至宋時,鄧名世根據此說,正式把「左丘」一姓,錄入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之中。
其實,此說之虛妄,是很容易拆穿的。因為遍查古今圖書,我們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姓「左丘」的人。左丘明無父無祖,已經夠淒涼了;又復斷子絕孫,豈不慘絕人寰!史公說「左丘失明」,大概他預知後人胡說八道,才哭瞎了雙眼吧?不料一直拖到清朝,才見俞正燮在他的《癸巳類稿‧卷七》中提出質疑,斥「左丘」為「怪姓」;但是他仍不肯讓左丘明歸宗,多方考證的結果,提出一個「左」其官(左史),「丘」其姓,「明」其名的結論。他說:「邱明傳《春秋》,而曰『左氏傳』者,以為左史官言之,如史遷書今名『史記』也。」這意見,近世篤守舊說的劉師培先生也採納了,只是略為增飾,以為孔門弟子諱言「丘」,故不叫「丘傳」,改稱「左傳」而已。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無須一一指摘前儒的瑕疵—例如《左傳》、《史記》並為後起之稱(《史記》本名《太史公書》),但《左傳》義取「左氏之傳」,《史記》卻襲用古史之通稱,義取「太史之記」,非「史氏之記」—因為他們說不能稱「左丘明」為「左丘」,在根本上就出了差錯。
古人多以單字為名,而把用兩個字組成的名字叫做「二名」。顧炎武說:古人二名,往往只稱一字。如晉文公名重耳,可連氏稱「晉重耳」;但定四年《左傳》載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盟約)只稱「晉重」;昭元年《春秋》載「莒展輿出奔吳」,《左傳》只稱「莒展」。再如〈晉語〉載曹僖負羈稱叔(字)振鐸(名)為「先君叔振」;並省其下字(見《日知錄‧卷二十四》)。此例《史記》中也屢見不鮮,如曹叔振鐸,〈管蔡世家〉贊只稱叔鐸;夏徵舒,〈陳杞世家〉或單稱舒;並省其上字。又如魯隱公名「息姑」,見〈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則一概稱「息」。魯閔公名「啟方」,見《世本》、《漢書‧律曆志》、杜預〈世族譜〉;〈魯世家〉避漢景帝諱,易「啟」為「開」,但只稱「開」,而略其「方」字。由此看來,「左丘」即「左丘明」的省略,應無疑問。這種省稱的方式,後世不用了,古代是很通行的。
那麼太史公為何不稱「左丘明」,而一定要省呢?既然要省,為何不稱「丘明」,卻稱「左丘」呢?我們先錄出〈太史公自序〉有關的上下文再說: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這段文章,自「左丘失明」起,一連八句,都是四字句,一旦寫「左丘明失明」,就破壞了句法的整齊;因此這句子一定得省。但若省作「丘明失明」,在四個字的短句中,重複用兩個「明」字,又犯了修辭的大忌;於是不得不省作「左丘失明」。明白此理,就知道作傳的左丘明定姓左氏,不氏左丘,也不氏丘;同時「左」也不是官名。至於「丘明」,熊十力據孔子「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以為是他的字,不是名,可從。因為自謂用名,稱人用字,是古今通行的社交常禮,孔子絕不至忽忘的。古人對二字組成的名可以只稱一字,對二字組成的字應該也是可以的。
附帶一提,屈原的時代,在孫臏之後,不韋之前;太史公把他序在西伯、孔子之下,可能是推崇他的心志明潔,可與日月爭光,尊他為聖賢,故不與諸子等列。至於降左丘於孫子之前,可能基於「失明」和「臏腳」同為身體上的殘傷,屬辭聯類的緣故。有人忽略了文章修辭的法則,認為史公序列這些人物,都以時代為次,遂斷定丘明為戰國人。果然如此,史公以《詩》三百篇斷後,難道三百篇是戰國以後的作品嗎?
(三)左丘明的國籍和身分
宋儒鄭樵以《左傳》序晉、楚事最詳,謂丘明為楚人。朱子也認為左氏為楚左史倚相之後。明儒郝敬,則謂《左傳》出於三晉辭人之手。近人衛聚賢先生本《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吳起,衛左氏中人也」的記述,以為《左氏春秋》為衛人子夏在魏西河時作,傳給左氏人吳起,吳起世傳此傳,世人歸功於他,故有「左氏」之名。錢穆先生則直接認定《左氏春秋》即吳起所作。又有瑞典漢學家高本漢,著《論左傳的真偽及其性質》,從文法上推考,認為《左傳》不是魯國人作的。這些學者的主張,都針對《史記》魯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記載而發。他們都避過一個事實,即《左傳》上經常稱魯國為「我」,「我」就是「我國」的意思。如前傳(《左傳》的第一段)云「故仲子歸于我」,隱十年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桓十年傳「我有辭也」,莊九年傳「我師敗績」,十年傳「齊師伐我」等是。同時外人至魯,傳只說「來」,如隱四年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六年傳「冬,京師來告饑」。這都是《左傳》乃魯人所作的鐵證,證明太史公所言不虛。我們必須注意,太史公的祖先自周宣王之世(西元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年)起,世典周史。史公既承其祖業,博識舊聞,又生於去古未遠的漢朝初年,長在遺文古事畢集的太史公府,如果他的記述尚不可信,後人的猜測又如何可從?
太史公稱丘明為「君子」,大概據《論語》說的,他沒有明言左氏的身分,也許當時學者都知道,用不著說,不如稱他「君子」,使讀者聯想到孔子的讚詞而心生景仰;也許基於「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的明訓,不願隨便論定,貽誤後學。究竟如何,如今無法斷定了。
但是《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下,班固自注:「左丘明,魯太史。」杜預〈春秋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先後為丘明加上魯太史和仲尼弟子雙重身分。
說左氏為魯太史,到底是本於傳聞,還是出於猜測,雖然無從考證;但縱使是推測出來的,也推得很近情理。元儒黃澤說:「左氏是史官曾及孔子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趙汸《春秋師說》引)他以竹書簡帙重大證左氏為史官,可謂獨具隻眼。古代簡長或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或八寸。每簡只寫一行(偶有寫二行者),每行字數見於記載的,少則八字,多則四十字。劉歆校中秘書,見古文《尚書》,每簡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東漢服虔《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注》,謂古本《左傳》「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可能用的是八寸短簡。春秋時各國皆有國史,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最著名的三種。蘇軾《春秋列國圖說》,統計春秋列國見於經傳者總共一百二十四國,蠻夷戎狄不在其間;和孔子作《春秋》,命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見《公羊傳‧疏》引閔因敘)的傳說相合。列國的史記,是丘明作傳的憑藉,此固不必全部有用,但若取其半數,總字數亦將數十倍於《左傳》;倘每簡以二十五字計,則簡帙之重大,不難推算。這樣重大的簡帙,私人實無力收藏;何況史記收在秘府,為天子諸侯所珍寶,怎能任其流落民間?所以《孔子家語》說丘明和孔子觀書於周史(此《嚴氏春秋》所引的真家語,非王肅所偽造)是可信的;說孔子「得」寶書就傳聞失實了。
至於左丘明「因孔子、史記,作《左氏春秋》」,說他「受經於孔子」,也是可信的,但因此說他是孔門弟子,則又未必;因〈十二諸侯年表〉既說他「懼弟子人人異端」,那麼他本人必不在弟子之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言左丘明,也表明他不是孔子的學生。據孔子對丘明的讚美,以及《左傳》述孔子言經常冠以「仲尼曰」字樣,不像《論語》尊稱「子曰」;可以斷定左氏和孔子的情誼,應在師友之間。
三、《左傳》的性質
太史公既說左丘明為了怕孔門弟子各走異端,才「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當然認為左氏的書,具有闡釋經旨,傳示來世的性質,是一部為《春秋》而作的「傳」(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說:「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但是左氏不把這部書稱為春秋傳,卻叫作《左氏春秋》,不外下列兩個原因:
1.《春秋》所記的某些事件,左氏找不到原始資料作參考—至少孔子所得的一部分「舊聞」業已失傳—沒有辦法講論其大義。所以《春秋》所有的,《左氏春秋》中往往沒有。
2.左丘明既蒐集了許多寶貴的史料,其中有些站在經學家講正名分的立場可以不收,但站在史學家備述一代史事的立場卻不可不錄。所以《左氏春秋》雖然以「以事翼經」為主,又往往溢出經文之外,敘述一些《春秋》所無的事情。
因此我們可以說左氏的書,本是一部祖述孔子,熔經學於史學的開創之作,其旨趣和一以闡述經義的《公》、《穀》二傳不同。中國正史,自「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純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的《太史公書》以下,一直沒有脫離過這個軌範。「春秋」和「史記」一樣,本來是史書的通稱。這部別開生面的「春秋」是左氏所作,所以題名《左氏春秋》。這名稱既表現出左丘明不敢自附於聖經的謙卑的一面;也透露他志在自成一家之言的自負的一面。
《史記》「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一語,說得異常精深。「孔子」非謂其人,而謂其意旨,指《春秋》大義而言。「史記」則指孔子作《春秋》所據的史冊原本。這句話是說《左氏春秋》一書,是以《春秋》大義為經,以史記為緯,撰述而成。左氏所用的資料,和孔子用的大致相同,如有出入,應該是孔子尋訪的「舊聞」,丘明不一定全知;左氏參考的「史記」,孔子不一定盡讀。孔子筆削所得的史記、舊聞作成《春秋》,丘明便彙集孔子所筆削及所獲的史記撰為《左氏春秋》。左氏的原則,是有經就傳經,無經則敘史,把既得的史料充分利用,竭力保全,所以說他「具論其語」。因為左氏取材,孔子大都看過;所以其書雖然晚成,內裏許多文辭,孔子日常早已在引用。如孔子的正名說,就是師服命名之論的化身(後詳);「出門如見大賓」之語(見《論語‧顏淵》),出於臼季薦郤缺(僖三十三年傳:「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秀而不實」之喻(見《論語‧子罕》),本於甯嬴評處父(文五年傳:「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不學禮無以立」之訓(見《論語》〈季氏〉、〈堯曰〉),始於僖子告其家臣(昭七年傳:「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十二年傳載:「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便明白指出「克己復禮為仁」(見《論語‧顏淵》)這句話出於古志。自來論《春秋》、《左傳》的關係,沒有比史公更深切有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