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知名科學家面臨性侵指控
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報導──知名免疫學家、退休前曾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國家衛生研究院擔任免疫學與病毒學中心主任的亞伯拉罕.諾頓.佩利納醫生,昨天被控性侵遭逮捕。
七十一歲的佩利納醫生面臨的指控,包括三項強暴罪、三項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兩項性侵罪及兩項危及未成年人的罪行。提出指控的人是佩利納醫生的養子們。
「那些指控都是假的。」佩利納的律師道格拉斯.辛德利昨天聲明:「佩利納醫生在科學界的聲譽卓著,備受尊崇,他非常希望盡快釐清現況,讓他回歸工作與家庭。」佩利納醫生曾於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理由是他發現一種延緩老化的病症,也就是「瑟莉妮症候群」。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有個名為烏伊伏的島國,在該國三島之一的伊伏伊伏島上,他發現歐帕伊伏艾克族的族人罹患此一病症,儘管他們的心智退化了,身體仍維持在很年輕的狀態。他們之所以不老,是因為吃了歐帕伊伏艾克海龜,於是佩利納醫生用海龜名來為該族命名。他發現這種海龜肉能夠抑制端粒──端粒這種天然酵素有分解端粒的功能,進而限制每個細胞分化的次數。受到瑟莉妮症候群(瑟莉妮是希臘神話裡永遠不死與青春永駐的月之女神)影響的病人,能活好幾個世紀。佩利納醫生初次前往烏伊伏國是在一九五○年,年輕的他隨同知名人類學家保羅.塔倫特,在當地各島做了多年的田野研究。此外,他也在那裡領養了四十三名小孩,其中多人是孤兒,或是歐帕伊伏艾克族窮困族人的兒女。其中一部分小孩目前正由佩利納照顧。
「諾頓是模範父親,也是天才。」長期於佩利納的實驗室裡擔任研究員,同時是其摯友的隆納德.庫波德拉醫生說:「我深信這些荒謬的指控一定會被撤銷。」
(美聯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九日)
知名科學家暨諾貝爾獎得主被判刑入獄
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報導──亞伯拉罕.諾頓.佩利納醫生於今天被判二十四個月徒刑,執行地點為費德列克懲教機構。
佩利納醫生曾於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理由是他證明一種原產於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烏伊伏國、如今滅絕的海龜肉,能抑制端粒,限制每個人類細胞的分裂次數。他發現,這種被稱為瑟莉妮症候群的病症,可移轉到包括人類在內的多種哺乳類動物身上。
獲准自由進出那些遙遠神祕島嶼的西方人寥寥無幾,佩利納是其中一位,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他陸續在該國收養了四十三名小孩,全都安置在他位於貝塞斯達鎮的住家。兩年前,佩利納被控強暴其中一個孩子,威脅其安危;指控他的人是他收養的某個孩子。
「這真是一樁悲劇。」路易斯.雅特舒爾醫生在佩利納醫生服務多年的國家衛生研究院擔任院長,他表示:「諾頓是個思想家與天才,我衷心希望他能夠獲得他所需要的治療與幫助。」
佩利納與他的律師目前都處於失聯狀態,無法評論此事。
(路透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
編者序
我是隆納德.庫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學術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隆恩。沒錯,如果你曾在報章雜誌上看到隆納德.庫波德拉醫生這個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聞報導的內容並非全都屬實──當然真實的成分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那些報導都是真的,而且我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與諾頓有所關聯(別忘了,若是在僅僅十八個月前,我根本不用提這件事),事實上我們相識已久,從一九七○年起,我就在他位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隸屬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實驗室工作了。當時,諾頓還沒拿到諾貝爾獎,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醫界掀起一陣革命,自此改變學者對於病毒學、免疫學,還有醫學人類學的看法。讓我自豪的另一點是,與他成為同事之後,我們也變成好朋友;事實上,我覺得我倆建立了一種最有意義的關係。不過最重要的是,歷經了過去兩年的風風雨雨,我很自豪我們兩人仍是朋友。當然,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有機會就能與諾頓講話或溝通,無疑地,他也不行。他不在身邊,讓我有一種奇怪而寂寞的感覺。大概十六個月前,我才遷居此地(也就是諾頓被判刑的一個月後),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過在自然的狀況下,我們居然會分開超過兩天以上。也許連一天都沒有想過。(當然,所謂自然的狀況是排除某些特例,像是偶爾和當時還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們各自去參加葬禮、婚禮等活動。即便不在一起,我還是設法每天與他保持聯絡,不管是透過電話或者傳真。)重點是,與諾頓談話、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經變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電視、看報紙一樣:儘管是瑣事,卻不會忘記去做,藉此確保生活按照常軌運作。但是,當這種節奏突然被打斷,給人的感覺比不安更糟糕,簡直是不知所措。過去一年半,我就有這種感覺。早上醒來後,我跟往常一樣把白天的時間過完,但到了晚上總是晚睡,在公寓裡閒晃,瞪著夜空發呆,心想自己是否遺漏了什麼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幾件平日瑣事核對一番,心裡想著信件是否打開看過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沒?門鎖了嗎?直到最後,我才帶著後悔的心情上床睡覺。每逢快要睡著,我才想起我這輩子的所有模式都改變了,接著感到一陣短暫的憂鬱。你也許會覺得此刻我已經能接受諾頓驟變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隨之改變,但我心裡的某個角落就是抗拒著;畢竟過去將近三十年來,他已然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覺得寂寞,諾頓的生活一定遠比我寂寞。當我想到他必須待在那種地方,我真是憤怒不已:諾頓不是年輕人了,身體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懲罰他既不適當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數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試著向朋友、同事與記者(還有法官、陪審團與律師)解釋,諾頓是個有同情心、聰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數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實上,過去十六個月來,我屢屢想起諾頓的許多朋友曾宣稱愛他也尊敬他,卻選擇背叛,並且這麼快就忘記他、遺棄他。有些朋友,諾頓認識且共事了幾十年,在他被起訴時就立刻消失。更糟糕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後便離開他的人。當時我才發現一般人有多麼不忠不義、滿嘴謊言。
不過,我離題了。牢獄生活讓諾頓感到最難過的一件事,應該是他必須勉強自己去適應單調的生活。我必須承認我有點訝異,他入獄不到一個月就開始抱怨生活無聊到令人難過。過去,諾頓跟許多累過頭的能人志士一樣,滿心夢想著在一個溫暖的地方住上一個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講,不用編輯或撰寫文章,不用教學,不用顧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閒時間,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過去,諾頓總是說時間就像一片大海,一面無邊無際的空白鏡子,而這個他稱為「大海時間」的美夢已經變成一則笑話,短短幾個字,代表著他目前沒時間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總是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用來種植熱帶蕨類植物。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讀一些傳記。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寫自己的回憶錄。不曾有人認為諾頓真會擁有所謂的大海時間,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時間,只是沒有溫暖的地方,沒有那種努力一輩子過後應得的安逸感,讓人覺得快樂而慵懶。不幸的是,諾頓有可能天生就是勞碌命;這陣子以來,他深受折磨(雖然如此,我得承認他會這麼想,很大一部分必須歸因於他是在不幸的情況下獲得這種悠閒時光)。在最近的一封信裡面,他寫道:
這裡能做的事不多,而且在某個時間點過後,能夠思考的事情甚至更少。我不曾想過自己會落到這一步田地,筋疲力盡,而且被放空了,不是放血,而是腦袋一片空洞。窮極無聊──事實上,過去我總以為如果有一段長時間的閒暇,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很容易把時間排滿。但此刻我已經瞭解,時間不是由一段段長時間的空檔組成:我們常說時間管理,其實剛好相反──我們只能用一件件忙碌的小事來填滿生活,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這似乎是充滿智慧的洞見。
儘管諾頓明顯看出自己的處境嚴峻,還是有些魯莽的人表示他應該感激自己受到的寬大處置,這種說法不但愚鈍,也很殘忍。其中之一是赫伯特.威斯特(雖不情願,但我在這裡還是把他的名字改掉了),一九八○年代初,他也曾是諾頓手下的研究員,他在前往倫敦參加會議的路上,去貝塞斯達鎮拜訪諾頓。當時還沒進行審判,不過諾頓已經被起訴,等於被軟禁在家裡,他收養的所有小孩也都重新安置。過去,我曾認為威斯特不會像諾頓先前的許多研究員那樣令人不耐,他在諾頓家待了大約一小時,問我想不想去餐廳與他共進晚餐。我不是特別想去(在我看來,他在諾頓面前邀請我非常不禮貌,畢竟諾頓不得離開住家),但諾頓說我應該去,他還有一些想完成的工作,自己一個人也不錯。
於是我與威斯特共進晚餐。儘管腦中一再浮現諾頓獨自待在屋裡的模樣,我們依然聊得非常盡興,提到威斯特的工作和他準備在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也提到諾頓遭到逮捕前與我共同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還聊起我們都認識的一些熟人。直到吃點心的時候,威斯特說:「諾頓老了很多。」
我說:「他的情況很糟。」
「是啊,很糟。」威斯特低聲附和。
「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說。
威斯特不發一語。
「太不公平了。」我又說了一遍,再給他一個機會。
威斯特嘆了一口氣,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角,姿勢做作而且很娘,像在賣弄他的英國氣質,令人厭惡。(幾十年前,威斯特曾經拿馬歇爾獎學金到牛津大學讀書,雖然只有兩年,但不管是社交或公事場合,他總是能夠很有技巧地提到那件事。)他正在吃脆皮藍莓餡餅,牙齒上一片藍紫。
「隆恩。」他開口說。
「嗯。」我說。
「你覺得他有做嗎?」威斯特問道。
當時我已經習慣被問及這個問題,也知道該怎樣回應。「你覺得呢?」
威斯特看看我,面帶微笑,看了一下天花板再看看我。「我覺得有。」他說。
我不發一語。
「你覺得沒有。」威斯特說,口氣有點驚訝。
接下來這句話也是我學會該怎樣講的。「他有沒有做無所謂。」我說:「諾頓是個偉大的思想家,我只在意這一點,而且也是我會對後人說的話。」
我們陷入一陣沉默。
最後,威斯特膽怯地說:「我想我該回去了,明天搭機前還要讀一點東西。」
「好吧。」我說。我們默默吃完甜點。
是我開車載他到餐廳的,付了晚餐錢之後(威斯特說要請我,被我擋掉了),我載威斯特回飯店。在車上,他數度想跟我閒聊,這讓我更憤怒了。
到了飯店停車場,我們杵在車上,沉默了好幾分鐘,威斯特欲言又止,我則是非常生氣,最後他伸出手,我握了一下。
「呃──」威斯特說。
「謝謝你來看他。」我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諾頓很感謝。」
「呃──」威斯特又說了一遍。我看不出他能否察覺我的言詞暗含嘲諷;我想他應該沒察覺。「我會想起他的。」
我們又陷入一陣沉寂。
「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開口往下說。
「他不會的。」我跟他說。
「但如果他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著說:「他會去坐牢嗎?」
「我不能想像他去坐牢。」我回答道。
「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堅持往下說,我則是想起過去威斯特當研究員時吃相有多難看,有多貪婪,還有他是多麼迫不及待地離開諾頓的實驗室,另立門戶。「至少他會有很多大海時間,不是嗎,隆恩?」這句話輕率無比,讓我驚詫到無法回應。我坐在那裡,目瞪口呆,威斯特對我微笑,又說了一句再見,下車離去。我看見他穿越飯店的雙扇門,走進燈光明亮的大廳,便重新發動車子,開回諾頓家,我晚上都在那裡過夜。之後幾個月,審判程序開始又結束,最後判刑結果也出爐了,但無庸贅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沒去看過諾頓。
但是就像我說的,沒有人同情諾頓的處境。實際上,他是先遭到大家的審判與唾棄之後,才在法庭上,被一群理應與他相提並論的陪審團團員審判與判刑──然而,那十二個人卻是如此無能(就我記憶所及,其中一個團員是收費員,另一個是做寵物美容的),像諾頓這種天才居然要由他們來斷定人品,由他們來決定命運,他不知作何感想?更何況,他們的決定就算不會全盤抹殺他過去所有成就的意義,但至少那些成就幾乎不再具有重要性。從這個角度看來,諾頓此時覺得沮喪、無聊、了無生趣,還有什麼好奇怪的。
關於諾頓這個案子的媒體報導,我也有幾句話要說,如果我沒有談一談報導內容的語調與範圍,似乎是件很蠢的事。首先我想說的是,由於諾頓犯的是強暴罪,各家媒體除了報導他那些外界已經知曉的少數生平事蹟,還浪費了許多篇幅加油添醋,完全罔顧真相,這一點也不令我意外。(無可否認,那些報導的確用三言兩語簡述了他的偉大成就,但只是讓他被控的罪行更令人髮指而已。)
還記得諾頓等待審判的那段日子,我陪他守在家裡(屋外有一群電視台記者鎮日聚集在草坪邊緣的人行道上,在蟲聲嗡嗡作響的夏日晴空下吃飯聊天,簡直像在野餐),在我們接獲的許多採訪邀約中(當然,最後他並未接受任何訪問),只有一家媒體(令人遺憾的是,那家媒體是《花花公子》雜誌)請諾頓寫下自辯之詞,而不是派某個見獵心喜的年輕作家,來為讀者詮釋他的生平與他被指控的罪行。(儘管仍在開庭,我覺得那確實是個好主意,不過諾頓擔心不管他寫什麼都會遭人利用,變成一篇對付他的自白書。他說得沒錯,我們也打消了念頭。)但是我也知道,當他發現他無法為自己辯護時,內心想必是悲憤交加。
諷刺的是,就在諾頓被捕不久前,他已經在計畫寫回憶錄了。早在一九九五年他便已處於半退休狀態,不用處理各種煩人的行政事務與實驗室瑣事。這並不代表他不再是實驗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人力,而是他開始允許自己用不同的方式規畫時間。
然而,諾頓並沒有機會把非凡的一生記錄下來──至少他沒辦法在他偏愛的情況下做那件事。但就像過去我常說的,他的心智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挑戰。所以,在他入獄兩個月後,也就是從四月起,我每天寫信問他想不想寫回憶錄。我跟他說,他的回憶錄不僅對人文與理工學界都有所貢獻,也能對有興趣傾聽的人剖白,藉此擺脫外界強加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我說,如果他願意,我很榮幸能幫他打字,做初步的編輯工作,就像過去他把論文提交給各大期刊之前,都會由我經手。我在信中說,那對我來講一定是個很迷人的計畫,或許他也會覺得有趣。
一週後,諾頓寄了一封短信給我:
我不能說我非常樂意把人生最後的這幾年用於說服別人,讓他們瞭解我並未犯下我被判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已經選擇開始撰寫你所謂的「我的人生故事」。我非常信任你。一個月後,我收到了第一批稿件。
在我邀請讀者瞭解諾頓的非凡人生之前,我想我應該以導論的形式先說幾句話。說到底,這畢竟是反映出某種問題的故事。
當然,諾頓說得肯定比我精彩,但在這裡我要先向讀者交代一些關於他的細節。他曾跟我說,他的人生一直到他離開美國、前往烏伊伏,才有了意義,而他在那裡的許多發現,也的確深深影響現代醫學的發展,讓他獲得諾貝爾獎。一九五○年,年僅二十五歲的他,初次前往位於密克羅尼西亞的神祕國度,人生自此大變,也對科學界造成了革命性的影響。在蕞爾小國烏伊伏停留期間,他跟一個後來被他命名為歐帕伊伏艾克族的「失落的部落」住在一起,其居住地是該國最大島,也就是人稱伊伏伊伏的「禁閉之島」。他在島上發現一種未曾列入文獻、也沒人研究過的病症,當地原住民深受影響。過去,在世人的印象中,烏伊伏國人民的壽命都很短,到現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這樣。但是,諾頓在伊伏伊伏島上認識一群島民,其壽命遠比一般人長,有的多活二十或五十年,甚至還有一百年的。此一發現之所以了不起,還有兩個理由:首先,儘管罹患此症的人身體並未老化,心智卻有衰退的現象;其次,他們的病症並非天生,而是後天的。
在諾頓發現這個病症之前,人類不曾如此接近過永生的目標,也未曾看過如此美好的願景會這麼快就從手邊溜走:他發現了一個祕密,又讓祕密流逝,整個過程不過十年光景。
關於歐帕伊伏艾克族的研究,讓諾頓在醫學以外的領域投下震撼彈:他與他們一起住了將近二十年,結果衍生出現代醫學人類學的新領域,他在那些年完成的著作,如今已成為許多大學課程的必讀書單。
只是他也是在烏伊伏國惹上了麻煩。烏伊伏國之旅對諾頓的許多意義之一,是他開始愛上孩童,這種愛戀持久不變。讀者們恐怕都不熟悉烏伊伏這個國家,它是一個地景壯美險峻的國度,那裡的一切都比我們的世界更為壯闊純粹,比我們想像的更令人讚嘆,不管往哪個方向走下去,總是能看到愈來愈壯觀的景致:一邊是無邊無際的水澤,靜止不動,色調強烈到令人無法久視;另一邊則是綿延不絕、層層疊疊的高山,山峰被淹沒在裊裊白霧之間。初到烏伊伏國,諾頓聘請該國人民當他的嚮導,帶著他去尋找未曾看過的景物。幾十年後,在當地人的請求之下,他帶著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代回馬里蘭州撫養,完全視如己出,提供他們在烏伊伏國不可能體驗到的教養方式。被他帶回國的孩子有許多是孤兒,都是一些生活條件其差無比、長大後的處境也不可能改變的嬰兒幼童。
在他自己還沒驚覺之前,他領養的兒童已經超過四十人。將近三十年間,他總計領養了三批孩童,其中許多人返回密克羅尼西亞,當上了醫生、律師、教授、酋長、老師與外交官。其他人選擇留在美國,出社會工作或留在學校裡。遺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貧窮潦倒,吸毒犯罪,不知所蹤。(任何有四十三個小孩的人,都無法期望每個小孩皆出人頭地。)如今,他們當然不再是諾頓的小孩了。而且在他們的選擇下,諾頓也不再是他們的父親:在他近年來陷入困境期間,他們幾乎全都放棄了他,這實在令人震驚。畢竟他提供他們住所,教他們說話,教養他們──他給了背叛他所需的一切工具,而他們也的確背叛了他。諾頓的孩子把美國與西方世界的一個現象看得很透徹;他們發現,只要指控某人是性變態,社會大眾多半會買帳,就算他是備受推崇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挺不住。這真是可惜;其中幾個孩子跟我還滿投緣的。
我想我該說清楚的第二件事是:我對這部回憶錄非常感興趣,但我並非故事主角。理由之一是,我這個人向來沉默寡言,也沒興趣述說自己的故事──畢竟這世界上已經有太多故事了。
不過,我想針對回憶錄的編纂工作說幾句話。身為編者,我所做的事其實很少。回憶錄的每個段落(段落標題都是我下的)都是諾頓入獄期間寫下分批寄給我的,前面都附了一封信,由於信件內容大都涉及隱私,我認為不適合收進回憶錄。同時,文字是一批批寫出來的,讀者偶爾會發現內容寫得自然而隨性,並且預設大家非常熟悉作者的生平與作品。既然我是最瞭解諾頓的人(這本回憶錄其實是在我的要求下寫給我的),每當我覺得需要提供額外資訊,幫助讀者瞭解諾頓的故事,我就有責任加上一些註腳。(偶爾為了彌補諾頓敘述的故事之不足,我也會加上自己的註解。還有,某些我覺得無法讓內容更為豐富或者不相關的段落,我也自己做主刪除;但是此類刪減不會影響諾頓勾勒出來的人生全貌。)
最後,我覺得我該試著回答諾頓開始寄稿子之前於信中提出的問題:我希望這本回憶錄的撰寫計畫達成什麼目標?我的想法一點也不複雜:不過就是為諾頓平反,並提醒大家,與那短短幾個月內他可能犯下也可能沒有犯下的罪行相較,他過去幾十年間的成就實在重要太多了。也許我太天真,但這是我該做的:如果我沒辦法盡力幫助一個為科學界與醫界貢獻良多的人,我將無法原諒自己。
隆納德.庫波德拉
於加州帕洛奧圖市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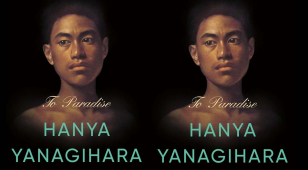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