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禪宗不立文字,主張教外別傳。但是,中國佛教的大乘諸宗之中,禪宗所留下的文字最多,在《大正藏》的諸宗部,禪宗典籍占首位,有一千五百九十九頁;天台宗以義理的闡揚著稱,卻占第二位,計九百八十二頁。於《大正藏》的「史傳部」,禪宗所占篇幅,與各宗比較也是首位,例如《景德傳燈錄》及《續傳燈錄》的兩部禪宗史傳,合起來便有六十六卷。再看《卍續藏》,所收中國撰述的部門內,禪宗撰述,占了十七冊多,共計八千二百八十四頁;其次為淨土宗的撰述,計不足四冊,共一千六百八十五頁;再次是天台宗,計一千六百零四頁。
可知,禪宗雖稱不立文字,並非不用文字,相反地,倒是善用文字來傳播佛法的一個宗派。「不立文字」的主張,出於菩提達摩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所稱:「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言教。」過了二百多年,至圭峰宗密的《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始有「然達摩西來,唯傳心法,故自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句。到了宋朝,楊億序道原的《景德傳燈錄》時,也說:「首從於達摩,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踐階梯,徑登佛地。」由於文字的教義,是用符號,形容事物整體或局部的觀念,並不等於事物的本身。如果以為文字即是文字所表達的事物觀念的本身,便永遠無法見到文字所要表達的事物了,所以達摩主張「不隨於言教」。可是,文字仍是一種最好的工具和媒介,為了使人達到不立文字的目的,最初還得用文字來做為通往悟境的路標。
以路標為目的地是愚癡,不依路標所指而前進,更加危險;以研究經教為唯一的工作而不從事實際的戒定慧三學的修證者,那是佛學的領域,不是學佛的態度。所以如永嘉大師起先研究經教,後來以禪悟而遇六祖惠能之後,便說:「入海算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一般人只見到禪宗大德訶斥文字的執著,殊不知,唯具有淵博學問的人,才能於悟後掃除文字,又為我們留下不朽的著作,引導著我們,向著正確的佛道邁進。故在悟前的修行階段,若無正確的教義做指導,便會求升反墮。因此,明末的蕅益大師智旭,極力主張「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的看法。
二
有人問我:何等人始夠資格學禪?有多少人由於學禪而得解脫生死,出離三界?我的答覆是:如果限定資格,那就不是平等的佛法;如果學禪不能出離三界,那就是說任何法門都沒有使人解脫生死的可能。因為禪是鍊心之法,是戒定慧三學的總綱;離戒定慧三學而別有佛法可修,那一定是受了外道的愚弄。
但是,禪的修持,在近世的中國,的確容易受人誤解,那是由於缺乏明師的鍛鍊指導,或者對佛法沒有正確的認識,習禪者便可能墮入兩種可憐可哀的心態:
(一)知識較高者,多看了幾則公案和語錄,往往會以自己的想像,揣摩公案和語錄中所示的意境及悟境,自以為懂得了並也悟入了。此即不假真參實修,也不必持戒習定,以為自然天成,本來是佛,即煩惱是菩提,即生死是涅槃。這種人目空一切,放浪不羈,自傲自大,不信心外有佛,不敬三寶,不信三世因果,或者倒因為果。一般人以為唯有利根上智者才夠資格學禪的論調,即是錯將這一模式的人當成了禪者。
(二)有一輩好求奇蹟的人,在修行若干時日的禪定之後,由於求功心切,定境無法現前,悟境更無?影,卻在幻覺與幻境中自我陶醉,例如自以為見光見華,見佛菩薩像,親見淨土,聞佛說法,以及種種奇象異境。而且逢人便說,他們是已有證悟的人,是具有異能的人,是親見聖境的人,乃至自以為是某佛或某大菩薩的再來。由於他們以幻覺幻境為實際的證悟經驗,也可能招致一些外道鬼神的趁勢而入,利用他們的身心,真的發揮若干彷彿是宿命、天眼及放光、噴香等的神奇現象,例如告知你的過去世曾是什麼、做了什麼,又向你預報吉凶等,非但增強他們自以為是聖者的信念,也能引來許多貪便宜、走捷徑以及好奇者的崇拜與追隨。一般被尊稱為新興宗教的創始者,在佛教則稱之為附佛法外道,大多是屬於這一類型。下焉者則成精神錯亂的精神病患者,身心均受損害,乃至無法過他們的正常生活。所謂修行禪定走火入魔者,即是這一類型的人。
至於正確的禪者,必定是戒定慧並重的切實修行者,不做浮光掠影的牽強附會,不為光影聲色的境界所動,不因身心的任何反應而起執著。此在《楞嚴經》、《摩訶止觀》等的?述中,均有明確的指示,否則便稱為魔境現前。中國佛教所用「禪」字的意思,是依戒修定,依定發慧的智慧行,它與布施持戒等的福德行,必須相應,始能成就。正像《阿彌陀經》所說,若人求生西方阿彌陀佛的國土,必須具備足夠的福德與深厚的善根方得。如果說禪不易修成,往生西方的彌陀淨土,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假如不能備積資糧,並且不斷地修行,學禪固然不能立即超凡入聖,修持任何法門都會同樣地無法速修速成,否則便與因果律相背了。所以,禪雖不是修行佛道的唯一方法,確是修行佛道的通途或要門,它以戒律的生活與禪觀的定力為基礎,智慧與慈悲──大菩提心的開發為目的。從釋迦世尊以來諸大菩薩及諸祖師無不以此方法而得成就。因為禪的修行方法,並無定法,若得明師指點,一切方法均可匯歸禪的入門方便,包括念佛、持咒、禮拜、讀誦等方法,並不限於靜坐或禪數。唯其用疑情、參話頭,乃是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方法。若能用任何方法使得身心寧靜之後,再以疑情來參話頭,智慧的火花,或所謂悟境,便會出現。當我們有過一次真正的失卻了身心世界的經驗之後,信心才會落實,氣質才會變化,菩提心才會滋長,慈悲心才會殷切。那時,你的心胸擴大、清靈,性格開朗、穩定,奠定了一個學佛者的人格基礎。
三
向來的禪者,以及重視實際修行的佛教徒,大都不重視思想史的演變過程,似乎覺得「禪」的修證方式和觀念,從來不曾有過變化,僅憑以因緣而接觸到的某一種或某一些禪的方法或禪的文獻,做為衡斷及修持的標準。縱然是聰明的禪者,涉獵了往古迄今的各種禪籍,多半也僅以同一個角度來理解它們,此與各還其本來面目的認識法,是有很大出入的。
因此,我已在《禪的體驗.禪的開示》一書中,以歷史的角度,介紹了〈禪的源流〉、〈從印度禪到中國禪〉、〈中國禪宗的禪〉。在本書中,則以抽樣的方式,將中國禪宗史上留下的禪門重要文獻之有關於修證內容及修證方法者,摘要選錄了二十四篇。時間的歷程,自梁武帝(西元五○二-五四九年在位)時代的菩提達摩,直到現代的虛雲老和尚(西元一八四○-一九五九年)經過一千四百多年,其間的禪風,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因人而異,變化多端,愈到後來愈圓熟,愈往上追溯,愈明其源頭的活水及其基本的形態。
比如幾乎盡人皆知,北宋以下,參禪與念佛合流,倡導禪淨雙修最有力的是永明延壽禪師(西元九○四-九七五年),明末的蓮池大師袾宏(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則將念佛分為「持名」與「參究」的兩門,皆以往生西方淨土為其指歸。持名即是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六字洪名;參究即是以大疑情參問「念佛是誰」。因此,晚近的淨土行者雖不參禪,而參禪者無不念佛;雖有淨土行者排斥禪門,真的禪者則殊少非議念佛之行,因為淨土的念佛法門,即是禪觀方法的一種,如予排斥,就像有人用右腳踢左腳,舉左手打右手,豈非愚不可及!
事實上,禪者念佛,早在四祖道信(西元五八○-六五一年)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門〉,即舉《文殊說般若經》所說的念佛法門,勸導大家照著修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說明禪門也用持名念佛。又引《觀無量壽經》所說「諸佛法身,入一切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觀點,說明禪門的「是心是佛」,淨土經典中,也早有此說。我本人亦常勸念佛不得力的人,先學攝心的禪觀方法,心安之後,專心持名,庶幾容易達成一心念佛的效果。因為念佛往生極樂者,一心念要比散心念更有力。一心念,心即與佛相應,散心念,則不能與佛相應;所以永明延壽的《宗鏡錄》內,數處提到「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的主張,那也正是《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所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的道理。要是六根不收攝,淨念不相繼,而想「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是不容易的事。故請淨土行者,不可盲目地非議正確的禪門修持。
四
本書的編著,是以「述而不作」的態度,介紹禪門的重要文獻,逐篇從藏經中抄出,予以分段、分目、標點,並且抉擇取捨節略而加上我的附識。一則節省讀者的時間,能在數小時之中,一窺禪籍精華的原貌。二則便於闡揚禪籍精義的大德,輕易地得到已有新式標點的教材課本。三則使得有心於禪之修證的行者,在見地上有所依憑。四則是向已是禪師或將要成為禪師的大德,在鍛鍊法將及勘驗工夫方面,提供參考的資料。當然,最重要的,本書的編著,是給讀者看的,更是給我自己看的。我將置之於案頭,攜於行囊,溫習再溫習。
一九八○年雙十節後一日序於中華佛教文化館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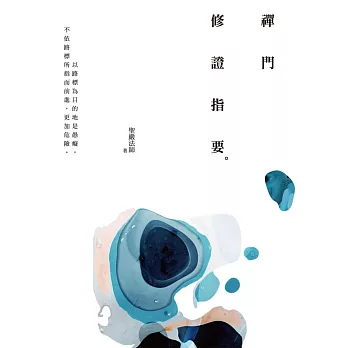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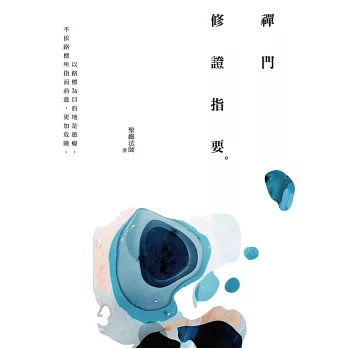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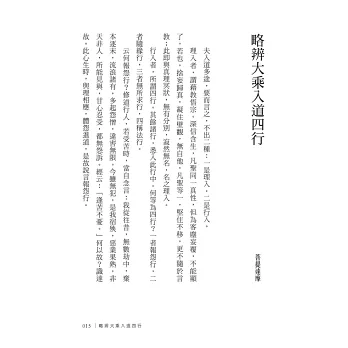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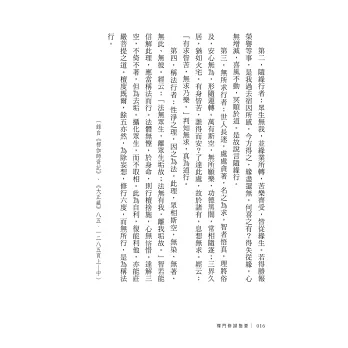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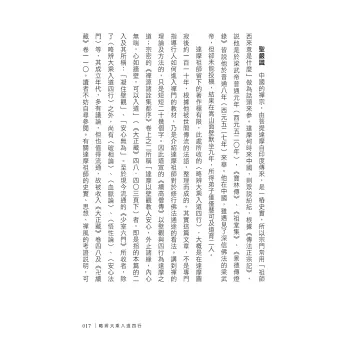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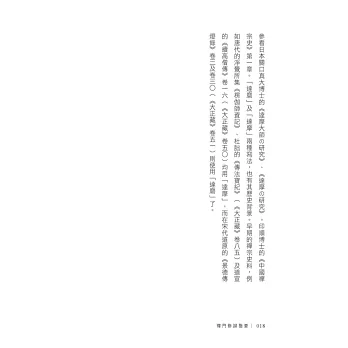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