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序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固然工商業也有過幾度飛躍的進展,但是農業始終是中國經濟的主要面貌。自從秦漢大一統以後,土地私有制下的小農耕作成為中國農業的基本生產方式。即使中間有過幾種其他的方式,終究還是變回了小農制。中國人口多,可耕地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往往不夠,因此土地所有權的分配成為嚴重問題。在儒家人本精神的理想下,國的社會改革,總是以均土地為一個大課題。另一方面,社會的變亂,土地分配不均亦為主因之一。治亂相尋,土地問題成為一個重要關鍵。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口號中,平均地權出現很早,足見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歷史上均田的嘗試也有過好幾次。可是每次都不能成功。只有在廿多年前在臺灣進行的耕者有其田成功了。這次土改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以技術改進與地權重新分配同時進行。
中國的精耕農業,發展甚早,在漢代即已達到很高的水平。此後精益求精,成為極高產的農耕方式。精耕制要求大量的投入勞力,而且每一階段都不能掉以輕心。為此之故,農夫必須有強烈的工作動機,才能充分的發揮精耕制的長處。中國的小農制可能是精耕制的必然條件。只有在農夫覺得自己的收穫歸自己的情況下,精耕方能真正有用。
臺灣實行的耕者有其田,正是強化農夫生產動機的惟一途徑。不過,若是農夫仍照傳統的耕作方式生產,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傳統的耕作方式已到達潛力的極限。突破這個極限必須借助於現代科技的成果,例如使用化學肥料及殺蟲劑;科學的選種、育種;農業機械的使用,和以現代的設備儲存運送。臺灣的農業在本世紀初期即接受了現代農業技術的第一次洗禮。廿多年前進行土地改革時,農復會的同仁們以其專業知識與技術,幫助新獲耕地產權的農夫,完成了更上層樓的技術突破。我個人以為,這次土改的成功,既實現中國自古以來嚮往的平均地權的理想,也承認了精耕農業看重技術的傳統,實在是中國邁向現代而又與傳統接榫的最佳成就。由此可見,走向現代,並不一定要與過去切斷,更不必一定要對過去「革命」。
餘姚沈宗瀚先生,是中國農業史上的重要人物。沈先生由農家子弟,接受現代農業教育,以其所學,奉獻給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工作。沈先生自己的育種工作為中國找到了優良麥種;他的推廣工作,使中國農夫接受了現代農業的成果。他在農復會參加了土地改革的大事,也主持了農業推廣,使這次土改不是單純的分配土地,而兼顧農業技術的提昇。沈先生的遠見,可以肥料換穀一事覘見。當時反對這個政策的人很多,但沈先生堅決的為這個政策辯護。由今回顧,這個政策在實施初期使農夫在作物未收穫前,可以不必「貴青苗」。幾千年來,中國農夫在「貴青苗」上吃盡大虧。而肥料換穀的政策使農夫終於可獲得現代科技的裨益,而不必擔心一時負擔不了這筆肥料款。這一環節的突破,農夫不必因舉債而再度面臨喪失土地的危險。沈先生的功勞又豈僅在為社會確實的掌握餘糧,以穩定糧價來安定社會一端而已。
沈先生一生奉獻給中國的農業,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與沈先生的一生事跡殊不可分。臺灣大學黃俊傑先生把沈先生的事跡編為年譜。這本書的內容不僅涵蓋沈先生的一生,而且也是一部中國現代農業史。此稿尚未付梓,而先生竟歸道山,從此不能再在他左右請益,悲夫。然而,先生的遺惠當永在臺灣農友心中,長誌不忘。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增訂新版自序(摘錄)
這部《沈宗瀚先生年譜》的初稿完成於1978年秋間,其後續有修訂,而於1981年八月印行初版。
這部書稿的撰寫,初非有意為之,它基本上是我的農業史研究的副產品。自從大學時代開始,我對農業與農村問題就產生極大的興趣,常到臺大農學院旁聽楊懋春先師所授的「鄉村社會學」等課程,希望從學術立場為我所熟悉、所關懷的臺灣農村,找尋一條出路。從1975年開始教書以來,我開始有系統地蒐集近代臺灣農業史的相關論著與史料。就在這個時候,我逐漸發現了宗瀚先生在現代農業史上的重要性。他和他所領導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與戰後臺灣農業與農村是分不開的。為了更深入地釐清這一段所謂「臺灣經驗」,我開始從長期所蒐集的史料中,挑出有關宗瀚先生的部分,加以整理排比,撰成年譜長編初稿。到了1978年夏間,《年譜》初稿長編已近殺青階段的時候,我才獲緣拜見宗瀚先生。
記得初次拜見宗瀚先生大約是1978年五月間的某一天午後。他的親切誠懇和藹可親,解除了見面前我的侷促與緊張。侍談之際,宗瀚先生告訴我,他自民國十六(1927)年任教金陵大學開始,所寫大部分的檔案、報告、公文、論文、筆記等都有留有副本。他並引導我參觀置於他辦公室,裝訂成冊的手稿和文件。我當時的欣喜若狂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於是,就利用這批資料,將《年譜長編》初稿很快地增訂成為定稿。在爬梳這批資料的過程中,我對沈先生一生治事為學那種一絲不苟,實實在在的風格,開始有了最親切的體認,衷心欽佩。
在我所親炙宗瀚先生的風範,以及在他逝世之後細讀他留下的大批史料之中,使我最敬佩的另一點,是他堅守農業心繫農民的心志。宗瀚先生從少年時代立志學習,一生奉獻中國與臺灣農業,這是人人共知的事實。正因為他堅持此志畢生不渝,所以,他在二十世紀農業史上,所留下的腳印是紮實而深刻的。近年來,我的研究工作轉到農復會(1948.10.1-1979.3.16)的歷史。我愈深入農復會的歷史,就愈瞭解沈先生所代表的其實正是早期農復會的工作精神──「以農民為主體」的精神。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農業問題的看法,至少有四個比較明顯的流派:第一是「農業派」,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生產力的提昇的問題;第二是「平教派」,認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在於平民教育水準的提高;第三是「分配派」,認為中國農業的落後乃是由於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第四是「折中派」,認為農業技術創新必須與制度改良同時並進才能解決中國農業問題。這四種意見,取徑固然有所不同,或從農業技術創新入手,或從農民教育著眼,或主張以地權分配為要務,或以技術與制度並重;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這就是他們對「農民主體性」都同樣地加以肯定。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認只有農民才是農業發展的主體,農民生活的提昇是一切農業技術改良的最終目的,而土地改革正是從制度面根本保障農民之不再受剝削。由於這項基本認知,所以,當1948年10月1日農復會創立,綜合以上四派見解時,「農民主體性」就特別受到重視。蔣夢麟曾特別強調農復會工作的根本原則就是以農民為依歸,他說:
「自地方及農民處瞭解彼等需要,而非教導彼等何者乃彼等所需要。因彼等所需,彼等自身瞭解最清楚也。由此一方針,故本會工作常在進步中,常從農民處獲得新的經驗。吾等不以先入之觀念推行工作,但虛心自農民處學習。此乃本會方針所以不斷進步之一重要因素。不問吾等之意向如何良好、計劃如何健全,倘不為農民所需要,吾等無法勉強使之實行。」
所謂「自地方及農民處瞭解彼等需要」,正是早期農復會最根本的精神之所在。沈宗瀚先生的一生所展現的正是這種以農民為主體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今日特別值得我們懷念,並發揚光大。遠在1979年,著名的經濟學家Erik Thorbecke回顧戰後臺灣農業發展的歷程,就指出1970年代末期的臺灣農業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未來何去何從,有待於明智的抉擇。十一年後的今日,臺灣農業仍在這個十字路口徘徊,但隨著1987年解嚴以後整個大環境的急速變遷,國內農民的政治自覺日益提昇,農民的主體意識日益成熟,他們勇於走上街頭,爭取最起碼的經濟人權;另一方面,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壓力,卻又日甚一日,美國三○一條款的夢魘,像一隻貪婪的蒼鷹始終盤旋在臺灣的上空;來自中國大陸的走私入口農產品,則嚴重的打擊臺灣農民已經江河日下的農業收益。1950年代臺灣農村的風和日麗,滿園春色,凌夷至於今日,已經變成雪冷霜嚴,秋聲蕭瑟。三十年前臺灣農村所見的幾點鷺鷥,一雙鸂鵣的景色,在今日的工業污染之下,已經轉變為枯井頹巢,磚臺砌草。如何在這種臺灣農業的困境中走出一片蔚藍的天空?這是我們當前努力的方向。所謂「述往事,思來者」,我衷心期望這部書稿的再版,能使我們在臺灣農業的道路上走得更正確、更紮實!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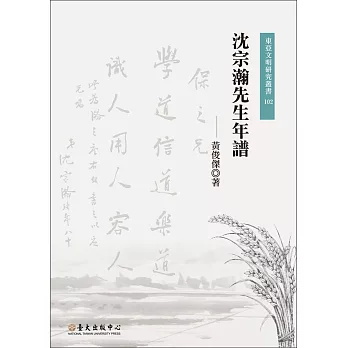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