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雨林的陌生來客──華萊士與他的《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
詹宏志
尋找華萊士
當代英國旅行作家提姆.謝韋侖(Tim Severin, 1940-)在他的一本名著《香料群島之旅:尋找華萊士》(The Spice Islands Voyage: In Search of Wallace, 1997,中文譯本由台灣馬可孛羅出版)裡,用了一段影像極其鮮明生動的描繪做為全書戲劇性的開場:
在一間以棕櫚葉覆頂的屋子裡,一位虛弱瘦削、面容憔悴的白種男人蜷曲在臥榻上,因為熱病而大汗淋漓且顫抖不止。時間大約是一八五八年的二月末或三月初,我們無法確定日期,因為這位病患做過太多田野調查,使得他的日記變得含糊不清,也可能是被熱病搞混淆了。他已在世界上最偏遠的一些島嶼上探險了三年半之久。他染過瘧疾,幾度瀕臨餓死邊緣;數次的熱帶性潰瘡使得他的雙腿不良於行,甚至只能爬在地上匍匐前進。他流浪的成果散落在他臥榻四周。床邊放著他的儲藏箱,那是用當地棕櫚葉編織而成,上漆後可以防水,裡面裝藏數以千計的死昆蟲。大部分是甲蟲,也有的是這地區令人嘆為觀止的蝴蝶標本。多數是訂好的標本,旁邊附注潦草散亂的詳細筆記。還有異國鳥類的乾皮和骨架,以及若干小型哺乳類的骨頭。病人還沒有時間剝皮和做乾燥處理的新鮮標本,則用細繩綁著倒掛在屋頂椽木下,或小心地存放在盛了水的墊盤中,避免經常跑來臨時工作檯掠食的螞蟻雄兵,將鳥肉或羽毛啣咬而去。這些未剝皮的標本在屋內散發著腐屍特有的惡臭,但病人對這種熱帶氣味已經習以為常,絲毫未加以理會。……
提姆.謝韋侖在書中描述的這位病人是三十五歲時的英國自然學者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他當時正流浪於歐洲人口中遙遠難及的「香料群島」,發掘並採集各種西方世界原來不曾知悉的動植物種,正確的位置我們也許應該說是今天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摩鹿加群島(Moluccas),作者形容這位病人華萊士是「新類型的自然學家」(這句含意深遠的話,我等一下還要試著加以延伸解釋),事實上提姆.謝韋侖正是被華萊士的歷史事蹟所吸引,想要用古船和古法「重蹈」一百四十年以前的華萊士旅程,追想華萊士昔日眼睛之所見,也重新體會華萊士陸地與海洋雙重的地理經驗。謝韋侖的旅行從「重造」一艘華萊士當年所用的土著船隻開始,一路追隨、反省、探索、發現,最後完成了一本包含了今古兩個旅行的雙重敘述,這本奇書對我這種嗜讀旅記、傳記成痴的讀者來說,簡直覺得好看到不行。
尋找演化論
但謝韋侖的故事為什麼要從那場熱病寫起?因為那場瘧疾熱病是科學史的關鍵時刻,它把標本採集者華萊士困在臥榻上,不能外出「執行業務」,他必須躺在床上等到「陣陣忽冷忽熱的痙攣結束為止」。昏沉躺著的華萊士想著十幾年來困惑著他的問題,這些問題從他一八四八年在南美洲亞馬遜河熱帶雨林中收集物種標本時已經開始,這些多彩多姿的自然世界彷彿扣問著他:為什麼世界上有這許許多多千奇百怪的動植物物種?它們的巨大或微小差異是怎麼來的?這些差異可有任何作用?有什麼普遍性的法則可以來了解物種與物種之間個別特徵的何以產生?
忽然間,昔日他在倫敦「職工學院」(Working Men's Institute)旁聽時讀過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的悲觀理論躍入腦中,讓他猶如遭到電殛,他試著把馬爾薩斯對人類社會的觀點代入生物世界之中,他發現自己竟然能夠回答自己的問題:「為什麼某些『物種』倖存而某些滅絕?就整體來看,顯然答案是最適者生存。最健康者逃過疾病死神;最強壯、最迅速或最狡猾的躲過敵掌;最佳獵人或具有最佳消化功能者可自饑荒中倖存下來等等。我突然想到這個自動過程必然會改善族種,因為弱者在每代中將被淘汰而留下強者。也就是說,最適者得以生存。」
華萊士掙扎從病床上爬起來,在陣陣發抖之間,他花了兩天時間把這個革命性理論寫下來,文章正文只有短短四千字,但卻是後來石破天驚影響現代科學最深的劃時代新觀念。他把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寄往英國一位他所佩服尊敬的自然學者,想知道這篇文章是否有發表的價值,郵件飄洋過海三個月後,遠在英國肯特郡那邊的收信者卻握著信紙因震撼而發呆,記錄者說他「近乎癱瘓」。
熟悉後來科學史發展的朋友讀到這裡當然已經知道,這位吃驚到近乎崩潰的收信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達爾文比華萊士年長十四歲,達爾文來到南美亞馬遜河流域調查生態的時間也比華萊士早十二年。自從參加「小獵犬號」(HMS Beagle)航行之後,二十年來達爾文已出版數冊極有分量的研究著作,朋友之間也陸續知道他發展出的「演化論」(有趣的是,也是受了馬爾薩斯的啟發),雖然沒有人知道他的理論究竟發展到哪裡,佩服他的朋友們卻都相信他一定會出版他的「曠世鉅著」。
但達爾文的「曠世鉅著」卻一直躺在抽屜裡(也只是他在一八四二年寫下的演化論草綱),他似乎頗畏懼這個理論對當時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衝擊,很想死後才出版這個研究結果(達爾文怕些什麼?有興趣的朋友應該去找顧爾德的《達爾文大震撼》來看),但華萊士捎來的信件卻使他發現,他一生的成就可能因為這位年輕人而一無所有。
達爾文慌忙寫信向學界老友包括地質學家萊爾(Charles Lyell, 1797-1875)和植物學家胡克爾(Joseph Hooker, 1817-1911)求救,兩位學術重鎮遂安排在林奈學會同時宣讀達爾文的論點和華萊士的論文摘要,那是科學史上一場震動人心的盛會。整個歐洲學術界因為這場學術會議的革命性觀點而翻天覆地,達爾文因此暴得了大名(他更趕在一年後寫完全書搶先出版,也就是後世所熟知的改變歷史的鉅作《物種源始》),可憐的華萊士遠在偏僻原始的馬來群島,他完全不知道那場學術會議和宣讀論文的事,渾然不知他的觀點已經震撼了全世界,更無暇站出來為自己的觀點做延伸或說明,使得「演化論」的創造者之名逐漸向達爾文傾斜,達爾文一開始對此還頗覺內疚,後來就慢慢大言不慚地只說「我的理論」了。
尋找天堂鳥
到這裡,我們也許可以回到為什麼謝韋侖說華萊士是「新類型的自然學家」的問題。 從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階級分明的社會裡,人們會發現華萊士的「出身」是很難成為重要學術突破發現的人,他來自家道中落的貧窮家庭,父親屢屢失業並不斷搬家,使華萊士十四歲就失了學。所幸十四歲的小華萊士在英國的帝國擴張中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土地測量員」(land surveyor),當時英國全境不斷追求鐵路與運河的建設,需要大量上山下海的土地測量員,華萊士隨他的哥哥自修學會了羅盤、六分儀、經緯儀的使用,也得到了這個經常要隨時流動遷徙、進入荒郊野外的工作,他對地質和動植物學的興趣,在這個工作裡得到最大的利益。他幾乎靠自修習得大部分的知識,譬如靠一本植物圖鑑,他就走入森林,現地學會辨識、採集與分類。工作與工作之間有空檔,他就到學校去旁聽或到公立圖書館去閱讀,這兩個好習慣改變了他的命運;在短期課程與旁聽中,他得知馬爾薩斯與勞勃.歐文(Robert Owen)理論,影響了他一生的觀點,而在公共圖書館借書的過程中,他無意中結識了生命中的貴人:一位重要的自然學者亨利.貝慈(Henry Walter Bates, 1825-1926)。
比起達爾文從小學到劍橋大學的一帆風順,連上「小獵犬號」所有的費用都由家裡所負擔(光是上船的自備儀器費用就高達六百英鎊,夠讓華萊士專心舒適地讀完大學了),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幾乎是當時學術成就的後盾,「三級貧戶」式的成功故事,在學術領域裡卻是前所未聞的。
但是華萊士找到一個新的途徑,他在一八四七年向貝慈提出建議,相邀聯合探訪亞馬遜河,探索沿岸的自然史,搜集物種與生態現象,以便「解決物種來源的問題」(toward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這是當時華萊士信上的原文,不可思議地已經包含後來達爾文名著的書名);但哪來的錢讓他們去探險呢?華萊士說,我們可以在倫敦販賣收集得來的罕見標本或複製品,用那些收益來支持探險的費用。這個前所未有的構想,不靠國家,不靠家產,一舉把「科學探險」(scientific expedition)轉換成「企業探險」(entrepreneurial expedition),也為窮人學術探險家找到了一條全新的突破性出路。
果然這個構想獲得大英博物館和倫敦標本代理商的支持,華萊士與貝慈因此展開了長達四年的巴西熱帶雨林的標本收集與生態調查(後來兩人分道而行,貝慈則滯留了十一年),兩人都在這趟旅程中收穫豐碩,建立若干學術地位。華萊士回到英國已是一八五二年的十月,他順利地出脫了手上的殘餘標本,也完成了他的《亞馬遜河與尼格羅河之旅》(Travels on the Amazon and Rio Negro, 1853)。這本書甚至引起達爾文的重視,兩人因此開始通信。 完成亞馬遜河之旅以後,信心與經驗使他成了一位成熟的科學家與探險家,華萊士有了更大也更個人化的野心,他的新計畫想「對東方群島的自然史進行更詳盡的調查」(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in a more complete manner)。
這個計畫把他帶到今天的新加坡、馬來半島,以及今天的印尼群島,讓他在海島與海島之間流浪了八年,讓他見到了成千上萬歐洲不曾見過的物種(他帶回兩萬隻甲蟲和蝴蝶,以及三千張鳥皮),也讓他敏感地體會到人種與文化上的差異與多元性(幾乎顯示出一位優秀人類學家的氣質),甚至他獨特的洞見也預言了文明人對生態的浩劫(這個觀點幾乎要再等一百年才被人類社會所熟悉);這趟旅程不僅讓他在病床上提出了石破天驚的演化論,也指出這些眾多島嶼的動植物分類其實有著亞洲與澳洲的隱形分界線(這條線後來就被稱為「華萊士」線,喜歡去峇里島旅行的國人應該知道,與峇里島一水之隔的龍目島,就分屬在這條線的兩端),這都是華萊士令人稱道的學術成就。而記錄著這趟不平凡的旅行的,就是這部不朽的作品《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紅毛猩猩與天堂鳥之地》(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1868)。
也許讀者應該自己體會這位科學家旅行者的不凡之處,但我要提醒大家這是一位氣質溫文、待人如己的旅行者,他不曾像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旅行者習慣挑伕成隊、僕役成群,他一向自己動手,對待土著猶如其他文明人。他是少數歐洲旅行者注意觀察當地民族的特性與文化,也能做出公平的描述與評論;他對自然界的喜愛尊重也見諸於許多細節,當他第一手見識到雨林中神秘的天堂鳥時,讚嘆於它的驚人美麗時,卻同時預言了它的滅絕,這段被後來環境保護者經常引述的話是這樣:
我想到從遙遠的年代以來,這個小生物依循自然法則,代代繁衍;在這片漆黑黝暗的森林中出生、成長和死亡,沒有文明人的眼睛注視著牠的活潑朝氣,或為牠浪擲的美麗感到惋惜,……如此精緻的生物終其一生必須在這片狂野荒涼、注定永遠無法開化的地區,展示牠的絕美魅力,讓人覺得悲哀。但另一方面,萬一文明人抵達這些偏遠的島嶼,而將道德、學術和物理知識帶進這片幽深的處女森林中時,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文明人將破壞自然界有機與無機間原本良好的平衡關係,即使只有他能欣賞這種生物的完美結構和絕倫之美,卻將會導致牠消失和滅絕。
自然科學的知識大概會不斷前進,達爾文與華萊士的貢獻大概也只是提供了一個進一步上升的巨人肩膀;但是隱藏在《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這本書背後的那位睿智溫文的旅行者,將會是值得讓我們一再回味、感嘆、學習、心嚮往之的永遠的旅行者。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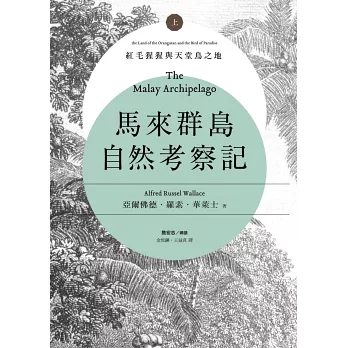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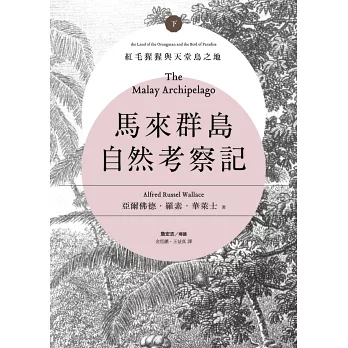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