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例外」的戰鬥姿態
在出版社詢問是否願意擔任涵榆新書的推薦人時,我感到十分的榮幸。除了本書的幾個章節在發表之初,我都作為親臨的參與者外,就此而言,這次邀約是一場友誼的邀約。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見證的邀約,見證著涵榆這些年來不論在思考還是行動上,都在進行著跨界的工作。不論是參與高教工會,捍衛教師勞動權益的抗爭,或者在其服務的學校,聲援學生校園民主的行動,還是投入哲學星期五的活動,與更廣大的公眾進行思辨及對話。在這些實際的行動中,涵榆將其化為對生命政治、公民運動、大屠殺、恐怖主義、安那其等議題的思考,就此而言,這絕對是一本結合著思考與行動的著作。應證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名言:「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
本書的書名雖為《跨界思考》,卻可將其視為由「例外」所貫穿的一本著作。在現今重視I級期刊、研究計畫和產學合作的年代,以不具任何計分效益的專書作為對公眾議題的回應,此為一例外。以演講錄而非研討會論文集結成書,讓本書不流於形式上的資料堆積,亦是例外。作為外文學門的學者,卻負有極深刻的哲學理論和思考,再是例外。而本書所涉及的議題,不論是安那其、附魔、倖存者、未到來的正義,在今日的出版品類型中,又為例外。
「例外」因此成了本書的姿態,這種姿態非但不是無力或邊緣,不是被排除的受迫者,而是一種戰鬥。這種置身例外的戰鬥,既是書寫,亦是哲學行動,戰鬥意味著作者以其自身及文本,作為一種充滿差異又具有張力的空間,劃出與既定事物的距離與界線,在此間性之中,差異對話在此展開,並挪移了各種界線。
於是,這種界線的挪移,展現了「例外」的第二個面向:作為對域外的探問與關切。這並非希望讓域外成為界內,亦非讓域外取代界內,而是問題化和基進化這道構成內/外的界線,它究竟如何構成?域外與界內是否是本質性的二極?是否有鬆動的可能性?邊界能推延至何種極限?然而,這實際上是一種雙重性而難以區辨的工作,即在詢問、思考域外何以作為域外之時,實際上也正在對界內進行相同的工作;在將邊界推延到更外部的邊緣時,實際上必須挖鑿更多更內部的問題。於是,內是外、內又不是外、內是內又且是外,內非外又且非內,一切簡化而慣常的二元邏輯,在這樣一種「例外」的戰鬥姿態下,顯得困窘而失效。正如同本書多處表示抗拒單一的、統整化的邊界,這除了讓我們能更多面向地思考問題、挑戰思考極限外,也讓我們對於未知(域外)具有更高的開放性,不論在面對現代醫學稱之為的病變、附魔,國際體系下的恐怖主義,主權概念下的非法居留或非法佔領。這些被稱之為「非人」、「非是」、「非法」,真的僅能從否定、負面的角度理解,還是必須問題化既有的「常態」、「已是」、「合法」等常規性的界線。
這種「例外」的姿態,亦非站在外部獨善其身或作為客觀觀察者,亦非躲匿於烏托邦的幻象,更非掉弄含糊不清的玄虛概念,而是在內部之中,一種拒絕被編碼的反叛行動。涵榆在此書中,展現了傅科意義下「說真話」(parrhesia),即它不是隨性漫談,也不只是自由表達意見或者傳授知識,而是承擔著引發爭辯甚至生命危險的風險,因為它挑戰著各種權威和多數人習以為常的觀點。西方哲學傳統與城邦公共事務密不可分,其不斷地介入並回應現實的問題,這個現實可能是公共議題、可能是生存處境,可能是社會結構、可能是與他人之間倫理關係,即一切因為差異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各種活動。也因此,這些思考不是抽象思維、不是將公共事務、社會關係、生存處境作為客觀存在的觀察對象,試圖從一套既有的學科知識解釋它,而是將這一切社會活動作為思考、發聲和行動的起點和基礎,是一件緊貼社會變動的實踐活動。正如同傅科在多部著作中表示(例如《古典時期瘋狂史》、《性史》、《知識考古學》或《安全、領土、人口》中有關生命政治和治理技術的歷史等等),他所作的工作不是科學實證定義下的歷史,而是要進行一種系譜式的歷史考掘,這並非現代實證科學下,發燒似地狂熱於檔案研究,也不是在已知、已說出的一套知識體系的同一性內部,以更多資料重複地證明或鞏固既有體系,而是透過那些已被遺忘、充滿塵埃的斷簡殘篇中,對固有形式進行一種話語的、思考的、行動的轉換,思考任何解構、重組的可能性,讓知識不再有內部結構的規律性和前序列。於是我們看到涵榆在本書中,如何戮力地、有意識的不再停留於文件蒐集,不再屈從於既有的學科論述規範,而是關注著台灣這塊土地的現實性,以台灣特有的歷史情境、社會力量作為思考、書寫和行動的鬥爭場域。
涵榆以「例外」作為戰鬥的姿態,思考、回應、撞擊台灣的現實性,作為讀者的我們,什麼是你我姿態呢?什麼又是我們的「例外」呢?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洪世謙
2017.05 於高雄西子彎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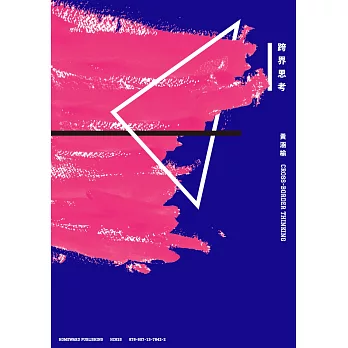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