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林語堂
我寫蘇東坡的傳記沒有別的理由,只是想寫罷了。多年來,我腦中一直存著為他作傳的念頭。一九三六年我攜家赴美,身邊除了一套精選精刊的國學基本叢書,還帶了幾本蘇東坡所作或者和他有關的古刊善本書,把空間的考慮都置之度外。那時候我就希望能寫一本書來介紹他,或者將他的一部分詩詞文章譯成英文,就算做不到,我也希望出國期間他能陪在我身邊。書架上列著一位有魅力、有創意、有正義感、曠達任性、獨具卓見的人士所寫的作品,真是靈魂的一大補劑。現在我能動筆寫這本書,我覺得很快樂,單單這個理由就足夠了。
鮮明的個性永遠是一個謎。世上有一個蘇東坡,卻不可能有第二個。個性的定義只能滿足下定義的專家。由一個多才多藝、多采多姿人物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組讀者喜歡的特性,這倒不難。我可以說,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
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一笑,這個結論也許最能表現他的特質。蘇東坡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能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這種混合等於耶穌所謂蛇的智慧加上鴿子的溫文。
不可否認的,這種混合十分罕見,世上只有少數人兩者兼具。這裏就有一位!終其一生,他對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實。他天生不善於政治的狡辯和算計;他即興的詩文或者批評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靈自然的流露,全憑本能,魯莽衝動,正像他所謂的「春鳥秋蟲聲」;也可以比為「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終捲在政治漩渦中,卻始終超脫於政治之上。沒有心計,沒有目標,他一路唱歌、作文、評論,只是想表達心中的感受,不計本身的一切後果。就因為這樣,今天的讀者才欣賞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過程中,最先也最後保留替自己說話的權利。
他的作品散發著生動活潑的人格,有時候頑皮,有時候莊重,隨場合而定,但卻永遠真摯、誠懇、不自欺欺人。他寫作沒有別的理由,只是愛寫。今天我們欣賞他的著作也沒有別的理由,只因為他寫得好美、好豐富,又發自他天真無邪的心靈。
我分析中國一千年來,為什麼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拜蘇東坡,現在談到第二個理由,這個理由和第一點差不多,只是換了一個說法罷了。蘇東坡有魅力。正如女人的風情、花朵的美麗與芬芳,容易感受,卻很難說出其中的成份。
蘇東坡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永遠教他太太或者最愛他的人操心——不知道該佩服他大無畏的勇氣,還是該阻止他,免得他受傷害。顯然他心中有一股性格的力量,誰也擋不了,這種力量由他出生的一刻就已存在,順其自然,直到死亡逼他閤上嘴巴,不再談笑為止。
他揮動筆尖,有如揮動一個玩具。他可以顯得古怪或莊重,頑皮或嚴肅——非常嚴肅,我們由他的筆梢聽到一組反映人類歡樂、愉快、幻滅和失意等一切心境的琴音。他老是高高興興和一群人宴飲玩樂。他說自己生性不耐煩,遇到看不順眼的事物就「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喜歡某一位詩人的作品,就說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他對朋友和敵人都亂開玩笑。有一次在盛大的朝廷儀式中,他當著所有大臣的面嘲弄一位理學家,措辭傷了對方,日後為此嚐到不少苦果。但是別人最不瞭解的就是他對事情生氣,卻無法恨別人。他恨罪惡,對作惡的人倒不感興趣,只是不喜歡而已。怨恨是無能的表現,他從來不知道無能是什麼,所以他從來沒有私怨。大體說來,我們得到一個印象,他一生嬉遊歌唱,自得其樂,悲哀和不幸降臨,他總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寫的就是這種風情,他成為許多中國文人最喜愛的作家,原因也在此。
這是一個詩人、畫家、百姓之友的故事。他感覺強烈,思想清晰,文筆優美,行動勇敢,從來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輿論的潮流而改變方向。他不知道如何照顧自己的利益,對同胞的福祉倒非常關心。他仁慈慷慨,老是省不下一文錢,卻自覺和帝王一樣富有。他固執,多嘴,妙語如珠,口沒遮攔,光明磊落;多才多藝,好奇,有深度,好兒戲,態度浪漫,作品典雅,為人父兄夫君頗有儒家的風範,骨子裏卻是道教徒,討厭一切虛偽和欺騙。他的才華和學問比別人高出許多,根本用不著忌妒;他太偉大,有資格待人溫文和藹。
他單純真摯,向來不喜歡裝腔作態;每當他套上一個官職的枷鎖,他就自比為上鞍的野鹿。他活在糾紛迭起的時代,難免變成政治風暴中的海燕,昏庸自私官僚的敵人,反壓迫人民眼中的鬥士。一任一任的皇帝私下都崇拜他,一任一任的太后都成為他的朋友,蘇東坡卻遭到貶官、逮捕、生活在屈辱中。
蘇東坡最佳的名言,也是他對自己最好的形容,就是他向弟弟子由所說的話: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難怪他快快活活,無憂無懼,像旋風般活過一輩子。
蘇東坡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個心靈的故事。他在玄學方面是佛教徒,知道生命是另一樣東西暫時的表現,是短暫軀殼中所藏的永恆的靈魂,但是他不能接受生命是負擔和不幸的理論——不見得。至少他自己欣賞生命的每一時刻。他的思想有印度風味,脾氣卻完全是中國人。由佛家絕滅生命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學和道家簡化生命的信念,他心靈和感覺的坩堝融出了一種新的合金。
人生最大的範疇只有「百年三萬日」,但這已經夠長了;如果他尋找仙丹失敗,塵世生活的每一刻依然美好。他的肉身難免要死去,但是他來生會變成天空的星辰,地上的雨水,照耀、滋潤、支持所有的生命。在這個大生命中,他只是不朽生機暫時顯現的一粒小分子,他是哪一粒分子並不重要。生命畢竟是永恆的、美好的,他活得很快慰。這就是樂天才子蘇東坡的奧秘。
本書不附加太多長註,不過書中的對話都有出處可查,而且儘可能引用原句,只是不太容易看出來罷了。所有資料都來自中文書,註腳對大多數美國讀者沒有多大的用處。書目附表中可以找到概略的資料來源。為了避免讀者弄不清中國名字,我將比較不重要的人名省略了,有時候只提姓氏。中國學者有四、五個名號,也有必要從頭到尾只用一個。英譯中國人名,我去掉惡劣的「hs」,改用「sh」,這樣比較合理些。有些詩詞我譯成英文詩,有些牽涉太多掌故,譯起來顯得怪誕不詩意,不加長註又怕含意不清,只好改寫成英文散文(譯註:中文版已「還原」成詩詞)。
譯序
宋碧雲
翻譯林語堂的作品,最大的困難就是人名、地名、書名……等專有名詞。因為背景是中國,專有名詞不能音譯,也不能意譯,必須查出中文的原名。翻譯《蘇東坡傳》除了這些困難,還要面對蘇詩蘇文的「還原」問題。蘇東坡生前留下一千七百多首詩詞,八百封信件,數不清的短記和題跋,不少奏議、碑銘、雜文,還為朝廷擬過八百道聖詔,別人談論他的文章更不計其數。本書所引的就有好幾百篇。某些詩文有篇名或寫作時間供譯者參考,查起來還不太困難。有些引句除了上下的括號,沒有任何「線索」可查,只好用死方法,依照林先生所列的參考書目一本一本、一頁一頁往下翻。除了手邊的《蘇東坡全集》、《宋詞》、《古文觀止》和《王荊公》等書,中央圖書館更成為我經常光顧的所在。有時候譯一頁原文,動筆的時間不到一個鐘頭,查書倒花了五、六個小時。
舉例來說,林先生的原序中說蘇東坡的作品都是真情流露,有如「the cries of monkeys in the jungle or of the storks in high heaven, unaware of the human listeners below.」照林先生的文風來判斷,他很可能是用蘇東坡本人的作品來形容他。但是這兩句話到底是詩,是詞,是碑銘,是書信,還是他的「文談」或「詩話」,我一無所知,甚至不能百分之百確定是他筆端的產物。我只好拿起蘇東坡的全集,一頁一頁做「地毯式的搜索」,打算查不到時再去翻閱其他相關的書籍。找了好幾個小時,終於查到蘇東坡給參寥和尚的一首長詩中有下列四句:「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後兩句正好吻合上述英文句的意思,前後也相當貼切。「找到了!找到了!」那份意料之中又像出乎意料之外的驚喜,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
說來我接譯這本書實在有點自不量力。我雖然學外文,從小也喜歡讀讀唐詩宋詞,自以為國學造詣總可以拿五六十分吧。蘇東坡家喻戶曉,他那些趣聞軼事人人都知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常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濃粧總相宜」、「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等名句,幾乎人人都會背。翻譯他的傳記還有什麼問題?於是一拍胸脯就接了下來。
仔細讀完原著,才知道問題不那麼簡單。書中引了幾百篇題跋、書信、奏議、詔命和詩文,很多我都沒有讀過。而且林先生聲明,書中的每一句對話都根據宋人或後人的筆記譯成英文。我雖不打算將這些對話「還原」成古文(讀起來太彆扭),至少也要查到出處,與英文對照翻譯,以保留原句的風采。引用的詩文則一定要「還原」,查考資料將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但是一股接受挑戰的狂勁卻使我不甘心打退堂鼓。反正林先生在書後列了一百多本參考書。了不起下「死功夫」,一本一本借來查嘛!於是一行一行譯,一頁一頁查,前後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整天埋頭苦幹,終於把這本書譯出來了。
我這本譯作不敢奢望「傳神」,只求儘量不出錯,但也只是「儘量」而已。如果有任何不妥當的地方,歡迎每一位朋友提出指正。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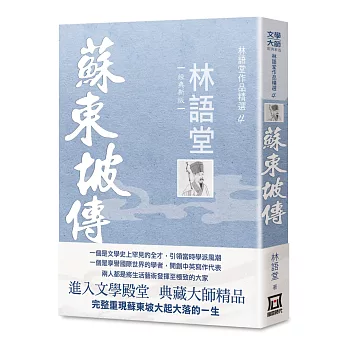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