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新的教育時代,挑起了世人興趣,因此,過去這幾年來,有幾本專門處理中國教育議題的英文書籍問世。其中,有瑪格麗特.波頓(Margaret E. Burton)的《中國的女子教育》(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亨利.愛德恩.金 (Henry Edwin King)的《中國教育制度的晚近重建》(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as Recently Reconstructed),以及胡燕蓀(Yen Sun Ho)的《西方視野中的中國教育》(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Western Viewpoint)。這些應時的著作,每本都闡述了諸多中國教育的面向,因此,在中國教育議題上,這些書都有參考價值。然而,世人還是十分需要一個針對中國公共教育制度之長期發展歷程的通盤說明,以全面理解古代和傳統教育制度在各個朝代下的興衰,以及現代教育制度在新民國政府下改革的局況。我的這份研究,企圖填補這個缺憾,同時,盡本人知識所能,首次代表中國向英語世界解開中國教育的糾結歷史。
在我處理這個研究主題時,資料的選擇和內容的比例分配,一直是難解的問題。儘管我自問謹慎,但讀者必然還是會發現,論文當中,有許多跟寫到的資料一樣重要的事,被我省略了;還有,某些部分應該要詳細說明,我卻以概述手法處理。即便有這些研究上的限制,我相信這份中國公共教育制度發展的整體概論,不僅僅對熱衷於中國教育的人大有幫助,同時也可以替未來的研究,照亮一條出路。
本論文的主要參考資料來源有二。其一,跟古代和傳統教育制度有關的資料,來自馬端臨的權威百科專書《文獻通考》;除了這本書之外,也包含這本書的其他補充資料;另外,我也參考了畢歐(Édou-ard Biot)的法文書《中國公共教育歷史文獻》(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1。其二,跟現代教育有關的資料,則得自中國的教育法令、教育部和其他教育機構的報告,以及目前各種官方或民間的教育期刊。至於另外的資料來源,已條列於參考文獻中。
在此,謹向以下人士致謝: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法林頓教授(Farrington)、孟祿教授(Monroe),以及希爾戈斯教授(Hille-gas);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德教授(Hirth);長老教會海外差會的賽勒博士(Sailer);還有審讀我手稿的同事余先生和陳先生。我特別要感謝負責我專科的兩位教授:也就是自始至終認真看待本研究的斯特瑞博士(Strayer)和法林頓博士(Farrington)。
郭秉文
西元1914年6月1日於紐約
孟祿序
東方對於西方知識的需求,是東方各民族知識分子階層強烈意識到的事。相對地,西方也想了解東方的知識、抱負以及成就,即便這種需求對於西方各國而言,感受並非同等強烈。中國,素來是東方最龐大,而且就諸多方面而言,也最為偉大的民族;郭博士的這本書,描述並記錄了他們晚近以來,為了取得西方知識,所下的種種努力。同時,這本書也清楚爬梳了中國文化和教育制度長期演進下的各個階段。郭博士的這份研究,增進西方對於東方的理解,可謂貢獻重大。
長期與中國人接觸的西方觀察家,若較能同理思考的話,會感覺到,雖然就看待事物的觀點和探討的方式,中國人和西方人有所差異,但在才智上,兩方並無根本的不同,也絕對不存在孰優孰劣之分。這種說法,雖然出於他們的自身經驗,但人類文化學家和社會學家,能提出學理上的支持:學者認為,東方與西方的差別,在於知識與技術,並非才智。只不過,由於中國人所操持的生活價值觀念,與西方民族的大為迥異,乃至科學知識與現代技術未獲發展。現在,中國人總算重新看待科學知識與現代技術,想必世界即將就要看到中國快速且根本的改變。
進步的產生,大抵靠的是智慧;而智慧,則是才智與知識的加乘,這就如同物理力是質量和動能的交互結果。中國民族,就像單單擁有質量,卻少了動能。中國人已有的才智,如果能夠加上現代科學知識,那麼,產生的結果,西方世界也只能佩服、加倍重視。
舉日本人為例吧!他們近來在軍備、商務、科學各方面努力獲得的成就,就是最佳的證明。也許,對於東方民族而言,自古以來就被看重的道德品格,以及社會實踐的成果,比起這些現代生活的產物,更具有本質上的意義,也更有基本價值。然而,西方世界的確對日本近來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而連帶地,東方世界也逐漸同意這樣的看法。
中國以和平手段維護了單一國家認同,長達三千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中國靠著同一塊土地的地力,就能維繫其組成龐雜之黎民百姓的生計,反觀西方民族,才不到幾百年,耗盡了自己土地的地力。這個國家除了創造出許多最具影響力的現代發明,如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之外,也發展了日常生活可見的機械工藝和商貿能力,足以令人敬佩。中國絕對有能力,利用西方世界開發的方法,發展出一番成就。中國人若把現代科學知識,加到他們在農業、商貿、工業、政治、軍事方面已有的能力上,必能以其形而下的毅力和形而上的道德為基礎,傲然有成;這將使得西方世界不再無知、冷淡、充滿偏見地看待有關中國的一切事物。
郭博士的這本書,不僅讓中國人更明白其眼下肩負之任務,也讓西方世界更了解東方正在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關乎東、西雙方,而我們期盼其結果能創造雙贏。
保羅.孟祿(Paul Monroe)
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
編者序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這是《說文》對這兩個字的解釋,二字成詞,指的是教誨、培育,是上對下的一種關係,有一種規範性、引導性;惟這個詞,古代並不多見,用得比較多的是「教」和「學」,《論語》的「有教無類」、「學而時習之」、「不學詩無以言」等;《孟子》有「易子而教」;《禮記》有著名的〈學記〉,談「教學相長」;《荀子》有〈勸學篇〉,論學習的重要及態度、方法、目標等。學而設官、設校,便與制度有關了,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即旨在論教育制度在中國之沿革史。
郭秉文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學博士。學成返國後,協助籌辦南京高等師範學院,爭取在南高的基礎上設立東南大學,並任校長。中央大學校史,上溯三江,年齡從南高算起,今已超過百歲。在校史上,郭秉文是一位奠基者,在他主持下的南高和東南大學,制度完備,名師雲集,絕對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學,特別是有二項創舉影響很大:其一是開放女禁,招考並錄取女大學生;其二是創辦暑假學校,向社會開放。以今天的角度來說,大學公共化、大學的社會責任,郭秉文早已在實踐。
《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原是他以英文書寫的博士論文,一九一四年在哥大教育學院正式出版。一九一六年,第一個譯本在中國出現,是周槃用文言文翻譯的;此後有二○○七年的福建教育出版社版,列入「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名著叢編」;有二○一四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版,列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由於郭秉文專業教育學者及卓越教育家的雙重身分,此書在中國教育現代化及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上,都影響深遠。
根據本校中文系李淑萍教授〈中大「秉文堂」溯源〉一文所載,在郭秉文曾孫甥女徐芝韻女史的努力下,近年來有關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教育事業的研究,頗為熱絡,這也間接促成了《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在台灣的新譯及其出版,譯事委請畢業於中大英美語文學系的沈聿德負責,李淑萍老師且做了詳細的校訂,由中大出版中心出版。這一方面表示中大對老校長的敬重,另一方面也說明郭秉文這本白百年前的教育學專書,至今仍富參考價值。
這是一部史書,從上古到周秦,乃至從漢到清,是前三章的內容;第四章是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第五章是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第六、七章即「現今」(民初)。可以看出,郭秉文把重心擺在晚清民初,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關鍵年代,中國在抵禦外侮的屈辱與尋找出路的內部鬥爭中,「教育」成了翻轉國家命運的關鍵。
郭秉文以批判的角度,全面考察公共教育制度在中國從古到今的發展,他看出了教育和國家發展的關係,指出中國之所以落後和積弱不振,和教育欠缺「具體」和「實用」、欠缺反覆試驗、和論證推理有關;在教育權責上,一定要盡可能避免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極端化;在課程的規畫上,要提供新世代多樣的機會,要排除萬難讓他們接受基礎科學訓練、學習如何精確觀察並詳實記錄;在教學實務上,不能過分強調背誦,要改善方法,訓練學生觀察力,學習各種技能,應用在問題的解決上。此外,他對於女子教育有願景,對於師資之培育,則有很大的期待。
台灣政治解嚴(1987)迄今的三十年間,教改喊得震天價響,政府被民間逼得往前走,步履蹣跚,亂象紛陳。現在,不論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問題都很多,這個時候,《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文版在台灣出版,應該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借鏡和啟發。
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暨出版中心總編輯
李瑞騰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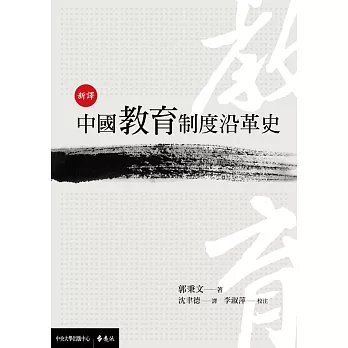
















































































































![(4/10開)Nintendo Switch 2主機包含《瑪利歐賽車世界》盒裝版 [台灣公司貨]](http://im1.book.com.tw/image/getImage?i=https://www.books.com.tw/img/N00/181/32/N001813288.jpg&v=67fdd34ak&w=210&h=210)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