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生命中的壯闊平原
作家的生活是枯燥的,幾乎說不出什麼來,但是,也有一點好,在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可以用一部又一部作品的書名來命名已逝的時光。舉一個例子,二○○三年一月至二○○五年七月,我生命中的這兩年零七個月,它們平靜如水,可它們有一個壯闊的名字,叫《平原》。
我的生日在一月。每年的一月我都是神經質的,有不可遏制的體能、想像力,當然,還有不可遏制的表達欲望——《青衣》動工於二○○○年的一月;《玉米》動工於二○○一年的一月;《玉秧》則動工於二○○二年的一月;到了二○○三年的一月,《平原》又上手了。我曾經用誇張的、玩笑的語調尋問我遠方的朋友:「為什麼一到冬季我就這樣才華橫溢的呢?」
其實不是「才華橫溢」,是恐懼。生日臨近,我的心智,我的肉體,它們對「時光」就有了異乎尋常的敏銳,我能感受到「時光」對我的洞穿。「時光」是尖銳的,也是洶湧澎湃的,這個世上沒有比「時光」更加倔強的東西了,它義無反顧,一去不回頭。
我很小的時候對「時光」就有了敬畏。因為敬畏,所以恐懼。因為恐懼,所以愛惜。因為愛惜,就有所企圖。我的有所企圖無非就是做點什麼。是啊,做點什麼。做點什麼呢?我只能尋找一些虛空的東西來陪伴我——我的認知,我的感受,我的激情,我的語言,我的想像,我的表達。
在我的書房裡,我不再恐懼。在書房,我可以笑傲我的時光。你去吧,你來吧。無論你對我做了什麼,我愛你。
《平原》描繪了一九七六年這一個特定的「時光」。當我在二○○三年一月回望一九七六年的時候,不恰當的野心出現了。我渴望包餃子。我渴望一巴掌把一九七六年拍扁了,然後,把我對「文革」所有的認識都包裹進去。在《平原》當中,我描繪了一個叫「王家莊」的地方——那也是《玉米》的人文地址——謝天謝地,寬容的朋友們已經把「王家莊」放置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地理版圖上了。那不是一塊「郵票大的地方」,充其量,那只是一個「芝麻大的地方」。這地方為什麼叫「王家莊」呢?原因很簡單,這地方姓「王」,它是民主的死角,自由的死角,也是尊嚴、同情、悲憫和愛的死角。它奉行的依然是「王道」。
作為一部「批判歷史主義」的小說,在小說的結尾我寫到了一條狗。這條狗是一個重要的「人物」。牠是狂犬。在一九七六年的冬季,牠被打死了。牠在臨死之前咬了男主人公端方一口。當我寫完《平原》的時候,我在二○○五年的盛夏推開了我的窗戶,我望著窗外,特別想知道,端方,你在哪裡?你在做什麼?你的健康有異樣嗎?你的傷疤是否放射出刀鋒或冰塊一樣的光芒?
在這裡我必須要說一說三丫,那個不幸的女孩子。我在這裡把她專門提出來,也許不是因為這個人描寫得成功。這個人物是《平原》的支撐點。從小說結構的意義上說,她不是。但是,在我的情感上,她瘦弱的身體一直支撐在我的內心。為了描寫她,我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從技法上說,她並不難寫。是我害怕她。我害怕在我的小說裡和她面對面,我只能停下來,一次又一次停下來。當她被我「寫死了」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個人作為小說家的不潔。可我沒有辦法。我無能為力。柏拉圖說,藝術家是不道德的。是的,作為《平原》的作者,我感受到了藝術家的鐵石心腸。這是代價。
除了端方,三丫,除了「王家莊」的那些農民,我在「王家莊」還安置了一些特別的人物,那個叫吳蔓玲的知青,還有那個叫顧先生的右派。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讀者朋友們也許可以發現,他們和以往的「知青」和「右派」是有所區別的。我珍惜這種區別。這種區別並不是來自於我的認識才能和文學才能,我把它歸功於理性的進步。
現在是二○○七年的夏季,我已經在寫另外的一本書了(這本書開啟於二○○七年的一月)。就在這樣的時候,這本書在臺灣刊行了。我是欣喜的,也是感激的。它使我獲得了一次回望的機遇。我衷心地感謝九歌出版社,衷心地感謝這本書的責編薛至宜女士。
世道變了,我當然知道這樣的書早就不合時宜了,可我還是期盼著臺灣的讀者能夠喜歡。我在南京感謝你們。
畢飛宇 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於南京寓所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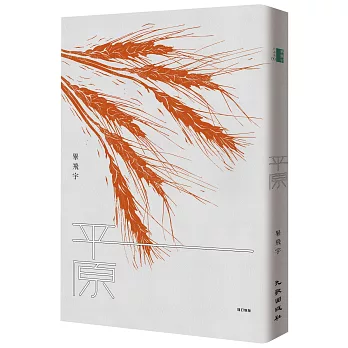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