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
不能動一顆棋子
八年前我考進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在教室裡只是一席蘋果臉的大一新生其中一個。可能就是第一節現代文學課上,張均老師課上的投影片出現了下面幾行詩:「一幅色彩繽紛但缺乏線條的掛圖,/一題清純然而無解的代數,/一具獨弦琴,撥動簷雨的念珠,/一雙達不到彼岸的槳櫓。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他讓第一排第一個學生猜這首詩的名字是什麼,猜不對的就輪到下一個。輪了半個班級,都沒有人回答正確。有人說「彼岸」,有人說「等待」,輪到我時,我站起來說:「思念」。結果我答對了,這是舒婷的名詩《思念》,我那時並沒有讀過。我並不喜歡她充滿讓步的低微口吻,雖然全詩沒有思念二字,卻都是在給「思念」穿衣服。如果是茨維塔耶娃,這首詩的題目和第一句都會是「我想你」。
但那時,一個十八歲的姑娘(或許還暗戀著誰!)還沒完全放下席慕蓉,還是被舒婷的這幾句感動得眼睛有點濕潤,甚至覺得自己就是舒婷的知音吧。現在我對詩的選擇更嚴格了,但也喪失了許多這些粗礪的感動,這幾乎是每一個長期讀者必然會經受的一種損失。或許過幾年,我回頭看這本詩集裡的作品,也會產生相似的尷尬。幸運的是,在這種尷尬發生之前,有機會讓我將它們付梓。至少就這些沒被我刪掉的詩作來看,它們並沒有比我稚嫩。詩中讓人欣賞的詩質:機智、剛烈、敏銳,對應在我的日常性格裡卻是難以相處的種種缺點:狡辯、粗暴、神經質。正是由於這種偏差,我寫得很少很慢,因為詩的語言狀態並非我的日常狀態,我能做的只是觀察和等待,會有一些經驗性的句子突破情緒的重圍,顯露出來。這就是我的寫作方式,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放棄虛構、放棄設計、放棄漂亮的詞語,只是我的經驗還是遠遠不夠去填這些空檔。
四年前剛到台灣的時候,我最先迷戀上的是熱帶喬木寬闊的葉子。清大郵局旁邊的橡皮樹葉子,大如帽子,擲地有聲。周夢蝶的詩〈積雨的日子〉寫的就是被一片手掌大的葉子打在肩上後,彷彿故人拍肩重逢的錯覺。這是在南方才有的感受,北方的落葉太輕太乾燥了,已經沒了問候的力氣。第一年我撿了一百多片葉子回去,逐一裝在透明的自粘袋裡,貼了滿滿的一牆。我不知道它們大部分的學名是什麼,可是我都給它們標上了名字,有一片變葉木的名字叫「河流的下午」,有一片斑斕的楓葉叫「世界地圖」,這種命名的遊戲,是和自然事物間樸素的對話,也是感受力的保養。但事實沒這麼簡單,被我保存、命名後的落葉,在牆上繼續進行它們的枯萎。如果你剛好也讀過魯迅《野草》中的那篇〈臘葉〉,就知道,發現原來自己好心收留被大自然萎棄的事物,也沒能阻斷一絲一毫它們與歲月同盡的進程。
這一面琳琅滿目的葉子牆,很快就面目全非了,可我沒有將它們取下來,這本詩集中的大部分詩,都是在這些葉子牆前面寫下來的。對著這它們看得久了,會覺得自己是在「格」這一面牆。就像如果你得在一片窗戶前早晚工作,對著一面無勝可言的窗景過上幾個小時,也會讓你覺得是在「格」那面窗子。
弟弟小時候學下盲棋之前,要從殘局開始練起。他坐在棋盤面前,手不能碰棋子,要在腦海裡把這盤殘局可能的走法都算盡。殘局練好了,再學著去「格」中局,中局練好了,才能「格」開局。有時我走過他的棋盤,於我是毫無變化,於他已經是另一番景象。我是在這一面葉子牆前,才養出這一個「不能動一顆棋子」的念頭,滿足於所見即所得,所得非所有。這也不完全是一種無力感,而是要讓一面風景熟悉到成為你性格的一部分,靠的不是浪漫的持續的旅行,而是靠這樣枯燥的固守。關於你的困惑,你眼前的已知條件就這麼多,它們只會造成局面,不會提供答案。如果你再去看舒婷的那首〈思念〉,你會發現,那首詩多像在羅列一個個已知條件,說的就是「不能動一顆棋子」的心情。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覺得我這些保守的、晚熟的文字不值得獲得什麼讀者,總覺得無論在寫作還是學業上,再晚出成績也無妨,可是到時我想要與之分享的人很可能不在了,為了這個,我也不應該太過懶惰。這篇後記之所以寫得有些傷感,是因為我想把這本詩集獻給她的那個人,已經在半年前去世了。
謝謝這幾年鼓勵我幫助我的前輩老師,是他們讓我在台灣感受到無與倫比的親切。謝謝永遠搞不清楚我在做什麼的爸媽,總是那麼盲目地支持我。謝謝老楊總是提醒我寫的詩還是太做作。
帕麗夏
二○一七年八月 於汕頭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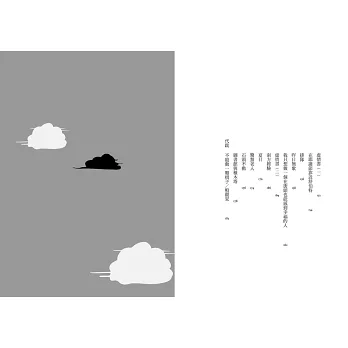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