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封來自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信
溫又柔
即使是今天,我的中文程度仍然相當低落。如果幸運碰上有耐性的人願意忍受我,那麼至少對答還說得通。但要是必須聊比較深入的話題,那我只能舉手投降了。而且說到我會講的中文,我所知的語彙和使用方法都非常有限,有時或許會讓人覺得太過單純或幼稚,很明顯地並不符合我的年紀。
相反的,使用日語對我來說,卻絲毫沒有任何障礙,儘管有時碰到稍微難懂的文物,必須要花一些時間去解讀,但是我卻有自信不會動搖或驚慌。有些時候,旁人甚至會佩服地這麼說:「妳的日語比大多數日本人都還要流暢呢。」
在日本長大的過程中,我上的是日本當地的學校,周遭的環境裡除了自己之外,全都是日本人。一回過神來,才發現我竟然成長為一個「理所當然地使用著日語」的人了。沒錯,就像是成了一般普通的日本人一樣。
如果我是日本人的話,大概就沒有人會誇獎我:「妳的日文真好」了吧。畢竟日本人說日文是很理所當然的事嘛。但因為我是台灣人,反而經常有人這麼問我:「妳的中文怎麼說得這麼差?」
明明是台灣人,日文能力卻比中文能力好得多。
明明不是日本人,卻只會日文。
這樣的我,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呢?
自從某個時期開始,我便經常思考自己與日文、中文(以及台語)之間的關係。
接著,我又以這個問題為核心,開始寫起了小說。
誠如我的上一本小說《來福之家》所收錄的兩篇作品,本書也是這種嘗試的一環。
天原琴子、吳嘉玲、龍舜哉。
根源自台灣、戰前中國大陸,並在日本成長,他們為了學習父親、母親,抑或祖父母的「母語」,前往了上海。
日本與台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日語和中文、普通話和華語、北京話和台灣話……擺盪在「國」與「國」之間,他們各自摸索著自己的生存方式,而這些人正如同我的分身一樣。
我希望對「和他們一樣」,以及所有「像我一樣」的人傳達一個訊息:
出生的國家、長大的國家。
父親的國家、母親的國家。
祖父母曾經待過的國家、從父母親那一代開始生活的國家。
你不需要站在這麼多個國家之間,煩惱著自己的母國究竟是哪一個。
因為這些國家,都是你我的母國。
我們站在這些母國與母國的中間點,從這裡為起點,我們可以前往任何地方。
繼《來福之家》與《我住在日語》之後,本書也能透過聯合文學出版,讓我感到無限的喜悅。
──「母語」總是會被人解讀為「傳承自母親的語言」,但是這個「母語」到底是不是只能有一個呢?我覺得小孩子的「母語」是可以由很多種語言所構成的。
在小說的結尾,當我寫下了這些「成為了天原琴子意識覺醒的契機」的話時,這部小說尚未寫到最後的時間點,但我就確信了,如果這部作品要翻譯成中文的話,那麼翻譯者就必須要找郭凡嘉。
一開始我們是以原作者和翻譯的身分相識,現在則成為了我敬愛的友人。她理解並接受了我的想法,爽快地接下了翻譯的工作,讓我衷心感謝。
或許有一天,某個人會把這本書和前兩本放在一起,稱作我的「初期三部曲」吧,而這初期三部曲中最後的一部作品《中間的孩子們》,現在即將送到台灣人──但是到底誰才是台灣人?──的手中,或許不光只是台灣人,而是所有在台灣、在中文環境中長大的所有人們、再更進一步地說,甚至是所有能夠讀懂繁體中文的讀者手中,一想到這件事,一股新鮮的力量就不禁從我心底湧現而升。
這股力量正是督促著我繼續寫下去的動力。
我要用這種包含著中文與台語、我獨特的日文,繼續寫下去。我會站在日本與台灣的中間,為了打從心底需要我的語言的「你」,繼續寫下去。
二○一八年四月吉日於新綠耀眼的東京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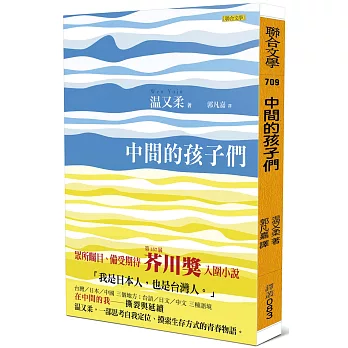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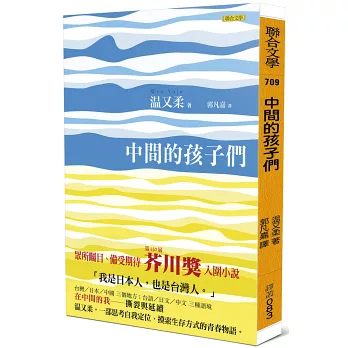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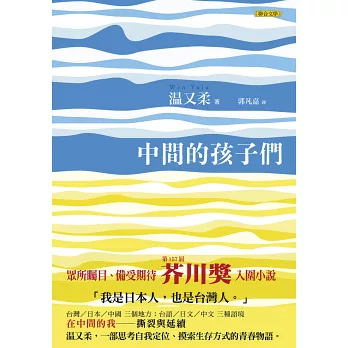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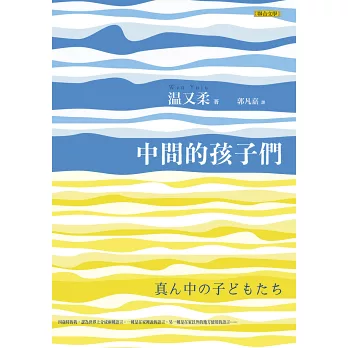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