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嗳嗳含光——序王嘉澤的詩集
趙衛民
詩總是靈魂深處的回聲,歌德說:「靈魂的喫苦受難,使文學成為必要。」靈魂來自於在經驗中獨特的感受,沈澱在我們的回憶中。
青春期或者窖藏著我們人生的原始動力,敏銳與堅持就成為最珍貴的靈魂財富。尤其在青春時期,帶著銳氣與活力,面對著未來眾多的可能性,尚未成熟的生命,卻得做出影響一生的選擇。青春期的艱難,恐怕對喜歡文學卻在企管系就讀的嘉澤,體會尤其深刻。不過,青春期的光陰雖禁不起浪費,但哪個人生不是邊走邊調校準星的。這些選擇過的生活方式,終會成為生命深處的回聲。
我在嘉澤的詩中,讀到的正式孤獨的聲音,這種聲音難能可貴,在日常的閒談與浪語中闢出一方寧靜,且令人回味。
在第一首〈樂園〉中:
夏日喧鬧的結束了
葉子紛落下來
詩句相當簡淨,葉落告別了喧鬧,在句尾自有「了」與「來」雙聲的呼應。時序的更易,只是時間的綿延(duration),故而:
長生不老的宇宙啊
陽光總是斜的
時間的循環不會死亡,宇宙不斷進化。陽光的偏斜是時間的推移。
他們建造許多屋頂
搭起一座花園
屋頂是大自然庇護人間的居住,因為嘉澤的樂園是人間的花園,季節的花園,故而:
秋天時是黃色
冬天是白色
嘉澤的詩在簡淨的詩語中,已構成獨特的風格。在第二首〈淵與丘〉中:
短暫的沈默與光
永恆而寂寥
卻是我想說的
如一堵虛牆 如空的魚網
緘默
像心懷秘密的孩子
大量的寂寞,折射著詩的靈光。語言的詩化超越了日常溝通的工具性與目的性。「虛牆」任一切事物穿透,「魚網」並無捕魚的現實利益。我特別喜歡末二句,但「緘默」與第一句的「沈默」,兩個「默」字重複,宜改為「緘口」。詩人天真的言語,總是寂靜之聲,海德格所謂「沈默中的金鈴聲」。而最後一句已捕捉到詩心之所繫:詩人的天真之眼,正是玩味一切流動的意味,只有「孩子」才能超出現實的功利。
我也喜歡〈卵〉這首,通篇美好,充滿活躍的想像,甚至有這樣的警句:
我們走在街上
如未乾的顏料
城市總是功利的,故而嘉澤的夜晚是在「城市的褶皺裡,孵化著夢」,但到白天,夢想還是「未乾的顏料」。不過「倦在城市的褶皺裡」,「倦」字宜改為「坐」字,雖然深夜令人疲倦,但夢想總是活躍的。此句有創意。
〈尋貓啟事〉甚至進入了貓的內在世界,這隻「追逐光」的貓,終於跳出「牆」和「欄杆」,逃出「魚罐頭」的誘惑與「毛線球」的幼稚遊戲,為自己畫出了一條逃逸線(德勒茲語)。有自由的流浪,才有真正的驕傲,故而「高高的豎起尾巴」。
嘉澤的詩多來自於生活的領悟,故靈光一閃,萬古不磨,常惹人深思。如〈無題〉一首:「把鮮花的種子/分給孩童和孤島」,對生活的熱愛和夢想,成為他的主題。這也就構成在〈博學者〉的反諷:「把沙漠關進沙漏/海洋鎖進魚缸/雪山裝進明信片」,博學者沒有真正的面對大自然。
在〈我〉的自畫像中,「我想成為詩」已成為嘉澤對新詩創作的雄心,讓一切捕捉下來的意義成為「永恆」。要「成為海」一樣,能「包容」一切,要「成為風」一樣,不斷重新撲塑生命新的形式,「想成為光」,照察「美醜善惡」,嘉澤對詩及人生而宏大的企圖。
我無法盡數羅列這冊詩集中的沈思與警句,嘉澤有詩才,也有能力創造佳句和佳作。他青春的戀情也在詩中留下創傷的烙印,這部分詩作冷靜而深刻,但在經驗的提煉上,似乎相對少一些對傑作的觀摩與學習。他七年來的詩作,已結成驚人之姿,猶如初戀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跡。告別初戀,等待的是生命的圓熱,那才將是「永恆詩篇」。
凝視深淵,或成為深淵 — 讀王嘉澤
洪春峰
忘卻一切。於存在的夜晚深層降下。在完全黑暗中,品嘗深淵的恐怖。
在孤獨的寒冷與人類萬劫不復的沉默中,體會戰慄與絕望。神,這個字。
為了抵達孤獨深處而使用神一詞,但我已經一無所知,連神的聲音也無法
聽見。就連神,我也完全不認識。
——喬治‧巴塔耶《內在經驗》
最早萌生於詩人心中的是什麼?那種半帶脅迫的驅動力,半賦予了詩人有話要說的使命感是什麼?我們可以追問每一個創作者,那最初與最終的事物的核心,是什麼驅動了詩人動用語言、調度意象、熬製情感、調音協律的意志之源是什麼?
是孤獨、是存在的質問、是對生命所感悟的點滴、還是對人情與自然的懷想…我想都是,而王嘉澤的作品中,浮現的是一種渴望溝通的孤獨感,以及某種生命本質欲追索情愛、掙脫綑綁、紀錄光影的初心。
孤獨就像是谷川俊太郎所說的,所謂的萬有引力,便是吸引人彼此靠近的引力。而我想補充的是,萬有引力的背後,也埋藏了不少因緣際會,有些引力的蛛網羅織與稠密,便是另外一些個體之間的互斥的引力。因為引力,不單純代表所有的「萬有」,而是各種萬有在接近與疏離之間,促使詩人按下快門,鑿下第一斧的那些時間空隙裡,寫詩者將那些空隙以語言填補,以視覺或聽覺的意象補綴,偷天換日掠奪而來的生命的印象之光,或光明後面的黑暗。
以他的〈下午〉為例,近乎俳句:
陽光在街道上躺著
把積水曬成白色的雲
被飛機穿過
物我之間的交換,視覺上的剪輯,與對於一瞬之光的拿捏,是小心翼翼而凝住時光的一闕短歌,這是為何嘉澤作品中,經常予人一種「鏡頭」般的感受。王嘉澤走訪過不同國度,在那些旅行的時刻中,他在熙攘與寂靜之間穿越現代國家的文化、文明與人群,思考回望自己的愛情與人生,就如同在他黑框眼鏡之下,那雙追問著世界關於愛情、自我、成長與生命本質的眼神。他的詩人之眼就是一具肉身的攝影機器,持續讓隱形的底片流淌,印上光影,正片負面,旁敲側擊或直取中軍,他彈奏著他自己的孤獨。形成詩句,化作攝影,在你的視網膜與心房內部,沖刷出生活的肌理與層次。
作者的無意識之流,往往有意無意洩漏了其詩背後的靈魂的形狀,以〈珍珠與鰭〉、〈物種主義〉、〈熬夜〉、〈讀我〉諸作之間,我們可以共鳴其孤獨,消瘦如傑克‧梅蒂的瘦長靈魂般的量感,孤獨的量感不在於巨大,在其犀利,而〈讀我〉一詩之中,「我把自己摺成一封信給妳 / 想著你會將我捧在手心 / 輕聲的讀我」
其中有渴望被慾望的對象,或慾望的主體所理解的念想,這是其一。
其次,在創作者王嘉澤的攝影作品與詩作之間,正巧構成了一有機的詩意系統,此詩意系統便以讓攝影之作與詩句的雙元架構,成就了無聲之詩與有聲之意象的對位。此種對位比起一般單純攝影,或單純寫作者的技術層面,王嘉澤打開了一個歧異且意義更不穩固的詩性空間,那詩性空間可能是豐饒的,也可能是虛無或廢墟的,廢墟不是大自然無可避免的循環……也不是神的旨意。廢墟是人類傲慢、貪婪和愚蠢的結果。但創作者是有情人。他不會容許廢墟無限綿延,或無限豐饒,無論是「刺點」或「打開詩意空間」,創作者的寂寞便是讀者的歡愉,創作者王嘉澤將自己書寫成詩,摺疊成信,化作時空中一張張相片,投向時間之河,泛起漣漪。
在〈淵與丘〉一作中,他說:
世界已有無盡的言語
短暫的沉默與光
永恆而寂寥
卻是我想說的
如一堵虛牆 如空的魚網
緘默
像心懷秘密的孩子
是的,世界已有無盡的語言,短暫的沉默與光,王嘉澤深明這一點,心懷祕密的孩子,究竟心懷什麼秘密?是揭開世界空虛的牆的簾幕,帶你看見更多豐饒或更精采的風景,還是邀請你看見無盡的語言所無能指涉的種種?詩人的責任在此,詩人的存在意義也在此,在深淵與丘之間,人人都是心懷秘密的孩子。這是詩人的初心,或許也是提醒讀者「去看」的一道季節之間的夜空中的火光。
像紀伯倫所言:「的確,你像是一隻秤,懸掛在你的快樂與憂傷之間。唯有當你心空無一物,你才能平衡靜止。」(Verily you are suspended like scales between your sorrow and your joy. Only when you’re empty you’re at standstill and balance.)在他的詩作〈無題〉中,「想著想著,一隻蝴蝶停在我的夢裡,睡著了」,在他的攝影作品裡,你可以看見群鳥驚飛,坦然的街景,走過的人群,那些睡在他光影作品中的人事物及街道、天空、建築,就如同蝶谷裡面的隱隱亮翅的蝶群,當你閱讀,你便啟動了令他們飛翔的密碼與指令,當你掩卷,你就穿越了詩人的夢境,走過了深淵的天空,或成為了天空所凝視的深淵。又如他〈失眠〉所寫:
在此即是彼的
日出與日落下的地球兩端
有人走進夢裡 也有人自夢裡走出
孑然一身的
把鑰匙留給下一位房客
他彷彿創造了一個愛的孤獨的時區,在鐘錶所無法指點之處;他也彷彿一個闖進世界的創作者,帶著某種意圖而來,帶著某種訊息前來,傳遞給你。王嘉澤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創作者,他還有許多往古典汲取養分的時間,他還有更多通往未來的通行證。讀王嘉澤,就如同凝視深淵,深淵也會回望你,而這道深淵將否更深?或是令你獲得更多無法言詮的美麗、靜謐與力量,端在於你是否與他共鳴。時光的逆旅中,此身皆是客,在此即是彼的日出與日落下的地球兩端,他的作品,是留給你的夢之房間的鑰匙。
洪春峰 寫於 澳門 2018/4/2
自序
我總這樣覺得,一首詩就如同自給自足的星球,如果微弱的引力可以吸引你靠近,那是美好的事,如果沒有,它也還在那裡。
前些日子聽朋友說,poem源自希臘語,意思是「我創造」。
我想,這也是一切偉大與孤獨的根源吧。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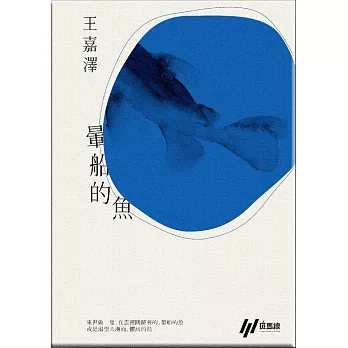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