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世界錯時我亦錯──馬奎斯小說中的好兇手、非處女,以及路過的主教
「主教走了。」
「我就知道。」她說。「真是狗娘養的兒子。」
《百年孤寂》譯到臺灣之時,我還是高中生,當年人手一本的盛況,我仍記憶猶新。馬奎斯做為偉大小說家的聲譽與地位長年不墜,篇幅相對短小的《預知死亡紀事》,提供讀者一個絕佳的機會,在一窺經典文學堂奧的同時,還能透徹了解,這個可以說是小說發展中的愛因斯坦,極具藝術教學性的基礎理論演繹。
小說的原點是什麼?對於小說家來說,小說經常源於一種「世界是錯的」的感受,但是從這個立場出發,怎麼處理這個「錯」呢?就讓我們跟著馬奎斯,走一趟這個好錯亂之旅吧。
好好兇手,好在哪裡?
《預知死亡紀事》的第一個特色,我會說,是馬奎斯刻劃了一對雙胞胎的好兇手。兇手怎麼可能是「好」的呢?可能──因為他們在謀殺之前,幾乎告訴每個人,他們打算殺人──方法有的、動機是明白的──真是省下了所有我們要煩惱的事項。歷來社會在謀殺一事耗費最大的成本,難道不是找出真兇,搜集證據以及設法定罪嗎?
這回,一切都省下了。「事實似乎是維卡里歐兄弟一點也不想趁四下無人,或那麼快殺掉山迪亞哥.拿紹爾,他們盡可能做了各種努力,希望有人阻止他們殺人,卻沒有成功。」如果我們探究得更深一點,兇手甚至等在拿紹爾平時不走的前門──馬奎斯在小說開始沒多久就細寫了這個被標為「奪命之門」的地理位置。它很重要,因為相對於常用的後門,這個前門面對廣場,有人群、有目光──非常能夠佐證,兇手確實是在最光天化日也最具公共場所性格的空間中,等待他們的獵物。呼應了主述者在重建記憶時,覺察到這對兇手能拖就拖的心理。「所有人都看見他走出來,也都明白他已經知道他們要殺他。」有些人大聲要拿紹爾繞路走,然而沒有人對兇手說什麼。這是意味深長的一幕:人們也許不希望他死,但對兇手想殺他這事──如果不說沒有意見,至少也有點隨便。
拿紹爾從他未婚妻的家裡走向自己家的前門,還未走到就遇襲。謀殺的事因起於夜間三點,然後他在七點喪命──在這四個小時中間,知情眾人的反應林林總總:從袖手旁觀到疲於奔命,有按下不表與私心竊喜──馬奎斯不只讓我們迅速進入當地生活與人際的組成方式,也揭開了人們複雜的心理史與性態度。
主教路過,路有什麼?
這個血腥的週一是個大日子,因為主教會坐船路過──這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元素,但若要了解小說廣闊的版圖,它卻是樞紐。如果借用米歇爾.傅柯等的觀察,從上帝到主教到家中父親,存在著某種一條鞭的關係,只要教化人們愛其中一個,都是加強對其他的臣服,也是鞏固父權的歷史手段。拿紹爾盛裝,為了可以親吻主教的戒指──無論村人的宗教信仰內容為何,他們的情感與行動是積極的,而且在信仰與對父權的尊崇上,後者絲毫不讓前者──即使出門是為迎接主教,拿紹爾也不放過侵犯廚娘女兒的例行公事。
與主教路過的澎湃慶典相對照的,是前一夜將軍兒子巴亞多.聖羅曼的婚宴兼誇富宴──讀者或許很難直接理解婚禮用錢砸人的影響,其中一個被錢砸到的西烏斯,會在兩年後去世。他很健康,「但是有人替他聽診時,感到他的內心深處冒出淚水。」馬奎斯一貫不批評,冷靜描述。但西烏斯的傷心是個例外,其他人多感到「有為者亦若是」──財富的權勢與主教的榮光,是村民生活的至高指導原則。某些女人對雙胞胎發出的謀殺預示較有警覺,比如賣牛奶的女人,她認為這兩人像小孩,「只有小孩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但她丈夫反駁,認為雙胞胎除了不會殺人,「更不會殺有錢人」。雙胞胎殺人後不是到警局,因為他們感到清白無罪,他們到了神父的家,神父還會分辨,他們只在天主面前無罪(!!!),未必在人類面前得以開脫,但雙胞胎認為到哪都無罪,而法律後來也同意他們:以「名譽」為名。神父的態度提醒了我們,宗教的命令與文化,可能比世俗法規更有勢力──在回顧歧視史時,也應占有一席之地。
在受到媒體片面報導的影響下,當今讀者很可能認為「名譽殺人」與伊斯蘭尤其相關,而這是一個因為失憶而產生的錯誤刻板印象。被殺的拿紹爾是遷徙到此地的阿拉伯人,死在天主教氛圍的「名譽殺人」之手,這一點對世人想像的誤區是個有力的反詰。於是我們來到一個主教無疑會感興趣的領域,那就是「非處女之身」。
非處女,如何能非?
就像在石器時代不會出現「手機」一詞,父權時代不會有「雙重標準的性道德」這種女性主義批判字眼:性對兩性的雙重標準,就是唯一標準。
處女不處女,事情大條。然而如果我們以為馬奎斯是以類似魯迅控訴禮教吃人的手法切入問題,我們就錯了。巴亞多.聖羅曼的未婚妻,雙胞胎的妹妹安荷拉.維卡里歐,她「非處女的方式」,就跟聖母瑪利亞的懷孕一般如奇蹟降臨。這段非常美的文學表述,我不在此贅言,留待讀者自行品味。必須非常謹慎地閱讀安荷拉.維卡里歐的段落,她並非現代意義下的自我權益主張者,我們甚至可以說,她是雙倍的父權原則擁護者,她不但接受處女新娘的概念,還為它添上誠實不自保原則──對於自身,她只想到死。
讀者必然會感興趣,這個除了感覺,什麼都不顧惜的女人,堅持說出拿紹爾的名字,使他成為謀殺的目標,背後的故事是什麼。應該只有極端沙文主義的讀者,才會認為,只要使得男人送命的女人就是賤女人──不過,安荷拉.維卡里歐確實使自己成為社會意義下的「超級大賤民」:如果女人只是一般性貨物般的賤民,透過新婚之夜認證她的「貨物缺損」狀態,她也使自己成為相當卑微的被放逐者,而她在這種更加清楚的「賤態」中,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激情,對象竟就是她之前不願接受的巴亞多.聖羅曼。如何解釋她在被公開羞辱之後,反而產生了追求他的動力?她不只是愛,而是成為一個極端的追求者,儘管愛慾饑渴到非人狀態的女人,可說是馬奎斯的簽名式之一,安荷拉.維卡里歐仍有其離奇的顛覆性。或許我們可以說,她愛的並非男人,而是經此「顏面掃盡」,不再像男人的男人。愛在權力罷黜後。
原來,愛完全不聽財富與貞潔的話啊!
世界錯時我亦錯
為什麼小說不明白指出在拿紹爾與安荷拉.維卡里歐之間的關係中,拿紹爾是個強暴者、情人或是被冤枉的人?
以習性來說,他是三者兼具。對廚娘的女兒來說,他與強暴者無異;對被他迷戀的妓女來說,他最可能是情人;對於只聽到他要辦盛大婚禮的人來說,認定他無辜才符合自身的經驗──但關鍵是,一個父權社會不能在乎這些差異,因為分辨這些差異就必須尋求女人的真實經驗與發言權,遲早會使女人的自由意志與權利言說浮出地表──拿紹爾是個不明不白的存在,因為女人們在父權社會裡,就是不明不白地活著──他與女人牽扯,就是與不明不白牽扯。且問,若不是拿紹爾被殺,有誰會問廚娘的女兒為何害怕拿紹爾?
就算拿紹爾不死,也會有別的人死,同樣也是眾目睽睽、眾所周知,並且不明不白的死。
這就是馬奎斯「世界錯時我亦錯」的小說藝術。
但是不能以為小說與眾人同步──既不落後也不超前,就表示小說家同意這個「錯」。
小說寫作就像,必須有所作為,才能變成非處女的非處女──我並不擔心我事先張揚了小說的幾個關鍵特色,會損傷讀者的閱讀樂趣──這個引領一個世紀風騷的敘述技巧與倫理立場,並不是把小說寫得光怪陸離而已,它有它百密不一疏的思索,絕對會讓你/妳從第一行,就欲罷不能地讀下去。
如同安荷拉.維卡里歐在賤活賤愛中找到出路,拒絕說出絕對真理的馬奎斯小說,也是低的與賤的──卑之,無甚高論。不再高瞻遠矚的小說或是推理小說,終於做到了更全面與激進的苦民所苦──這固然是小津的榻榻米高度美學,也是不可錯過的、匍匐在地,化做爛泥更護花的,馬奎斯世界。
作家/張亦絢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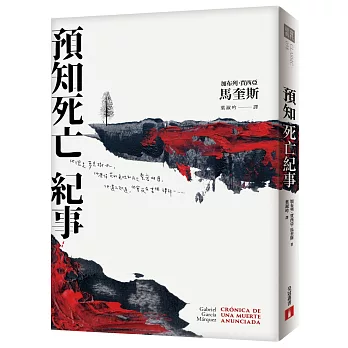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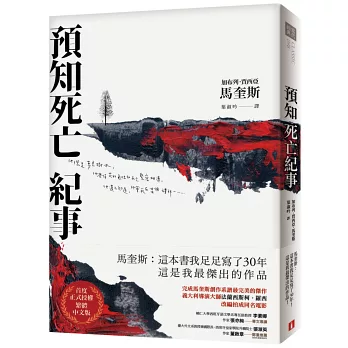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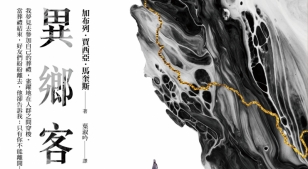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