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後真相時代中談劇場敘事
我可以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劇場,但無法想像這個世界沒有敘事。
敘事的出現,哪怕僅是一個表意的字詞,就是打開了一次理解的可能,猶如射入黑暗中的一道光。
在這個所謂「後真相」的時代,敘事的信效度相對低了。但既然揚棄敘事不可能,提高判斷敘事的能力成了唯一的出路。
在這個意義上,劇場敘事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遠比現實中的敘事更複雜。劇場中,一切的敘事都是謊言,也都是真相。在這個真相與謊言並沒有區別的地方,判斷的敏銳更不可或缺。
判斷牽連著目的。儘管坊間不乏談論戲劇敘事的著作,但絕大部分都停留在技術的層次,教人「如何說故事」、「如何說吸引人的故事」:布局、鋪陳、伏筆、高潮、角色化等等技術性的觀念,接連躍然於紙上。這些技術性的分析固然在寫出發人深省的故事時至為需要,但完全也可以用來弱化或癱瘓觀眾的判斷能力。
判斷需要視野。在這種技術性的分析背後,其實預設了一個所謂「好故事」的典範,而且定義非常狹隘。從學理上說,這種「好故事」不過是兩千五百年前亞里斯多德1《詩學》的變體與延續;從現實上說,它不過是服務了今日包含影視工業在內的戲劇主流。這樣技術取向的思維,其實很難含括劇場敘事的全貌,造成的排斥與遺珠更多。
學術研究在學理上的探討,應該是一個社會智力最後的防線。它的薄弱與窄化,結果就是實踐時的理盲、混亂、偏食、狹隘與排它,最後難逃向市場投降的命運。當對於劇場敘事的探討都窄化如斯,怎麼可能期待劇場的實踐多元又兼容?
於是,很自然地,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可以想像活在一個沒有劇場的世界。
在西方,過去一個多世紀來,劇場像是感到自己存在的危機,不斷地確定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不可或缺,追溯它儀式性的源頭,強調它的當下與在場,並放大自己與電影、電視的區別──極致的方向之一,就是劇場在努力創造一個沒有敘事的世界。在沒有深厚劇場史底蘊,也欠缺文化自信心(常表現為某種膨脹的自信)的臺灣,現代劇場的發展,摒除商業化的走向不談,也亦步亦趨地以一種辯證地姿態前進,呼應著西方劇場自我確定的浪潮:一拍浪頭追上一拍浪頭,有企圖心的劇場創作者不斷在劇場中找尋新的表現方式,重新界定表演與觀眾的關係,並提出理論論述為自己形式上的創新與主張背書,彷彿不如此就很難讓自己在眾家爭鳴中有鮮明的定位,也是在這個潮流裡,劇場更容易陷溺在概念中創作。小劇場運動曾被鍾明德形容是「美學與政治齊飛的年代」,現在,則是「形式與理論齊飛的年代」。
這本書因此顯得不合時宜,也不企求可以說服喜歡擁抱大勢所趨的人們,只是這麼多年,這股潮流也沒有說服我。無法說服,是因為這樣一種信念:我們總是先成為一個人,才有能力愛上劇場,才能進一步進行劇場美學上的探索,包括敘事或形式。這個從自己(與世界),到劇場(與世界),到劇作家、導演或任何美學的過程,應該環環相扣,但前兩個層次,卻經常在劇場美學與技術的討論中被淹沒。環繞劇場的人們像是殷殷期盼著深入瞭解這門藝術,卻沒有好好停下來關心自己。這本探討劇場敘事的書,是從七個命題出發,從不同的面向探索分析劇場敘事的可能。每個命題包含一些子題,共同集合成一個理解劇場敘事的面向。本書始於觀眾的行為(0.空的時刻),並界定觀眾的本體與對劇場的期望(1.觀眾/普通人);其次,它重新探索,或是恢復劇場的本質(2.可能性/觀點);為了避免陷入技巧取向對劇場敘事過分細瑣的分析(譬如切割成人物、空間、場景等元素),命題3以「結構」的概念以為替代;命題4嘗試探索「時間」在劇場敘事中扮演的角色;命題5則是提出「缺席」的概念,試圖分析現代戲劇的敘事策略──這是主流觀點完全忽略的;命題6以「表演」為核心,揭示不同歷史與存在條件如何影響文本與表演的關係,以求恢復古典戲劇被主流觀點掩蔽失色的部分;最後的命題,「土地」,則是受惠於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2的啟發,想指出根性在敘述中的重要性,並指向劇場敘事有待發掘的可能。
不論在這本書,還是在教學中,我都很努力擺脫掉一些流行但根本禁不起進一步思索的概念,譬如寫實(反寫實)主義、象徵主義、荒謬劇場等等──它們帶來的方便與對腦子的傷害幾乎一樣多。如果我們對戲劇的思索不能抗拒使用這些便宜行事的概念,甚至連一份警覺都沒有,那在劇場中發生的事也很難讓人期待。這本書之所以會寫出來,其實就是源自這份抗拒與不滿。感謝本書的編輯謝依均小姐,很願意聆聽我的想法,給我很大的空間,在她企劃的一系列劇場與戲劇教科書中,讓本書能以這樣的面貌出現。我們同意這不會是一本篇幅很長很厚的書,但希望這是一本讓人可以讀不止一遍的書。書末所列的劇本寫作習題,很多是我的美國老師Howard Blanning在教學上的設計,希望能透過實務操作,帶來一些劇本分析的眼光。雖然看起來不像,但我的確希望本書可以是一本教科書,如此,或許我(們)又能想像這個世界上不僅敘事不可或缺,劇場也是。
何一梵 謹誌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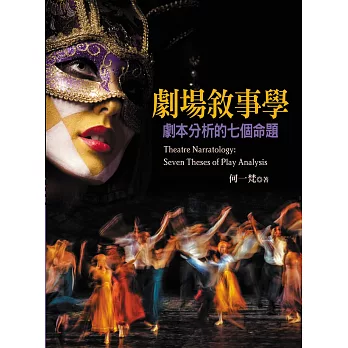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