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獨舞」到「眾愛」──閱讀李琴峰小說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同志文學史》作者/紀大偉
台灣年輕作家李琴峰在日本得獎的小說《獨舞》一鳴驚人,已經榮獲多位日本文學專家盛讚。這部用日文寫成的小說一方面回顧1990年代英年早逝的作家邱妙津,另一方面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同志人權運動,儼然成為勇於承先啟後的當代同志文學代表作。我必須強調,想要認識「台灣同志『跨世代』連帶」(從1990年代到現在)以及「台灣日本『跨國』連帶」的國內外讀者,都不能錯過《獨舞》。
我在這篇文章的工作,並不是要重複指認《獨舞》在「同志文學領域」的成就,而是要承認《獨舞》在「身心障礙文學領域」的貢獻。小說主人翁趙紀惠在小說開頭,就跟讀者偷偷承認:她向日本人自我介紹的時候故意強顏歡笑,但是她心裡卻想著,「一段簡短的自我介紹引得大家笑聲不斷。當然,沒講的事多著,包括身為女同志,包括『災難』,包括憂鬱症,包括自己其實是以近乎逃亡的心情來到日本的」。也就是說,在《獨舞》載沉載浮的「衣櫃」(秘密)有好幾個:「女同志身分」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憂鬱症」也是一個讓人難以走出來的衣櫃。(至於「對災難憧憬」這個衣櫃,是指紀惠對於各種死亡的詭異期待。這個衣櫃跟憂鬱症其實是無法切割的。)不過,除了承認《獨舞》可以歸入身心障礙文學「領域」之餘,我也要描繪「從『獨舞』到『眾愛』」的軌跡。「獨舞」一詞固然來自書名,也來自於書中描述趙紀惠從小孤獨生活的生活樣態;「眾愛」一詞看起來像是日本漢字(例如,像「若眾」),但其實是我自己隨手捏造的「獨 / 舞」對照詞:「眾」是「獨」的相反, 「愛」則算是「舞」一種對照。如果「獨舞」類似「顧影自憐」、「自怨自艾」(我在這裡沒有價值評斷的意圖),那麼《獨舞》敘事中,人與人磨合,或可稱為「走出獨舞」狀態的「眾愛」吧。……(節錄,全文請見本書)
再生之書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楊佳嫻
由在日台灣人李琴峰(1989-)以日文寫成的《獨舞》,主角趙迎梅/趙紀惠的情感資源──文學──複雜地鑲嵌在台灣當代文學、日本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交互參照的網絡裡。它是日本文學的一部分,也不妨視為台灣文學的外延。
就台灣歷史的角度看,小說提及大事件如九二一大地震、太陽花運動,小範圍事件如台大百日維新,鮮明地標誌出新一代女同志成長的波折與記憶據點。就女同志書寫的意義來看,《獨舞》再三向邱妙津致意,讀者們當可在小說裡感受到一種氛圍,由台大校園、文學課室與社團活動共同催生,似曾相識讓人想起《鱷魚手記》;然而,李琴峰卻有意展現青春大觀園的負片,所謂「對同性戀最友善的大學」,其實充滿了人際的黑水,主角受過傷的身體與心,封閉成為一隻恐怖箱,也許自己都不知道伸手到裡頭去會摸到什麼。就文化交匯的意義來看,《鱷魚手記》中屢次叨念著太宰治、三島由紀夫,日本近代文學中關於羞恥、美、死亡和文學的思考,也已內涵為邱妙津作品的血肉,而李琴峰則把這樣的邱妙津再吸收吐哺,使之能在日本文學中現身,也再次證明邱對不同世代台灣女同志自我認同塑成的長久影響。
然而,這部小說並非邱妙津顯靈版或轉世版,而是與邱妙津相距數個世代的年輕作者,展現了屬於台灣女同志文學文化活生生的遺產,也預備要說一個關於自己的故事──來自資訊求取迅速、交友管道相對便利、出走到異國相對自由、文化認同內容相對豐富的世代與社會中行走的女同志。可是,環境條件雖然轉好了,並不意味著做為女同志的孤獨感就能完全驅散。……(節錄,全文請見本書)
後記
《獨舞》繁體中文版後記──濃密黑暗裡的一縷微光
作為一個在台灣出生且居住了二十幾年的台灣人,將自己的小說翻成繁體中文,還要寫個「繁體中文版」後記,說起來實在是件奇妙的事。
二〇一三年,我結束在台灣的大學學業,正式作為一個碩士班留學生移居東京,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又過半年,二〇一六年,我進入一家日商就業,親身體驗日本上班族的通勤生活。某個忍受著擠沙丁魚般客滿電車的早晨,窗外仲春景色旖旎,陽光燦爛灑落在鐵路兩旁花草樹木之上,望著眼前的一切迅速往後飛快流逝,突然間,「死ぬ」這個日文單詞從天而降,擊中了我。
「死ぬ」讀作「shinu」,望漢字生義也知道是「死亡」之意,初級日語便該學會的動詞。然而那天早晨,我反覆玩味「死ぬ」一詞,發覺這個詞語帶著某種特殊的興味。在現代日語的動詞裡,以「ぬ」結尾的,唯有「死ぬ」一詞;同時,「ぬ」這個音節在日語裡,總帶著某種濕黏滑溜的感覺,與水澤湖沼有關,又有點陰暗的印象。擬態詞「黏滑地」為「ぬるっと」,「黏液」為「ぬめり」,「沼澤」為「ぬま」。或許死亡便是這樣一種意象,像一潭深不見底的湖沼,又像某種潮濕黏滑的液體如影隨形地膠著人類。「死」與「ぬ」這種必然性的結合,在語言學上當然純屬偶然,但這種饒富趣味的偶然卻深深吸引著我。在那瞬間,一些關於死亡的字句不斷自體內湧出,我本能地用智慧型手機將這些字句記錄下來,於是《獨舞》的第一段便這樣誕生了。
在我出道之後,屢屢被問及為何母語不是日語,卻要以日文寫作?對我而言,《獨舞》以日文寫成,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那天早晨的通勤列車上,「死ぬ」一詞恰好以日語的形式打到了我,於是《獨舞》便成了一篇日文小說;然而中文的「死亡」一詞確實不像日語「死ぬ」般,有著上述語言上的趣味,因此那天若打中我的是中文的「死亡」一詞,或許《獨舞》這篇小說便不會誕生。
《獨舞》寫成之後,我將它投至日本傳統代表性純文學新人獎之一的群像新人文學獎,幸運地獲選二〇一七年(第六十屆)優秀作品(相當於佳作,大獎從缺),由此得以外籍日本文學作家的身分進入日本文壇。會投稿群像新人文學獎也不是因為景仰村上龍或村上春樹(這兩位作家都是以群像新人文學獎出道),單純就是截稿日期與限制字數的巧合罷了。二〇一八年春,《獨舞》單行本在日本上市,由舉辦「群像新人文學獎」的講談社出版;二〇一九年,經作者本人翻譯而成的繁體中文版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因而得以送到您手中。
《獨舞》創作源起與出版時程大致如斯,而一讀之下,便不難發現其內容相當「台灣」,且相當「同志文學」。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我本身亦為同志族群,且確實承繼著台灣九〇年代風起雲湧的同志文學養分,有著不得不如此書寫的理由。另外由於首次嘗試以日文創作小說,半生不熟,只得就近從自身與周遭經驗取材,遂成了您所看到的如此樣貌。
進入新世紀之後,台灣的同志文學當然有所突破,不同於八〇、九〇那個晦暗而籠罩著死之陰影的年代,新世紀的同志文學應當呈現著一種更加豐富而多元的面貌(說「應當」,是因為其實我並沒讀過多少本,慚愧),相較之下,《獨舞》仍充斥著苦痛、不安、自殺與死亡陰影,或許略嫌保守。然而不可諱言,雖然我本身經驗與趙紀惠略有不同,但類似的苦痛、不安與自殺念想,曾籠罩了我的整個青春期乃至大學時期,至今仍偶爾在午夜夢迴折磨著我。主體的傷痛不是一句「時代已經進步」就能解決,無關乎文學史或同時代文學的潮流如何,《獨舞》之於我而言是,有傷痕,所以必須書寫,如此而已。小說裡趙紀惠一面體認到「說不定自己已經算是幸運的了……畢竟自己避開了折磨邱妙津的九〇年代,得以在新世紀安度青春歲月」,卻又一邊受著痛,便是此種心緒之反映。
創作《獨舞》時,有三位女性作家影響我鉅甚,作品裡也屢有提及,我想在此介紹。第一位不用多說,自然是邱妙津。對日本讀者(不論是否為同志族群)而言邱妙津仍頗為陌生,但對台灣讀者而言,想是再熟悉不過。創作《獨舞》那段時期,我是一邊讀著《鱷魚手記》的,因此在敘事文體上多少受了些影響。
第二位是賴香吟,特別是《其後》這部作品。閱讀《其後》是在創作《獨舞》的半年以前。《其後》不僅提供了一個不同視角,讓我得以重新回顧邱妙津死亡的悲劇,以及這悲劇對邱、賴兩人的意義與影響;同時它也提供了我一個契機,讓我深刻思考關於「治癒」這回事。可以說,若沒有閱讀《其後》,恐怕便不會有《獨舞》的誕生。
第三位是台灣讀者較不熟悉的,日本女同志作家中山可穗。中山可穗生於一九六〇年,於一九九三年以處女作《駝背的王子》出道,從此致力書寫女同志戀愛故事,至今已出版近二十本作品,在日本女同志圈頗享盛名。不同於邱妙津與賴香吟,中山可穗的作品更有著一種大眾娛樂小說的取向,然而其華美文體,以及作品裡展現的那種對於戀愛的義無反顧,以及來自彼處的苦痛、不安、徬徨與悲哀,卻深深打動著我。其代表作《直到白薔薇的深淵》也多少影響了《獨舞》的創作。可惜中山可穗的作品裡至今唯一被翻成繁體中文介紹至台灣的,僅有二〇一五年的《愛之國》一書(聯合文學出版社),台灣讀者不太有機會感受其作品的魅力。我由衷希望有天能以自己的譯筆將中山可穗的作品介紹給台灣讀者認識,如此想必便是一大幸福。
除上述三位女性作家外,在日本文壇有所謂「越境文學」的作家如楊逸、温又柔、橫山悠太,有他們在前面開路,才讓我能更加盡情地悠遊於漢字與假名之間。而本書得以在台灣出版,也該感謝「內容力」公司創辦人黃耀進先生的引介,以及聯合文學出版社周昭翡總編輯和蕭仁豪主編的賞識與協助,在此致謝。
正如書名《獨舞》所示,「黑暗中的獨舞」為此部作品的重要意象,同時這也是一個自青春期開始便糾纏我多年的意象。它意味著無邊無際的孤獨,舞蹈是為了求生,但生存只會帶來更深的寂寞,為了消解寂寞又必須舞動,於是只得陷入無窮無盡、無可救藥的輪迴。舞者只能期盼在濃密的黑暗之中閃現哪怕是那麼一縷微光,藉以打破輪迴,刺穿黑暗,終息獨舞。
然而那一縷微光具體究竟意味著什麼,卻因人而異,期盼的過程也宛如凌遲。之於趙紀惠,之於我,是否已經覓得那一縷微光,至今我仍不敢斷言;但若有讀者有著類似的、無邊無際的孤獨,且同樣渴盼著那一縷救贖的微光,那麼我衷心希望這部小說,能成為尋覓那縷微光的,一個至細至微的小小線索,如此作為作者,便是萬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於日本神奈川縣新子安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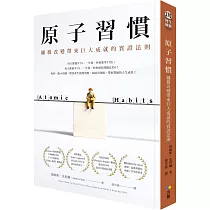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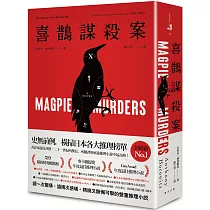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