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沒有主場優勢的信仰
本書《不寬容的信仰?》至少牽涉到三件重要觀念的演變:1. 道德相對主義、2. 世俗化、3. 文化戰爭。在二十世紀,特別是下半葉,這三件事同時在美國及西歐的文化中快速漫延開來,對原本是以基督教信仰為文化基礎的社會,造成極大的影響。作者從「寬容」的角度來剖析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本書可以幫助讀者明白,為什麼過去許多人心目中的美國,原本是以基督教信仰為文化底蘊的社會,到了二十一世紀,基督教的信仰漸漸被人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個人信念,並且在公眾領域中節節敗退。
首先作者區分了「舊寬容觀」和「新寬容觀」。舊寬容觀是指,我相信並堅持自己所持有的是真理,但是當別人信相和堅持的觀點與我不同時,我會尊重別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我不會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去阻撓他的公開發言。這是一種道德客觀主義,因為持舊寬容觀的人認為事情有善惡、對錯之分。新寬容觀所主張的是每個人都應該接納不同觀點,特別是在宗教或政治事務中,公平對待持不同觀點的人。它背後所採的態度是道德相對主義,因為新寬容主義認為事情的是非對錯都是相對的,或者我們無從知道對錯。如果有人堅持他的觀點才對,這人就是武斷、獨裁、偏頗。可是耐人尋味的是,當新寬容主義漸漸取得愈來愈多人的擁戴之後,很快就會成為不寬容者。新寬容主義駁斥具有排他性的真理宣告,並且設法以強制性、不寬容的方法對待持排他性真理宣稱的人。
作者在書中不厭其煩地舉了許多實例。福音派的基督教會及信徒,每當作出真理宣稱時,總是會惹來一身腥,甚至受到排擠。公開場合的禱告、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幾乎成為社會上的禁忌。基督教信仰在美國社會漸漸地不受到寬容,也和世俗化有很大的關係。世俗化是指:與宗教或神聖秩序為主導的年代相比,宗教、上帝、神聖的思想、價值觀和教會體制,在人類群體中,逐漸喪失影響力的過程。在過去,特別是宗教改革之前,大公教會對歐洲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宗教改革之後,個人享有愈來愈多的宗教自由,隨著各宗派的發展和互相競爭,少有任何一個宗派能全面性地掌握社會的資源和主導公共政策。世俗化不必然意味著相信宗教的人減少了,但是宗教被排擠到公共生活的邊緣。宗教只被允許在私人的領域中被提起。基於宗教信念所推動的公共政策或法律,常常受到疑懷和排斥。同時,世俗主義崛起,特別是無神的、自由人文主義者假設自己擁有「客觀的」、「中立的」思想,躍上公共對話的舞台,儼然成為唯一具有思想及道德正當性的發言人。
其實這個過程,有人形容是一場文化戰爭。它是傳統對激進、道德右派對道德左派的戰爭,同時也可能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對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戰爭。美國的保守福音派常是傳統價值擁護者。他們堅持胎兒生命的神聖尊嚴,反對婦女擁有墮胎自主權,他們堅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反對同性婚姻,他們捍衛在公私立學校裡教聖經及公開禱告的權利。幾十年下來,激進派取得了優勢。基督教信仰和教會的影響力大不如前。表面上看來,好似是以「新寬容主義」取代了「舊寬容主義」,但是骨子裡,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文化戰爭。當激進的、世俗的、自由至上主義的思潮在社會上取得勝利時,理所當然地會趁勝追擊,把保守派勢力一盡剷除。道理很簡單,新寬容主義雖然堅稱自己是具有多元代表性的,但其實,他們是具有同樣偏見的一群人,其思想也不具有多樣性。在這種群體中,幾乎是無法容忍保守派、傳統派的存在。
西歐及北美以外的基督徒,大概會好奇,在這場文化戰爭中,為什麼原本擁有優勢的教會,到底做了什麼,以致於無法保有原來的影響力。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以下幾項可能是關鍵的因素。傾向於自由派的主流教會,例如美國聖公會、長老會、信義會,因為樂於與這世界上所有的學問及文化潮流為伍,所以教會在核心的教義上,有許多退讓,在關於信仰的生活實踐上,也愈漸寬鬆,無法與世俗潮流相抗衡。至於保守的福音派,卻是因為另外一個原因,而喪失了影響力。福音派致力於傳福音、拯救靈魂、建立教會,本沒有錯。但是疏於在學術思想上不斷培育最頂尖的人才,使教會具有能力進行公共對話。福音派教會因為在智性上無法與世俗的學者和文化的潮流爭辯,以致於當美國社會全面性地受到世俗主義侵襲時,教會無力反抗。
本書的作者在最後一章提出了十個方法給教會和基督徒來面對「新寬容主義」所帶來的挑戰。其中,第一到第六項,都是有關於知識論、哲學思考上的澄清。這些思想上的澄清也是福音派教會最需要的。而第七到第十項的建議,仍回歸到基督徒作為基督門徒的基本概念,包括實踐寬容、傳福音、預備好受苦、以神為樂。
有一件事是本書作者沒有在書中強調的,美國的基督徒應當要有覺醒,美國不再是一個以基督教信仰為共識的社會。換言之,美國教會和基督徒都不應該假設自己的信仰立場是理所當然的、為社會上所共同接受的。基督教在美國不再享有主場優勢。在美國的基督教右翼團體,若是仍然以其自身對於聖經的解釋及生活運用,希望用法律來實現或保留原有的道德規範,必然會受到愈來愈大的反彈。
本書繁體字譯本的問世,具有獨特的意義。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台灣的公民投票中,其中有三案是由教會團體所提出來有關婚姻與家庭價值的公投案。其中,第十案主張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投票結果,這一案得到了765 萬票,占總投票數1102 萬票的將近七成。另外兩案也分別得到了過半的支持比例。這一投票結果顯示出,在婚姻與家庭觀念中,基督教所主張的,和台灣社會中的多數人是較為一致的立場。華人世界中,基督教思想和文化從來都算不上是主流。但是,至少在婚姻與家庭的道德觀上,基督教卻以公投的機制,引導台灣人民清楚地表達出多數人的道德立場。
但是,這樣的道德立場是不斷地受到挑戰的。發生在美國的文化戰爭,也已經在台灣發生。當道德相對主義、自由至上主義、世俗主義的擁護者,以各式各樣的方法、運動,擴張他們的勢力時,基督徒、教會、神學院皆應該儆醒地挺身而出,成為信仰價值的中流砥柱。同時,我們也應該培養更多委身的基督門徒。其委身的程度,不但使這群門徒在智性上成為各專業的頂尖人才,同時又有具深刻神學的涵養。在數量上也要充足,多到能夠延續這一代基督徒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如此,教會方有可能在世界上作光作鹽,作上帝真理的好管家。
陳尚仁(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院長)
譯者序
卡森是一位新約教授和神學家,也是一位敏銳的社會觀察家、歷史學家和思想家。他寫作本書是為了回應這時代的普遍病症,即建立在相對主義體系上的寬容觀。這個主題和內容不但適合對宗教現象有興趣的人,也適合對思想史、社會學、神學、宗教與法律和政教關係感興趣的讀者。
卡森在本書明確區分了兩種對「寬容」的不同理解:雖然人們都用「寬容」這個詞來表述,但一種寬容(編註:書中稱作「舊寬容觀」)是建立在相信存在絕對真理的基礎之上,另一種寬容(編註:書中稱作「新寬容觀」)是建立在相對主義基礎之上。他指出,現代人把這兩種寬容混為一談,或者在討論時頻繁偷換概念;這種缺乏反思,使新寬容觀的危害越來越明顯。
建立在相對主義之上的新寬容觀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的觀念,這不僅是美國社會價值觀日漸分化的體現,也是其他現代社會的普遍困境。這也是研究世俗化的學者普遍談到的。所謂世俗化是指:與宗教或神聖秩序為主導的年代相比,宗教、上帝、神聖的思想、價值觀、制度在人類群體中逐漸喪失影響力的過程。社會學家彼得‧ 柏格(Peter L. Berger)認為,社會的現代性具備一些制度特徵,包括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科學和技術成就,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大眾傳媒,現代高等教育等。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也指出,「對上帝信仰的衰退,尤其是宗教實踐的衰落,已經觸及整個西方社會公共和私人生活的中心,已然成為一種亞文化,成為一些人私下涉入其中的眾多形式之一。」但大多數學者也認為,這並不意味著宗教的消亡,只是宗教信仰不再活躍於公共領域。既然公共領域不能只為一種宗教信仰提供傳播平臺,不能只為一位上帝提供舞臺,人們就需要在公共領域中寬容這種多元化,而只把道德判斷留在私下進行。這種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是很重要的。
卡森指出上述這種寬容觀的演變,是始於一種前提預設上的轉變。也就是說,關於寬容和不寬容的問題,是「在人對上帝的認識之內展開」(頁88)。這還是延續了彼得‧柏格的論點,他認為世俗化和文化多元主義的發展,使得曾經為整個社會秩序提供「拱形」解釋的體系,也就是宗教信仰提供的「神聖的帷幕」,也隨之變成許多解釋體系中的一種。此時現代人都很善於提出個人的解釋,也普遍不再堅持有絕對真理,因為這種曾經在人類社會中佔主導的「絕對性」宣稱,如果在現代社會死灰復燃,似乎不符合人們普遍持有的「進步觀」。但是,持進步觀的現代人應該思想一下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的話:「我們這個進步的時代是一個對何謂進步最沒有把握的時代。」
卡森認為,對寬容和不寬容的思考,要回到一個更大的思想體系中展開。但首先要思考的一個歷史問題是,究竟人類社會之秩序是否有其規律可尋?究竟現代人是已經遠離了文明, 還是正在走向文明呢? 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 l e Durkheim)、馬克斯‧ 韋伯(Maximilian Emil Weber)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曾指出,現代化是一個逐漸祛魅、理性化和分化的過程。這種分化,不僅僅包括日漸複雜的勞動分工,也包括公共與私人、宗教與政治、事實與價值、手段與目的的分離。這似乎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連由清教徒締造的美國也難以逃脫。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論述過,美國的民主制度是生發自美國人的「心靈秩序」,根植於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很多物質上的祝福,也塑造了美國人極具創造力的品格。但同時也暗藏危機:美國人在實踐領域(不論是經濟、政治或文化)取得的成功,會使他們更傾向於依賴技術理性和追求物質舒適,這樣的話,他們就會越來越厭惡超然的事物。
全球化、城市化過程會強化相對主義的寬容觀。因為,人口的流動和複雜的城市環境會增強人群之間的「匿名化」,使族群之間相互貼上「非位格化」的「標籤」。柴斯特頓曾在《異教徒》(Heretics)的開篇寫了一個場景,來說明現代人如何竭力與「正統」的標籤保持距離:
從前,異教徒以自己不是異教徒而自豪。⋯⋯可是如今,幾個現代的術語就已經使他為自己是異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說:「我想我的思想非常異端。」然後環顧四周,尋求掌聲。「異端」這個詞現在非但不再意味著錯誤,實際上還意味著頭腦清醒、勇氣十足。「正統」這個詞現在非但不再意味著正確,實際上還意味著錯誤。所以這些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人們現在不太在意自己的人生哲學是否正確了。⋯⋯有一件事不知會比因一個人的哲學觀而將他燒死要荒謬、不切實際多少倍,那就是:習慣於說一個人的哲學觀無關緊要。
他隨後說,這種觀念上的改變在二十世紀、大革命尾聲時非常普遍,以至於原來佔主導地位的「普遍理論」處處遭到輕視:「有關人權的教義,與有關人類墮落的教義一起被摒棄了;無神論本身如今對我們來說太具有神學性了;革命本身太制度化了;自由本身太約束了,我們將不作任何概括歸納。」他生動地刻畫了現代人這種默然的道德觀:
現代人說:「讓你那些古老的道德準則見鬼去吧!我追求的是進步。」按照邏輯陳述出來,這句話的意思是:「讓我們不要確定何為善,讓我們確定我們現在是否在獲得更多的善吧。」現代人說:「朋友,人類的希望既不在宗教也不在道德,而在教育。」清楚地表達出來,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不能確定何為善,但讓我們給與孩子們善吧。」
相對主義在討論何為善上是無能的,因為它認為,所有世界觀都同樣有價值,所有立場都同樣成立,所有觀點都沒有對錯、善惡之分。如果你對這種姿態皺一下眉頭,它會縱身躍上最高道德的審判席,宣佈你是不寬容的。更讓人不解的是,很多人會在這一罪名面前低頭認罪,覺得寬容的確是一種需要持守的美德、和平氣質,可以免去很多爭論和煙硝戰火。但很多人沒有思考的是,這時候「寬容」的概念已經被偷換了。卡森引用哈奇(Nathan Hatch)的話,「這一隻寬容的小羊,常常會變回一頭相對主義之狼」(頁43)。
「寬容」的歷史,是一部社會秩序史。卡森在本書也討論了宗教自由和寬容的定義和演變,用他思想家的眼光透視了美國社會近些年來的很多公共事件(如基督教機構受到排斥、有信仰的醫學專業人士拒絕施行墮胎和協助自殺、跨信仰對話、種族歧視、校園宣教等)及其影響,深度分析了這種相對主義寬容觀的蔓延,和其問題根源。
馬麗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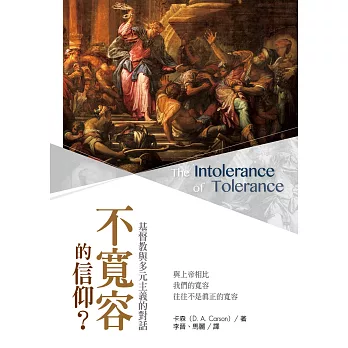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