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1993》三版依舊是五十一首,不過將初版的十五首詩替換成新的,並且重新編排詩的順序。編輯詩集總是有趣折磨的,改版重製過程中最讓我著迷的是,曾經你以為遺忘是不可能的,如今幾乎都快想不起來了。作為一個勉強通過的人,編輯這本書時不斷瞥見往昔幽靈,實際上像是進行了一場時空旅行,對過去的自己揮手致意,和被過去的自己打巴掌,或打他巴掌之類的。詩集中的每一首詩都擁有自己的意義,這麼多的意義排排站如同遊行隊伍般成就了詩集的一個集體意義,每首詩意義互相滲透,重複有其目的。
在二零一五年出版的《1993》作為第一本我以潘柏霖這個名字印製的書籍,違背我從十二歲開始那荒謬的成為小說家的夢想,我竟然是經由寫詩這件事情被記住的。很小的時候因為一些幾乎可以摧毀我身為人類未來的爆炸,而意識到一輩子根本不夠,導致我多麼想要寫一本永遠不停止的小說,人物像是開著車在公路上不停移動,齒輪持續轉動,我手中的花永遠不會爛掉。
一直到二十三歲時才發現齒輪不小心鬆動,車子早就越軌了,迎面而來是一台大卡車將我攔腰撞成一半,更別提那脆弱的花了。攔腰撞成一半,比較大塊的那部分被以「詩人」的稱呼框住保護,有段時間我並不知道如何應對這個現實,當被介紹時總以詩人稱呼,但我明明寫小說寫了超過十年。這時候多麼清楚「成為自己」只是口號,口號是用來煽動人心的,讓人以為自己真的能夠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東西。事實上是,就像性向是不能被外界設備干擾改變的,自己是誰也不是想要就能做到,我們是無法靠許願改變現實的。
大學開始寫詩後小說創作減少了,甚至是停滯不前的狀態,事實上當初之所以開始寫詩的部分原因也是無論如何書寫,我總是認為我的小說缺少了某種東西。在啟明出版我第二本詩集《我討厭我自己》之後,我意外開始重新進行小說創作,某些遺失的東西找回來了,以為自己將再也無法書寫小說的恐懼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開始明確感受到兩個不同文體對我的不同意義,明白成為自己是一條非常漫長艱苦,但也許值得的旅行。
我的第三本詩集,我習慣稱呼它為《1993》增訂版,作為反思《1993》,以及被這本詩集影響的我自己。《1993》初版是對我所熱愛的現代詩進行的一次小小回聲,在完成的當下幸福感充滿,隨之而來的其他怪物卻是讓自己精疲力竭不可思議。這很像是當初為了拯救自己而領養一隻狗,狗替你度過難關之後,在你的生活中製造出新的難關,總是干擾你的睡眠,霸佔你的床,早上五點舔你的臉要你餵牠吃飯,你還得每天帶牠出門閒晃。拯救自己的藥物常常都是有損的,抗抑鬱抗焦慮抗快樂抗悲傷抗失眠,一切的抵抗都得付出代價,至此終於明白,於是《1993》增訂版誕生。
《1993》增訂版,或者稱之為二版,是很快樂的一本詩集,它是被閱讀後的詩集,也是閱讀過程中的詩集。形式以兩個讀者共同建構一款《1993》閱讀規則並且進行閱讀詮釋為主。你不覺得書中兩個讀者不斷互相抗爭,試著在不同閱讀視野中將對方往自己這邊拉近一點,最後的不協調融合看起來像是幸福快樂的愛情喜劇故事嗎?出版增訂版後,偶然在二手書店翻閱到這本書,裡頭有著其他讀者寫下的閱讀筆記,那一年的我是何其幸運。
後來就是世界末日。《恐懼先生》作為度過末日的倖存者日記,試著告訴自己(其次才是別人),一切都會沒事的,你可以通過的,基本上是一種精神療法,更接近一種夢幻少年的參選宣言。製作這本詩集時出現一個構想,極端願意成為他者(儘管深知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人工擁抱》委託創作計畫誕生,至此寫詩的方式開始轉變,出現不同的聲音。
在這轉變過程中,過去的自己仍發出許多聲音,那些聲音最終都成為《1993》三版中所新收入之詩。作為一個介於過去與未來的中間產物,《1993》三版不僅是對前兩個版本《1993》的回聲,更是一個現時此刻的產物。是我的現在,不是未來將會出版的《人工擁抱》,但也不完全是過去已經出版的任何作品,像是一隻還沒有成為成熟水母的成熟水螅體,儘管已經不再是剛誕生的幼蟲,但也還沒有真正成為最終型態。如果用神奇寶貝來比喻,就是迷你龍進化成哈克龍,但還沒有進化成快龍。而我仍然不確定成為快龍是必要的,我只想不斷移動,暫時不想抵達終點。
創作上有個信念,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應該寫的東西,你必須寫你的當下,而那個當下會變,但你的現時此刻是還沒變的。你必須把那個還沒變的敘述出來,如果你不寫出來,等到你變了,就無法再回頭去寫當時的事情了。一切的回顧都不是現在,現時此刻,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猜測我們必須在闡述此刻自己的同時,盡可能成為當下最好的自己——當然那是永遠都不夠好的,我們只可能成為當下最好的自己。
這些是我希望我能夠記住的事情。
2019/03/18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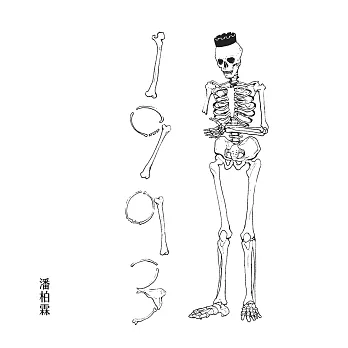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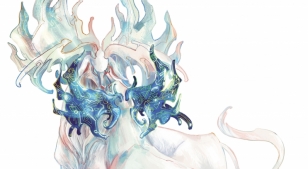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