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孔子生平言行,具載於其門人弟子之所記,復經其再傳三傳門人弟子之結集而成之《論語》一書中。其有關於政治活動上之大節,則備詳於《春秋左氏傳》。其他有關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後,又散見於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穀梁傳》、《小戴禮記》〈檀弓〉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語》等書者,當尚有三十種之多。最後,西漢司馬遷《史記》采集以前各書材料成〈孔子世家〉,是為記載孔子生平首尾條貫之第一篇傳記。
然司馬遷之〈孔子世家〉,一則選擇材料不謹嚴,真偽雜糅。一則編排材料多重複,次序顛倒。後人不斷加以考訂,又不斷有人續為孔子作新傳,或則失之貪多無厭,或則失之審覈不精,終不能於〈孔子世家〉以外別成一愜當人心之新傳。
本書綜合司馬遷以下各家考訂所得,重為孔子作傳。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為人,即其所自述所謂「學不厭、教不倦」者,而尋求孔子畢生為學之日進無疆,與其教育事業之博大深微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業次之。因孔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之主要貢獻,厥在其自為學與其教育事業之兩項。後代尊孔子為至聖先師,其意義即在此。故本書所采材料亦以《論語》為主。凡屬孔子之學術思想,悉從其所以自為學與其教育事業之所至為主要中心。孔子畢生志業,可以由此推見。而孔子之政治事業,則為其以學以教之當境實踐之一部分。雖事隔兩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業已不足全為現代人所承襲,然在其政治事業之背後,實有其以學以教之當境實踐之一番精神,為孔子學術思想以學以教有體有用之一種具體表現。欲求孔子學術思想之篤實深厚處,此一部分亦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學與教人與其政治事業外,尚有著述事業一項,實當為孔子生平事業表現中較更居次之第三項。在此一項中,其明白可徵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謂訂《禮》、《樂》,事過境遷,已難詳說,並已逐漸失卻其重要性。至於刪《詩》、《書》,事並無據。贊《周易》則更不足信。
以上關於孔子之學與教,與其政治事業、著述事業三項層次遞演之重要性,及其關於著述方面之真偽問題,皆據《論語》一書之記載而為之判定。漢儒尊孔,則不免將此三項事業之重要性首尾倒置。漢儒以《論語》列於小學,與《孝經》、《爾雅》並視,已為不倫。而重視五經,特立博士,為國家教育之最高課程,因此以求通經致用,則乃自著述事業遞次及於政治事業,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則不免轉居其後。故在漢代博士發揚孔學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轉成為對古代經典之訓詁章句,此豈得與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擬。則無怪乎至於東漢,博士皆倚席不講,而太學生清議遂招致黨錮之禍,而直迄於炎漢之亡。此下莊老釋氏迭興並盛,雖唐代崛起,終亦無以挽此頹趨。此非謂《詩》、《書》、《禮》、《易》可視為與儒學無關,乃謂孔子畢生精神,其所謂學不厭、教不倦之真實內容,終不免於忽視耳。
宋代儒學復興,乃始於孔子生平志業之重要性獲得正確之衡定。學與教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餘事。故於五經之上,更重四書,以孟子繼孔子而並稱,代替了漢唐時代以孔子繼周公而齊稱之舊規。此不得不謂乃宋儒闡揚孔子精神之一大貢獻。宋儒理學傳統迄於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漢,自標其學為漢學,乃從專治古經籍之訓詁考據而墮入故紙堆中,實並不能如漢唐儒之有意於通經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樹。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學與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瞭。下及晚清末運,今文公羊學驟起,又與乾嘉治經不同。推其極,亦不過欲重返之於如漢唐儒之通經而致用,其意似乎欲憑治古經籍之所得為根據,而以興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隔離仍遠。人才不作,則一切無可言。學術錯誤,其遺禍直迄於民國創興以來之六十年,中共邪說獲得乘虛而起。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復興中國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傳統,而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為目前當務之急。本書編撰,著眼在此。爰特揭發於序言中,以期讀者之注意。
本書為求能獲國人之廣泛誦讀,故篇幅力求精簡。凡屬孔子生平事蹟,經歷後人遞述,其間不少增益失真處,皆一律刪削。本書寫作之經過,其用心於刊落不著筆處,實尤勝過於下筆寫入處。凡經前人辯論,審定其為可疑與不可信者,本書皆更不提及,以求簡淨。亦有不得盡略者,則於正文外別附疑辨二十五條,措辭亦力求簡淨,只略指其有可疑與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於考證辨訂之詳。作者舊著《先秦諸子繫年》之第一卷,多於孔子事蹟有所疑辨考訂,本書只於疑辨諸條中提及繫年篇名,以便讀者之參閱,更不再事摘錄。
自宋以來,關於孔子生平事蹟之考訂辨證,幾於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為多。綜計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數十百家。本書之寫定,皆博稽成說,或則取其一是,捨其諸非。或則酌采數說,會成一是。若一一詳其依據人名、書名、篇名及其所以為說之大概,則篇幅之增,當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盡量略去,只寫出一結論。雖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誇多之譏。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錄》及《續錄》兩編,為考訂辨論孔子生平行事諸家中之尤詳備者。其書亦多經後人引用。惟崔書疑及《論語》,實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並《論語》而疑之,則先秦古籍中將無一書可奉為可信之基本,如此將終不免於專憑一己意見以上下進退兩千年前之古籍,實非考據之正規。本書一依《論語》為張本,遇《論語》中有可疑處,若崔氏所舉,必博徵當時情實,善為解釋,使歸可信,不敢輕肆疑辨。其他立說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標為作者個人之創見。立說必求有本,羣說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竊願以此自附於孔子之垂諭。
作者在民國十四年曾著《論語要略》一書,實為作者根據《論語》為孔子試作新傳之第一書。民國二十四年有《先秦諸子繫年》一書,凡四卷,其第一卷乃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諸家,詳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民國五十二年又成《論語新解》,備采前人成說,薈粹為書,惟全不引前人人名、書名、篇名及其為說之詳,惟求提要鈎玄,融鑄為作者一家之言,其體例與今書相似。惟新解乃就《論語》全書逐條逐字解釋,重在義理思想方面,而於事蹟之考訂則缺。本書繼三書而作,限於體裁有別,於孔子學術思想方面僅能擇要涉及,遠不能與新解相比。但本書見解亦有越出於以上三書之外者,他日重有所獲不可知,在此四書中見解儻有相異,暫當以本書為定。讀者儻能由此書進而涉及上述三書,則尤為作者所私幸。
本書作意,旨在能獲廣泛之讀者,故措辭力求簡淨平易,務求免於艱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盡求通俗化。如《論語》、《左傳》、《史記》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書皆引錄各書原文,未能譯為白話。一則此等原文皆遠在兩千年以上,乃為孔子作傳之第一手珍貴材料,作者學力不足,若一一將之譯成近代通行之白話,恐未必能盡符原文之真。若讀者愛其易讀,而不再進窺古籍,則所失將遠勝於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義理深邃,讀者苟非自具學問基礎,縱使親身經歷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難得真實之瞭解,此其二。又孔子遠在兩千五百年之前,當時之列國形勢、政治實況、社會詳情,皆與兩千五百年後吾儕所處之今日大相懸隔。吾儕苟非略知孔子當年春秋時代之情形,自於孔子當時言行不能有親切之體悟,此其三。故貴讀此書者能繼此進讀《論語》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於孔子言行與其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之第一大聖人者,能不斷有更深之認識。且莫謂一讀本書,即可對瞭解孔子盡其能事。亦莫怪本書之未能更致力於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讀本書而盡獲其所欲知,則幸甚幸甚。
本書開始撰寫於民國六十二年之九月,稿畢於六十三年之二月。三月入醫院,為右眼割除白內障,四月補此序。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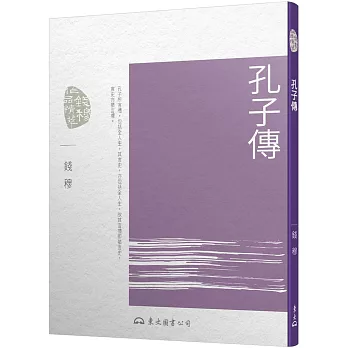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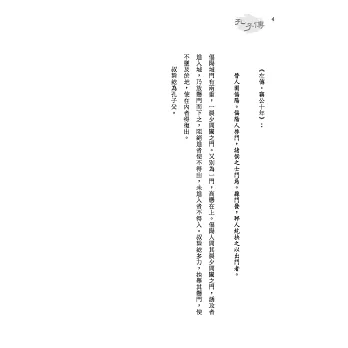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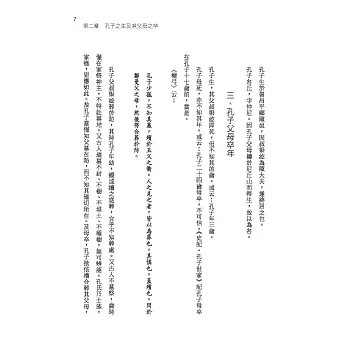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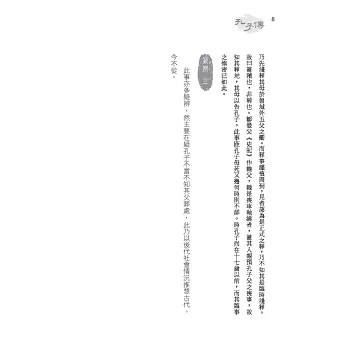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