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現代學者對孔子之前的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宗教,一般抱著相當強烈的敵視態度。對他們來說,現代與古代中國兩者之間,在思維及情懷上,似乎存在著一道令人無法跨越的鴻溝。外表看來,那些現代學者儼如他們的祖先,有完全相同的外貌特徵,但是他們內心的思維跟他們的祖先卻早已背道而馳,呈現出南轅北轍之勢。二十世紀最震撼中國學術界的發現之一應該是甲骨文,現代學者對甲骨文字面的意思一般都能理解,但至於潛藏在文字背後的思維就難免令他們不時有扞格不入的感覺。甲骨文是當時人神交通的記錄文字,現代學者或因受到孔子遠離鬼神思想的影響:「敬鬼神而遠之」,或因遵奉馬克斯(1818-1883)無神論的教條,一談到求神禱告,常有嗤之以鼻的傾向。因此他們看活在商朝事事尋求上帝的旨意的人,往往有輕蔑的態度,不是說他們迷信,就是說他們騙人,或者說他們愚蠢﹔換句話說,在現代一般學者的意識或潛意識中,他們活在商朝的祖先理當都是不入流的人物。當一個人把現代學者對他們祖先的敵意與春秋戰國以前的學者包括孔子和墨子對他們祖先的讚譽之詞互相對比的時候,現代學者對他們祖先蔑視的態度就難免更令人詫異了。究竟是現代學者對他們祖先的評價正確,還是春秋戰國以前的學者對他們祖先的評價正確,茲事體大,是每個學者都應該正視深思的問題。就時間上來說,春秋戰國以前的學者距古代比現代學者距那些時代要近,所以春秋戰國以前的學者對他們祖先的看法一般應比現代學者深入可靠些。就可信的記錄來說,中國的祖先如堯、舜、禹、湯、文、武,他們的為人、作風及思維,筆者以為確實要較後代的帝王高妙許多,他們所領導的世界因此不可能就一定比後世罪大惡極的多,應該不會如許多現代學者所描繪的盡是一個愚蠢無知和迷信的時代。其實,堯、舜、禹、湯、文、武的大環境所以能造就出他們傑出的人品與才智的事實即明確的顯示出,他們所活躍的世界在思維文化上其實有可能勝於後世的地方。
先秦以前的文化,根據社會政治體制和思維來看,大抵可分成兩大類,一為公天下的體制與思維,一為家天下或私天下的體制與思維。公天下的體制與思維的中心是神,焦點放在上帝的身上,或者放在超越這個世界的一個永恆的精神世界上,英文稱之為「彼世界 otherworldly」的思維﹔而私天下的體制與思維的中心卻是自我,焦點放在這個世界,對超越這個世界的事情興趣乏然,英文稱之為「此世界 this-worldly」的思維。以一己為據點的私天下思維形式發展到極端便是利己主義,「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在以上帝為據點的思維形式中,這種思維發展到極點就是利他主義,中國遠祖堯、舜、禹時代的精神和春秋戰國時代墨子的主張是這種公天下思維典型的例子,現代西方先進的文明國家所接受的基督教也隸屬於此一範疇:「我不再活著,而是基督活在我裡面 ζῶ δὲ οὐκέτι ἐγώ, ζῇ δὲ ἐν ἐμοὶ Χριστός。」(《聖經‧新約‧加拉太書2:20》)中國私天下體制所產生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在利己與利他的思維折中之後出現的哲學,孔孟稱之為中庸思想:「閑先聖之道,距楊墨」。自從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後,中國傳統學者致力尊孔,同時排斥其他諸子的學說,完全以儒家的論點為根據,一心認定從堯、舜到孔子的思維是本質相同一脈相傳的中國道統,這種說法不但誤解了堯、舜及孔子思想不同的本質,同時助長了私天下體制對中國持續不斷的戕害。甚至到了現代體制變成共和以後,中國的災難不但不減,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最根本的原因便在於一般現代學者對先秦文化有令人扼腕的偏見與誤解。
堯、舜時代公天下的共和體制,傳賢而不傳子,用人不是一味的只憑關係,而主要以賢能與否為標準,整個邦國的精神與體制的運作都在於體現神的誡命,照顧天下的生民百姓,「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上帝命令當時的君王不分區域疆界去照顧天下的生民百姓,而不是一心為己為家。當時一般人生活的中心、重心與基礎是主宰宇宙萬物的聖潔的神,例如舜還只是一個普通百姓的時候,他的父親、後母及同父異母的弟弟企圖謀殺他,《尚書‧大禹謨》記載說他每天到田裡,「日號泣于旻天」,向天伸冤,結果「至諴感神」,得到神的幫助,最終獲得堯的青睞。《詩經‧大雅‧生民》也傳述周始祖棄一生下來就被家人拋棄,後來得到神的幫助,成為堯、舜信賴的農業大臣,不僅建立了周朝農業社會的基礎,更教導了周人敬天畏神的精神。禹在外治水,孟子說他八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史記》說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以今天強調私天下家庭倫理的角度來看,不是不近人情就是大逆不道,但是禹那個時代強調的不是人或家庭,而是天或上帝,他當時所想的主要不是他自己或他的家人,而是聖潔的上帝。神要禹治水,照顧百姓,不要說八年,十三年,就是更多的時間,他都必須遵從神的旨意三過家門而不入,孔子說他「致孝乎鬼神」,而不是孝順父母,說得再清楚不過,就是指當時人跟聖潔的神之間密切的關係﹔在這一點上,孔子因距離禹的時間比現代學者近,所以孔子的說法比眾多現代學者漠視神而企圖將禹塑造成一個孝順父母的人要正確可信許多。
因為歷代帝王的提倡,孔子的思想對中國文化有無比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孔子可說已經成了偶像,他的學說在傳統文化中一向被認為是從堯、舜傳下來的道統的一部分,筆者在書中對孔子跟堯、舜的思想在本質上根本歧異的地方做了詳細的分析。孔子的仁是強調人際關係、嚴分階級、講究等差之愛且以人君為基礎、遠避鬼神、帶有自私自利色彩的思想。人君在孔子的人倫思想中是至高無上不受任何人制約的獨夫,他可以為所欲為,雖然人臣可以建議,但聽不聽只能由君主個人做主,旁人是無法勉強的,君主不聽,臣子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禮記‧曲禮下》說:「為人臣之道,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顯」這個字一般被解釋成公開的意思,筆者以為大臣跟君主私下相處的機會有限,如果做公開解,大臣不能在公開的場合對君主進諫,那麼大臣可以進諫的機會就會少之又少,甚至可能根本就沒機會進諫。「顯」這個字在這裡應該解做明顯或者俗語所說講話講得太露骨的意思,《禮‧曲禮下》建議大臣進諫應該要委婉含蓄,不要說得太過強烈,針鋒相對,把局勢鬧僵,斷絕了後來繼續進諫的機會。這跟《禮記‧坊記》中所說的「微諫不倦」的「微諫」意思相同,就是鄭玄註中所說的「怡色柔聲以諫」的態度。禮記說一個臣子如此進諫可以諫三次,諫了三次以後,君王不聽,就只能離開。《禮記‧表記下》同時記載孔子有關大臣進諫君主的一段談話說:「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孔子以為一個大臣服侍君主,進諫三次以後都無效,大臣還不離開,那就是貪心利祿了。孔子在《論語‧先進》裡更進一步解釋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果君王不聽大臣的意見,孔子認為做臣子的最後只有離開朝廷一途。
本書在詳細分析孔子的學說時,指出孔子主張的君臣之道含有極大的弊端,他強調的「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和《禮記》的「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基本上是一種消極逃避的私天下思維,與提倡公天下思維的墨子組織了強大的軍事隊伍,跟草菅人命的奸邪君主進行殊死鬥,兩者的心態完全相反。孔子對不利的政治局勢主張消極逃避的態度,影響了無數中國人的心態,導致一般中國人對邪惡常常產生妥協逃避的現象,因應這種情景而出現的中國成語,「溜之大吉」與「三十六策,走是上計」,很明顯的表現出臨陣脫逃在一般中國人眼中,不僅不是一件羞恥的凶兆,反而被頌揚成大吉祥的智慧。孔子的教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對解決腐敗的政局不僅毫無助益,反而令邪惡小人雀躍不已,奸臣賊子最喜樂的事莫過於所有的正人君子都自動退出政壇,國家政府完全由他們把持,中國一亂再亂,這跟孔子所主張的儒家思想對邪惡採取消極逃避以及無條件妥協的私天下思維有不可分的關係。本書正文會提到,當孔子的祖國魯國有亂,孔子立即跑到齊國去避亂﹔當陳國有亂,他又跑到衛國去尋求一官半職,孔子跟一個國家的關係,有如日常用語中所說的酒肉朋友,承平之時,關係密切,遇到災難,人便不見蹤影,頓時煙消雲散。齊國甚有氣節的大臣晏嬰和備受現代學者推崇的墨子對孔子的評語:「繁飾邪術以營世君」,應該不是無稽之談。
在世界文化史上,對邪惡的政治現實能夠永久堅持爭鬥的民族,就筆者所知,大概就是以色列人了。猶太人跟華人都是散佈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但是猶太人所以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原因與華人基本上大相徑庭。華人大體遵守孔子的教訓,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碰到亂世,比如西晉時的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本能的反應就是「三十六策,走是上計」,而「溜之大吉」,從中國北方逃到南方,再從南方逃到南洋或世界其他各處去:「河北士族大多逃奔幽、并等晉室遺存州鎮。所以在『永嘉之亂』中,流亡江東的士族大多來自黃河以南地區─後來,這被視為客家人的發祥地。」1960年代臺大政治系教授黃祝貴所寫的一篇文章,「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就是描述這種在危險混亂的困境中力圖逃亡的私天下思維在臺灣所造成的現象。正統猶太人的觀念與受孔子影響的華人迥異,即使生逢亂世,猶太人一般會死守家園,全力抗爭,拒絕脫逃:「耶華神是我的庇護所,你們怎麼可以跟我的靈魂說:『你應該像鳥一樣逃到山裡』」(聖經‧詩篇11:1)。以色列亡國以後,大批的猶太人被亞述王強迫遷徙離開他們熱愛的家園,「於是亞述王把以色列驅趕到亞述,把他們安置在哈拉和哈勃,溝攘河,馬答的各個城市中 וַיֶּ֧גֶל מֶֽלֶךְ־אַשּׁ֛וּר אֶת־יִשְׂרָאֵ֖ל אַשּׁ֑וּרָה וַיַּנְחֵ֞ם בַּחְלַ֧ח וּבְחָב֛וֹר נְהַ֥ר גּוֹזָ֖ן וְעָרֵ֥י מָדָֽי:」(列王記下18:11);如此,猶太人開始散佈到世界各地,他們不像一般中國人,動輒口誦「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溜之大吉」,自動移民,尋求安樂之地;他們也不像新加坡的華人一樣,在中國之外,另外建立一個國家。即便猶太人身在國外,他們普遍一貫的信仰還是要返回以色列的家園。他們遵守神的教導,對家園流露出無比的熱愛:「因為你的僕人迷戀她的石頭,熱愛她的塵土 כִּֽי־רָצ֣וּ עֲ֖בָדֶיךָ אֶת־אֲבָנֶ֑יהָ וְאֶת־עֲפָרָ֥הּ יְחֹנֵֽנוּ」(詩篇102:15)。就因為這種死守家園、力爭不懈的信念,他們在亡國長達兩千多年以後,能夠從世界各地的角落再回到他們的故土,驅逐佔領他們故土的異族,重建以色列國,一躍成為中東的超級強國。猶太人這種堅持不懈的公天下思維,對深受孔子私天下思維影響、動輒逃亡的中國人,確實有值得借鑑之處。
因為孔子把君主推舉為人倫社會的至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一般因此都有偏袒君主的跡象。在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司馬遷的《史記》把君主與臣子分開來列傳,君主的部分稱為「本紀」,臣子分成兩個部分,位高權重且有重要影響的臣子成為一個單元,稱為「世家」,一般的臣子另成一個單元,名為「列傳」﹔在列傳的這個部分,司馬遷把一些奉公守法的官員合在一起,立了一個「循吏列傳」,另外也把一些殘酷的官吏別立一章,稱為「酷吏列傳」。司馬遷把君主與臣子分開立傳的體例清晰地表明了在他的私天下思維中君臣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就他來看,獨佔天下的君主高高在上,顯然不可用善惡來區分,而臣子卻有必要以善惡來論斷,循吏應該稱揚,酷吏應該貶斥。《宋書》的列傳雖然有二凶,《南史》雖然有賊臣,但是兩書都是把殺害君王的大臣列為邪惡的臣子。真正開始把人品邪惡的臣子挑出立傳的是宋朝歐陽修和宋祁合撰的《新唐書》,分有奸臣、逆臣、叛臣三類,《宋史》沿襲《新唐書》的體例,列有奸臣和叛臣,《元史》照列奸臣和叛臣,《明史》也有奸臣傳,從歐陽修和宋祁合撰的《新唐書》開始,「奸臣」在中國史上便成了一個常用的詞。相對的,君主卻一直沒有忠奸之分,似乎他們總是超乎邪惡之上。歷史上到處都是奸臣,而卻不見「奸君」這個詞,傳統的歷史因此往往把過錯推給大臣,而卻處處設法替君主開脫罪名,似乎做了君主就絕對不可能變成奸人,跟奸就毫無關係。以家喻戶曉的岳飛為例,照私天下的想法,天下是趙家的天下,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君王一人的奴婢,他們能活著全是趙家的恩典。如此,岳飛枉死只能完全是奸臣秦檜的過失,「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至於高宗似乎什麼罪過都不必擔當。
其實在私天下的中國,在正常的情況之下,大臣一般都是看君王的臉色行事,君王寵信的大臣也往往是那些特別能揣摩主上心意的臣子,那些寵臣所以能手操重權,也是因為君王知道他們會照自己的心意辦事,所以那些奸臣的罪行就這一層意義來看,應該也是君王的罪過。如果沒有宋高宗的首肯和授意,秦檜應該是殺不了岳飛的,所以岳飛的死絕對應該歸罪到宋高宗。此外,就公天下的思維來說,岳飛是自絕生路。他大可以像舜、湯、文王、武王和墨子一般,選擇對抗的辦法,但是私天下的心態是「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這是公天下與私天下思維根本不同的地方之一。即使舜的全家要殺他,但是如果聖潔的上帝要他活,他就不能不活,而且要活得非常有尊嚴,所以不管誰要殺他,他就不能不抗爭。而在私天下的思維中,君令一下,就只好俯首聽命。晉獻公的太子申生如是,秦始皇的太子扶蘇也如是,即使他接到的詔書不是秦始皇的手筆,而是趙高偽造的文書,顯然只要是詔書,不論對錯,就必得順從,這是私天下思維必然的局限之處。
中國一般的知識分子經過數千年儒家思想的薰陶,和政府宣傳教條無止境的灌輸之下,在潛意識中,早把邦國領導看做一個超凡入聖近乎神的特殊範疇,君王在所有的事情上,幾乎都有道德豁免權。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如果要擺脫此一私天下思維的桎梏,對堯、舜、禹、湯、文、武和墨子所代表的公天下思維理當有所認知,在公天下的思維裏,普天之下,就如墨子所說:「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或如莊子所說:「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人皆是天的臣民與子女,在聖潔的神的面前,一律平等,沒有永久享受道德豁免權的特權階級存在的空間。天下既不是趙家的天下,江山也不是愛新覺羅的江山,而屬於所有的人。公天下與私天下的區分,不僅呈現在體制上,更顯示在思維中。在邁向公天下的旅程中,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僅須要注意體制的建立,更應該講究所以成就其特有體制的公天下精神。筆者以為,如果沒有相應的公天下精神,即使建立公天下的體制,而支撐體制運作的仍然是私天下的精神,結果往往也是徒具虛文,表面文章,所謂掛羊頭,賣狗肉,在表裡不一的情形下,不會有太多的實質意義可言。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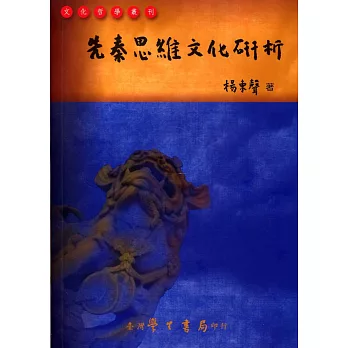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