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面對死亡,追求本真的存在
黃光國
這本《愛與意志》是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Rollo May的成名之作,原書在一九六九年由紐約諾頓公司出版。Rollo May在西方精神醫學界極富盛名,在台灣卻鮮少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於:長久以來,台灣心理學界一直籠罩在「素樸實徵主義」的陰影之下,對心理分析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已經是屈指可數;對存在主義心理分析下過工夫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在利潤掛帥的資本主義時代,台灣的出版市場到處充斥著許多沒什麼學術價值的通俗心理學譯作,這本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的扛鼎鉅著,雖然在二十年前經由「志文出版社」翻譯出版,卻早已絕版多時,二十年後的今天,「立緒文化編輯部」才又重新規劃,譯成中文,這大概只能怪台灣學風澆薄,這類著作「知音難覓」吧?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本書,我們當可發現: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對於台灣社會中的男男女女,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十分適用。為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說明存在主義所產生的時代背景。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理性主義的勃興,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同時也造成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金錢」和「權力」變成兩種最具主導力的價值觀念,許多人都喜歡絞盡腦汁,希望以各種不同的「知識」作為「工具」,來追求「金錢」和「權力」。結果西方文明從希臘時期以來對於「理論理性」的追求,異化成為「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人類的存在方式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海德格認為:人「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選擇「是自己本身」,他稱之為「本真的存在」;另一種是選擇「不是自己本身」,他稱之為「非本真的存在」。對於這兩種存在方式作出抉擇之後,則個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對自己的態度不同,和別人的關係不同,連時間觀也會有所不同。處於「本真的存在」狀態,個人所使用的是「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他並不像笛卡兒哲學那樣,將自己想像是和客體對立的主體,相反的,他會開放自己,放鬆自己,讓世界中的事物降臨到自己身上,和自己融為一體,這種境界海德格稱之為「與物同遊」(in play within the matter itself)。在這種境界裡,個人是他真正的自己,他人也會如其所是地展現其自身,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互為主體性的了解,他們之間的關聯,也有一種時間上的連續性和延展性。
「非本真的存在」則不然。在這種存在狀態裡,個人把自己想像成是和外在世界對立的「主體」,並且企圖用「技術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或「形上學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來掌握或操縱外在世界中的客體。當他用這樣的方式和他人互動的時候,他會選擇「不是自己本身」,努力地把自我隱藏起來,並且盡量變得跟「常人」一樣。如此一來,他既不需要作任何的道德抉擇,也不需要擔負任何責任,因而也喪失了所有的自由。在這種「非本真的存在」狀態裡,時間觀的表述方式是「現在—現在—現在」,因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沒有什麼值得回憶的;未來的尚未到來,也很難有所期待。個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握現在」。
在這本著作中,Rollo May指出:在西方傳統中,有四種愛的形式。第一種是性,西方人稱之為肉慾(lust)或力比多(libido)。其次是愛慾(eros),這種愛的驅力令人有繁殖和創造的慾望。第三種是朋友之愛,希臘人稱之為philia,第四種是「同胞愛」,或agap憿A意指會為他人的福祉設想,譬如:「神愛世人」即為此種愛的原型。然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西方人開始把他們的關懷集中在以肉慾為主的「性」之上,以為它可以取代愛的其他形式,「我們從假裝性根本不存在,猛地轉入一個全心全意為性著迷的狀態」,任何書店都可以買到談論性知識或性技術的書籍,每一天的報紙都可以看到許多有關避孕、墮胎、通姦或同性戀的消息,「人們大方地在性行為中裸露自己的身體,然而,對伴隨著溫柔而來的心理層面和心靈層面的裸露,人們則顯得戒慎恐懼」。為了克服自身的孤獨狀態,為了逃脫空虛感和冷漠的威脅,人們把自己變成了一部「性愛機器」,「伴侶們氣喘吁吁地顫抖著,希望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同樣的顫抖回應,好證明自己的身體並未麻木」。怪異的是:性行為愈開放,人們對性歡愉的感受卻愈來愈淡,熱情也減低到幾乎消退的地步,性關係變得枯燥乏味,甚至服用迷幻藥也無濟於事。Rollo May毫不含糊地指出:這種「性格分裂的人,其實是技術化之人的自然產物」,他們躲避親密關係,碰觸不著親密關係,甚至無法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用海德格的概念來說,這是屬於「非本真之存在」狀態,在異性關係或人際關係方面所顯現出來的特色。
然則,有什麼力量可以使由這種「非本真的存在」「選擇」成為「本真的存在」狀態呢?海德格認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超拔到「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一個人都會死,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在使用「技術性思考」的盤算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世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會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本質,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
同樣的,Rollo May也認為:對於死亡的覺識將使我們對於愛情的價值有更廣闊的開放性。在本書第四章的開頭,他引述著名心理學者馬斯洛在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後所寫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死亡,和它終將現身的可能性,使得愛、熱情的愛,成為可能。倘若我們知道自己將永遠不死,我懷疑我們是否還能如此熱情相愛,是否還能經驗到這等狂喜。」更清楚地說,就本書所關懷的「愛與性」而言,個人也是要清楚地認識到:人是一種「面對死亡的存在」,他才會反省並仔細評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價值;這時候,他才有可能選擇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不再把異性當做是滿足個人性慾的工具,而樂於和對方建立長久的穩定關係。愛與意志合而為一,他對於肉慾的耽迷才有可能超拔成為對於「愛慾」的嚮往。在這種存在狀態裡,時間並不是以「現在」作為核心,由「過去」奔向「未來」的直線型流失過程;而變成一種「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不斷往復循環:「過去」和「現在」打通了,走向未來也可回復到「過去」,人的存在不再是全然的空無,反倒蘊含著無限多的可能。
談到這裡,我們便可以回過頭來說明:為什麼我認為Rollo May的這本鉅著對於今日的台灣社會仍然有高度的適用性。台灣的文化發展一向是跟在西方社會之後,邯鄲學步,亦步亦趨。西方文明中蘊含有「工具理性」或「技術性思考」的文化質素,通常都會像疫病一樣地快速傳遍台灣社會;然而,西方思想家對其文明發展的深刻反思,通常都要晚個三、五年甚至二、三十年,才能經由少數知識份子的引介,逐漸為人所知。在過去幾十年中,在一批所謂「現代化派」知識份子的狂吹濫捧之下,傳統社會中的性道德和性規範早已土崩瓦解;對於新世代的年輕人而言,什麼「一夜情」、性解放、搖頭丸、墮胎、未婚媽媽、同性戀……等等,都是司空見慣之事。年輕人不管發生任何性的糾葛,許多「心理學家」和「輔導專家」的建議一定是「加強性教育」。在這種「性技術思考」氾濫成災的時代,將這本《愛與意志》譯成中文,讓我們對於自身的時代處境,有多一點反思的空間,誰曰不宜?
在對本書做完引介之後,作為一個致力於推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學者,對於本書的內容,我還想做一點提示。我們在讀本書的時候,切不可忘記: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西方的心理學家,他在書中雖然偶爾也會提到東方文化的觀點,但整本書的思維理路卻是純粹西方式的。比方說,在本書中,他花費許多篇幅所討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愛慾」或「愛洛斯」(Eros),就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跟傳統中華文化可以說是完全不相應的。在一篇題為〈自由與自律之間〉的論文中,哲學家唐力權曾經用一段十分精闢的話來突顯中、西文化在這一方面的對比。他說:中國人的文化心靈是「良知型」(良知偏勝)的,而非「愛羅型」(愛羅偏勝)的。愛羅心性(Eros)乃是一個喻於「自體性價值」的心性,而良知心性卻是一個喻於「互體性價值」的心性。愛羅人所突顯的乃是「材知愛慾」的「自由本能」,而良知人所彰顯的卻是「仁恕關懷」和「悱惻本性」;前者是一種「異隔對執」的本能,而後者則是一種「同體感適」的本性。
唐氏所謂的「愛羅型」或「愛羅偏勝」,就是本書所說的「愛慾」或「愛洛斯」。換句話說,所謂「本真的存在狀態」,對於西方人和華人是截然不同的。這樣的差異,恰恰是中、西文化最最尖銳的對比所在。當然,由於篇幅所限,在此我無法繼續深論:什麼是「良知型」(良知偏勝)的「仁恕關懷」和「悱惻本性」;它和西方的「愛羅型」(愛羅偏勝)又有什麼不同。這裡,我只能留下一個引子,希望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潮流導引之下,有些年輕的學者能夠繼續思索這個問題,針對華人社會中的實際情況,另外再寫一本中國式的《愛與良知》。
二○○一年二月一日
譯序
羅洛.梅——存在主義與精神分析之實踐者
彭仁郁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羅洛.梅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艾達城(Ada)。父母的離異與其姊的精神病發作,必定在羅洛.梅幼小的心靈中,暗自種下日後探索人類精神奧秘的種籽。在密西根大學就讀時,他因積極參與一激進派學生雜誌的出版而被勒令退學,乃返回俄亥俄州,於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取得學士學位,其後,轉赴希臘亞納托利亞大學(Anatolia College)教授英文,為時三年。訪歐期間,羅洛.梅以巡迴藝術家的身分實現其對繪畫的熱情和渴望,並曾短暫地求教於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的開山祖師阿德勒(Alfred Adler)。返美後,進入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結識當代重要神學暨哲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並於一九三八年獲得神學士學位。
身為猶太人的田立克在二次大戰、希特勒執行種族清洗屠殺期間,流亡到美國,其大半家人皆未逃過納粹魔掌;對於人類心靈深層之惡魔傾向有親身體驗的他,一直在基督教信仰的現代社會脈絡中,探問惡的終極意義。羅洛.梅在本書中之所以試圖藉「原魔」(daimonic)概念,以解構愛與意志的對峙處境,應受其影響至深。當然,他自身與病魔對抗的經驗,亦不容忽視。由於感染肺結核,羅洛.梅臥病在床整整三年,此病在當時仍無藥可治,令他幾度徘徊於死亡邊緣,然而一旦病情稍微緩和,他便貪婪地閱讀。在其青睞的作家之中,丹麥宗教哲學家齊克果(S顤en Kierkegaard)的存在哲學觀點,在羅洛.梅建構其存在主義心理學理論的道路上,宛如指引明燈。
大病初癒的羅洛.梅,進入懷特學院(White Institute)接受心理分析訓練,此間,他與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佛洛姆(Erich Fromm)等美國心理學界內扛鼎級人物,過從甚篤。一九四九年,他自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成為該校首名獲頒此頭銜的畢業生。
次年,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學專著《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該書首度有系統地提出「一般性焦慮」(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慮」一詞跨越心理病理專有名詞的囿限,而將之引入一般心理現象的範疇,以描繪現代科技發展對人類整體生活處境的徹底改變,如何導致現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緒問題。而在此科技理性時代所造成的特殊心理景觀(即社會學中所稱之「異化」)中,羅洛.梅觀察到現代人內在空虛感的關鍵,乃是因為愛與意志的舊有倫理力量已然遭到嚴重斲傷,而使得人類在面臨生命本身所發出的根本質疑時,悵然若失怙孤兒,伶仃無依。羅洛.梅進一步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愛已被簡化為性,而意志亦被誤解為過度理性、嚴竣的意志力。其著書之目的,即在重新定位古希臘的「原魔」(daimonic)——此一介乎意識與潛意識、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原型力量——概念,說明此原型力量乃為愛與意志的共同根源。依此觀點,愛與意志其實是人類在每一個當下所展現出的生命動力;而且,這眼前的當下,延續著過去(史性經驗)、並投向未來(歷史之開創)。此時間三向度的融會,即涉及羅洛.梅在本書中所欲重新詮釋的另一概念——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此概念雖然轉借自胡塞爾現象學之語彙,但是,當羅洛.梅試圖運用此構念,作為心理分析治療發生效用的根本關鍵時,即已脫離了胡塞爾藉其說明意識與意識對象間關係的哲學脈絡,而跨進了存在主義之境域。亦即,在人們面臨茫然未知的生命處境時,意向性如何成為既在後推動、又在前牽引的力量;這個力量不僅是意識的、理性的,亦為潛意識的、超越理性的。
羅洛.梅是將歐洲存在主義思潮引介至美國心理學界的重要拓疆者之一。讀者不難從字裡行間,看出他意欲在精神分析的基底之上,建構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努力。曾在病榻間撫慰羅洛.梅、更鼓舞他與病魔相搏的存在主義先驅齊克果,在日記中寫著:「我必須尋得一個對自己為真的真理;而此真理中所蘊含之意念,將足以教我為之而生、或為之而死。」自此開始,倫理學便反叛了柏拉圖式的價值觀,不再認為人世間應存在一種普遍而客觀的道德判準,因為,人所尋求的真理是否為真,唯有作為主體的人有資格評斷;但是,繼主體擁有選擇的自由之後,伴隨此自由而來的則是承諾和責任。然而另一方面,由於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論對於潛意識力量的揭發,卻彷彿默默支持著行為主義之生物決定論觀點,聯手削弱了存在主義所頌讚的主體自由。
面對此自由與制約的爭戰,比羅洛.梅晚生六年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在《自由與虛無》中藉由自在存有(en-soi)和自為存有(pour-soi)的總體性辯證,導出了「人注定是自由的、並且此自由將在對宿命論的永恆反抗中獲得」的結論。同樣受到存在主義與精神分析之波瀾衝擊,並據此二大思潮以建構自身理論的羅洛.梅,卻未選擇沙特式的基進反叛路線,他所採取的是中庸法則,試圖將對立的兩端,統整、併匯在一圓融之體系中。在他的想法裡,認為人類必須先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是被決定的,然後才能談論自由選擇的問題。在羅洛.梅心理學理論的鋪陳中,我們可時時嗅到中國傳統哲學裡陰陽相合的氣韻。比方「原魔」的善惡並存、兼具創造與毀滅力量;愛與意志的相生相依、不可或離等等。對羅洛.梅而言,任何一種形式的心理治療,其目的皆是在幫助病人獲得自由,而達成此目標的根本途徑,即為接納自身的原魔、學習聆聽潛意識的呼聲,並從愛與意志的共同實踐中,回應生命對人類所不斷拋出的意義探問。
在翻譯全書的過程中,最令譯者頭疼的便是「原魔」(daimonic)這個詞彙的譯法。劉崎先生在所譯之《悲劇的誕生》(尼采著/志文出版社)中,曾經將這個詞譯成「魔性」;另外,王溢嘉先生則在其所編著之《精神分析與文學》(野鵝出版社)一書裡,譯為「原始生命力」。為了想強調daimonic作為一潛意識原型力量的面向,譯者雖感羞赧,卻仍大膽地提出「原魔」的譯法。至於此譯法是否適切地呈顯此概念的實際意涵,還請讀者細讀本書之後,不吝指正。此外,羅洛.梅在本書第五章中,對於向蘇格拉底借用此概念的典故,有此一述:
……當蘇格拉底因被指控教授青年學子謬誤的「魔鬼學」而受到審判時,他如此描述自身的「魔」(daimon):「這個徵兆在我尚年幼時,便以一種聲音向我顯現。」
但事實上,上文中的「魔」(daimon)字,意謂的乃是「原魔」(daimonic),換句話說,它並非為一具有想像實體的生命形式,而是一種超乎理性、橫跨意識與潛意識,暗暗影響人所作所為的原型力量。由於在英文中,daimon和daimonic字根(按:來自古希臘文,詳見第五章註 ,以及內文中關於此概念的說明)相同,其意涵可神可魔、亦善亦惡、忽虛忽實。因此行文間,羅洛.梅經常在daimonic和daimon二詞之間來去自如地交互使用著。這一來可苦了學養甚淺的譯者,因為中文裡並無相對應的概念,最後,譯者不得不和自己的智力妥協,分別依上下文將daimon譯為魔(意指原魔)、魔鬼(現代日常生活中之指稱)或惡魔(當原魔全然展現其邪惡面向時)。
此外,書中某些段落行文背後的預設,不時衝撞著譯者的思考邏輯和倫理觀。每當羅洛.梅在談論性愛時,總不脫一種中古世紀騎士精神的口吻,彷彿欲藉其論述,諄諄善誘仍不識愛情真諦的男士們,真誠地對待自己的情感,選擇一個女人,並藉意志之助,讓愛繼續。此種將男性視為想像論說對象、並以異性戀關係作為參考架構的愛情論述,想必教時下對性別議題已具相當敏感度的讀者,感到不解,甚至可能引起某些女性主義者或性解放運動者的攻訐。然而,我們必須考慮到作者本身性別經驗及社會文化背景的限制。他在撰寫本書時,女性主義思潮猶方興未艾,而性別研究和同志論述亦仍在懷胎階段;當今讀者(當然包括譯者在內)已習以為常的性別多元觀點,在羅洛.梅的時代仍是一片荒蕪,尚待下一世代運動者的開墾、耕耘。念頭稍轉,譯者思及在閱讀中所呈現的兩個並置時空(三十年前的美國/甫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正映照出文化思考一路行來的足跡,便不禁豁然莞爾。或許,誠如羅洛.梅所言,如何在每個時代遽變的當口,重新尋得適合該時空脈絡的原魔意涵,才是值得人類深究的根本問題。
作者序
從內在真實中超越永恆循環
有些讀者想必會揣想本書書題中將「愛」與「意志」並置的原因。長久以來,我一直深信愛與意志是相依相屬的。二者皆為存有的連接過程——即,皆為朝向外部影響他人的動作;它們塑造、形成、並創生彼此的意識。然而就其內在意義而言,唯有當一方同時對另一方開放自身、接受對方的影響時,這個過程才可能發生。缺乏愛的意志將會成為操縱——其實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四處可見;而無意志的愛,在當今已成為令人感傷的實驗性作法。
對於這本書中所提出的想法,我不僅懷著作者所慣有的驕傲,也承擔所有的責任。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在這本書前後八年的撰寫過程中,幸有一群朋友閱讀拙作,不吝費時與我討論,才使這些章節的樣貌得以成形。他們是:傑若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朵麗斯.柯爾(Doris Cole)、羅柏特.利夫頓(Robert Lifton)、嘉德納.墨菲(Gardner Murphy)、艾蓮諾.羅柏茲(Elinor Roberts)、恩尼斯特.夏胥帖爾(Ernest Schachtel),以及已故的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謹在此一併致謝。而潔西卡.萊恩(Jessica Ryan)以其直覺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許多實際建議,是任何一位作者都會感激不盡的。
那些在新罕布夏撰寫此書的漫長夏日裡,我經常在清晨時分起身,走到屋外露台上,凝視朝北方和東方山脈連綿而去的山谷,還沈浸在黎明前的銀色晨霧中。在此純然靜謐的世界裡,只有清澈的鳥囀正以哈勒路亞合唱曲,迎接這嶄新的一天。籬雀使出渾身解數熱烈地高唱著,差點就要把自己從蘋果樹頂端的枝椏上顫下來,在一旁的金翅雀則以晨鐘般宏亮的嗓音搭配伴奏著。歌鶇那廂唱得如此全神貫注,一副渾然忘我的神情。還有啄木鳥在空心的山毛櫸樹幹上敲打著節奏。只有湖面上的潛鳥,迸出魔鬼般淒厲的哀鳴,似是為了拯救整個清晨,免於陷入過分甜膩的景象。不多時,朝陽升起,俯視群山,照耀出蓊鬱的新罕布夏,一派不可思議的綠意流淌在長長的山谷中,豐饒得直要氾濫。群樹彷彿在一夕抽長了數吋,而草地間則綻放著無數生著棕色眼睛的小百合。
我再度感到生命永無止境的來來去去,生長、交配、死亡,又回歸於生長的永恆循環。我深知人類也是這去而復返的永恆過程的一部分,分享著此循環所擁有的惆悵,亦參與著生命的謳歌。然而,身為探尋者的人類,由於受到其意識的呼召,不斷地追求超越此永恆循環的方式。無異於他人,我只是選擇了一個不同的領域,以執行這項探尋的任務。我一直堅信,人必須從內在真實中尋求這樣的超越,因我認為,未來價值唯有在歷史價值的播種之下,才能開花結果。在這急遽變遷的二十世紀,當人們已經飽嚐內在價值蕩然無存的後果之時,我想,出發去探尋愛與意志的根源,乃是極為重要的步驟。
羅洛.梅,一九六九年
於新罕布夏州霍德尼斯郡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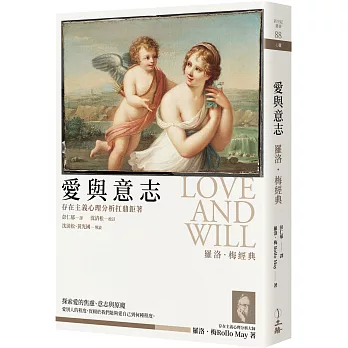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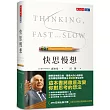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