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迄今為止,安娜對我來說仍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她是我在泉州第一中學同年級的同學。從入學的第一天起,她就給人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同學們的心目中,她清純、優雅,待人謙和而略帶矜持;老師則一致認為她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而在家長們的口中,她就是那個「別人家的孩子」。在她身上匯聚了多少仰慕的目光。然而,六十年代內地的中學生嚴守「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大家在同一個食堂用餐,在同一片操場奔跑,在同一棟教學樓上課,但男女同學之間,除了學習上的問難解疑,很少有機會進行思想交流,更談不上有親密的接觸。借用《西廂記》的一句曲詞來說吧,真可謂「隔花蔭,人遠天涯近」。
轉眼到了1969年,文革的高潮過後,曾經在政治舞臺上叱吒風雲的造反派戰士終於結束了他們的激情歲月。巨人大手一揮,全國兩千萬老三屆知青被送到廣闊天地去繼續革命。泉州一中的同學們來不及說一聲「再見」便各奔東西,走上互不相同的人生旅途。我和安娜重新取得聯繫,已是半個世紀以後的事了。是互聯網將兩個五十年不曾謀面的陌生人變成可以傾心交談的朋友。
今年春天,安娜將她近些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寄送與我。我一口氣讀完了所有篇章,深深地為她的文學才華所折服,就像當年在《中學生作文選》上讀到她的文章一樣。令我驚詫的是,經歷了半世紀的人世滄桑,我的老同學依然保持著青春活力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在退休後的短短數年內,創造這麼多的文學精品。我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促使她作出這樣的選擇?安娜說:我只想把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我們這個民族經歷了什麼樣的苦難。我以為,她已經通過辛勤的勞作,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然而安娜的創作還在繼續。她的詩歌自選集—《邂逅詩歌》又送到我的案前。她要用詩歌的形式講述沒有講完的故事。
翻開這部詩集,我彷彿又回到那個刻骨銘心的年代。我們這班老知青中的文學追夢者,在接受基礎教育的那段時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遺風猶存,民主與科學的文化啟蒙對我們這代人產生了深刻影響。我們曾經如飢似渴地閱讀從域外舶來的文學經典,一大群天才詩人在我們跟前排成長長的隊列:普希金、萊蒙託夫、雪萊、拜倫、葉芝、裴多菲……當然也包括曾經為蘇維埃政權唱過贊歌的馬雅可夫斯基。我相信安娜在她下鄉插隊期間,一定和許許多多的知青一樣,在他鄉異地的水稻田裏,在揮汗如雨的勞動之餘,用低沉的聲調,朗誦普希金的名作《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正是這樣的詩篇,點燃了我們對生活的希望,陪伴我們度過那些艱難的日子,以至於在許多年以後,還能聽到那個時代的回音。安娜在《春節感懷詩篇》中這樣寫道:普希金說/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生氣/煩惱時要保持冷靜/快樂的日子會來臨……/遠方的朋友/感謝你的支持/但願互相鼓勵/直到終極。讀安娜的詩,你時時會感受到一種情感的劇烈撞擊。她用詩訴說對親人的思念,對友人的牽掛,對這個悲慘世界的憐憫,以及對大自然遭受無情掠奪的痛惜;她甚至帶著自己的詩篇,站立在布達拉宮的臺階上,與六世達賴喇嘛—那個多情的活佛倉央嘉措展開心靈的對話:飛越千山萬水追尋你的蹤迹/你默然無語/仰望瑪布日山上的古老宮殿/只有風在淺唱低吟/那一天/我閉目在經殿的香霧中/驀然聽見你誦經的真言/那一月/我搖動所有的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世/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這樣的詩,往往令人怦然心動。
安娜的詩,表現出富有個性的審美追求。在這部詩集中,你看不到現代詩人經常運用的斷崖式的敘述,找不到紛繁復沓的意象疊加,更沒有「以艱深文淺陋」的毛病;不像某些新生代詩人,刻意去顛覆日常語言的語法規則,讀他們的那些詩就像遇上北京的霧霾,讓你在昏暗中把握不住方向。她的詩,純凈、淡雅,如同她少女時代的模樣,任何人從她身旁走過,都忍不住要回過頭去多看一眼。
還是在念中學的時候,我的老同學在古典文學方面就打下了紥實的基礎,所以在後來的詩歌創作中,便能自覺地向古典詩詞去吸取營養。她將古代詩歌的韻律、節奏融入白話詩的創作,從而使她的詩歌形成了富有音樂美的特點。或許你會認為,她的某些作品寫得過於平直,缺少深長的意味。但是你不可能沒有發現,她的所有詩歌都像是音調諧美的「新樂府」,如若配上樂曲來吟誦,你就會情不自禁隨著詩的韻律節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安娜的詩是經得起反覆吟誦的。
我期盼詩人創造出更多的佳作,與老同學分享。
蔡一朋 2019年8月31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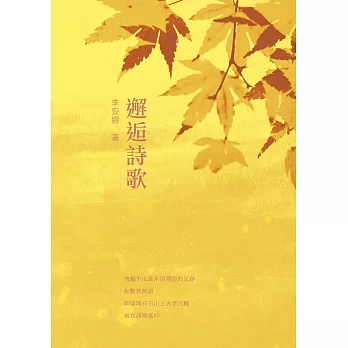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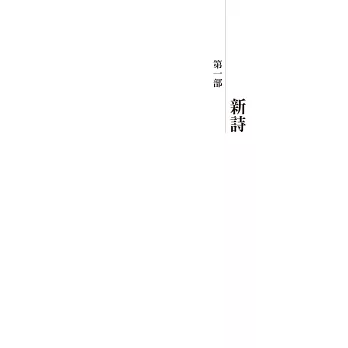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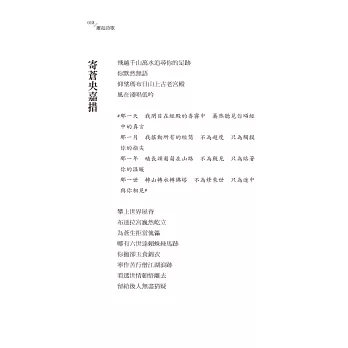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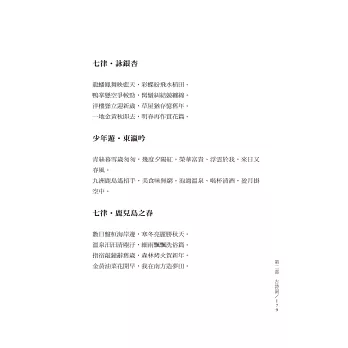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