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節錄)
老林的實踐:一個沒有止境的社會改造集體事業
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並且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黑格爾,《邏輯學》,一八一二
一九八○年代末,老林(朋友之間稱呼林孝信「老林」,我也就這樣稱呼他吧)從臺灣戒嚴體制的海外黑名單被解除不久,就回臺灣去找他的摯友、著名作家陳映真,也參加了陳映真一九九○年代開始舉辦的、有關臺灣社會性質論的讀書會。期間他與陳映真有過多次深入的對話,老林說:「……記得他(指陳映真)很多次建議我不要搞那麼多活動了,要多做理論的建設,因為臺灣非常需要理論的工作。但我認為理論的建設需要實踐的基礎,我在臺灣的實踐還太少。」(參見本書第三章〈一生釣運、普及教育的苦行僧〉,頁二○二)
一九九七年,老林與我帶著兩個還在小學讀書的女兒,全家自芝加哥返臺。之後,老林全身投入改造臺灣社會的種種工作,數年後,老林有「更多的實踐」了,朋友們都認為:老林腦袋裡頭的學問、經驗、智慧、理論,應該整理出來,我及朋友們也跟老林提過無數次,這已經是我們朋友圈的共識。但唯一不完全同意的就是老林本人,因為他認為對改造社會的事業而言,實踐工作、組織工作還是最重要的!至於理論的建設、著書立說……以後再說。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之中,老林跟數不盡的保釣戰友們、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同志們、科普同道們、社區大學運動的夥伴們、通識教育的同仁和師生們,及左翼運動的戰友和同志們,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就不曾停歇、為臺灣的民主(我這裡的民主不是當前我們見識到的那種扭曲的西式選舉民主)、公義、平等,為創造一個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的集體實踐而共同努力著。在這個改造社會的集體事業中,老林如「苦行僧」一樣、孜孜不倦地,甚至頑強而艱苦卓絕地,進行著一場沒有止境的實踐。雖然沒有「著書」,但在教學、組織、實踐的過程中,老林從不間斷地為集體理想事業「立說」,有時是教學、演說、研討,有時是評論、訪談、對談。《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這本書主要就是以訪談、對話的方式生動地將其展現出來。這個集體事業主要包含了科學普及、保釣運動、社大運動、通識教育及左翼運動等五個方向。
首先,科學普及。以《科學月刊》為例,老林一直強調,《科學月刊》「不是個人的事業」。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老林與廣大留學生社群共同體認到: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成就,自己的國家顯得多麼貧乏;民眾缺乏科學的態度,對科學盲目崇拜;臺灣的學生僅關注課業,對社會缺乏關懷、對國際局勢缺乏認識、對批判性思考訓練不足。於是,以一百多人為共同發起人,許多留學生與科學家無私地投入《科學月刊》的創辦與長期經營。老林在《科學月刊》四十週年之後,再度提及我上面說的「集體」,他說:「《科學月刊》從創辦起,四十多年來不知多少人貢獻他們的心血,默默地耕耘。大家都把《科學月刊》當作臺灣社會的公共資產。正因為這個公共性,才使『理想、啟蒙、奉獻』的理念與精神長期堅持下來。」半個世紀來,數不清的知識分子投入到這個科學普及事業的實踐,至今未曾停歇。
再說保釣運動。老林說,留學生投入《科學月刊》的創辦與投入保釣運動,有其內在的一致性。他們(包括老林)因自己家園中的釣魚台被美、日私相授受的不公不義而憤憤不平;預見臺灣漁民權益將無法受到保障的問題;失望於帝國主義強權霸道之下,政府怯懦不敢積極保釣。於是他們投入實踐、化不平為力量,在留學生中展開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老林說,參與保釣運動的一代滿懷理想主義的色彩,他們愛國愛民、關懷世事、熱情且不計較個人得失、勇於為正義事業出錢出力,甚至犧牲學業、事業,不怕被列入黑名單,投入與個人功成名就無關的保釣運動。保釣運動即將步入五十週年,海內外過去投入保釣運動、持續關注釣魚台議題的「老保釣」及「新保釣」正熱切討論及規畫如何舉辦紀念活動,見證這個半世紀以來沒有止境的、改造社會的集體實踐。
陳美霞(成功大學公共衛生所特聘教授,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前言(節錄)
理想、啟蒙與奉獻
實踐:《科學月刊》、保釣與第三世界
這五篇訪談,加上對談,突出了孝信先生一生志業與思想的幾個方向,其中保釣運動可以說是扮演了他人生轉折與樞紐的關鍵。這不僅是因為他對保釣事業投入之深,而被迫放棄學業、列入黑名單,更是因為保釣運動代表與喚發的理想主義精神,一直是孝信先生力求實踐的道路。從參與一九六三年的青年自覺運動受到啟發,到克勤克儉、群策群力地創辦《科學月刊》,孝信先生一直關心的是如何透過實際的作為,而非高蹈的口號或主義,將所學貢獻社會與國家,並在實踐的過程中集結同志、擴大參與,形成一個集體的,而非個人的事業。誠如他在《科學月刊》創刊號的代發刊詞上所題:「這是你的雜誌,不是我們的雜誌。」刊物與運動(事實上,刊物即運動)的目的,是讓社會共有,是為了改變社會與創造社會。保釣運動為這條實踐的思路添上了愛鄉保土的愛國主義色彩,也從而打開了長期內蘊於臺灣社會的潘朵拉盒子。但是孝信先生不為路線的分裂所動搖,反而在分裂的波折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社會主義世界觀,以及所謂「第三條路線」的行動綱領――期待超越統獨立場,支持公義的社會改造行動,能讓臺灣從戒嚴走向民主與解放。而一九七○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啟動,恰恰代表了「第三條路線」的素樸實踐與邊緣戰鬥。如他所說:「比統獨更重要的是對臺灣社會的關心……支持臺灣為正義的鬥爭、受壓迫的鬥爭,這是不論哪個立場都要去支持的。」誠然,透過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運作,孝信先生不僅找到了一個從海外介入臺灣社會的方法,營救陳明忠先生、支持黨外民主運動、培訓組織幹部,透過各種的連繫與活動(尤其是夏令營),他也將芝加哥變成了串聯海外左翼的樞紐。這種以自身為橋梁的實踐,讓孝信先生成為左右統獨共同敬重的前輩與諍友。或許彼此最終的立場並不一致,但他廣納百川、不拘一格、誠懇做事的胸襟與氣度,不只贏得了尊敬,也為臺灣社會保留了一個不為私利、只問公益的典範。或許,正是為了實踐這種務實的、帶有現實感的理想主義,敦促他從北美回到了臺灣,拋開光環,開創社區大學、推動通識教育以及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從《科學月刊》、保釣運動而通識教育,雖然跨度很大,但每個項目都是改造社會、創造社會的具體實踐,他一以貫之,毫無虛偽與違和,並且奮鬥不休。
保釣的另一個關鍵作用是思想性的。這包括了對中國現代史的重新認識,即劉大任所謂的「走出神話國」,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大陸)的同情理解。最後這一點尤其重要。在〈意識型態與第三世界再啟蒙:林孝信病中談話〉裡,孝信先生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根本、卻常遭忽略的問題:即雖然第三世界的相關論述已有不少,但是我們鮮少能夠從第三世界的歷史中解釋第三世界,因為以科學與民主為主軸的啟蒙思想主要還是西方的內容,第三世界自己的啟蒙,除卻科學與民主,還可以是什麼?換句話說,如果所謂的「進步」與「現代」,是以西方為尺規來理解的物質進步以及科技和制度的現代化,那麼在科技破壞與民主蒙塵的當代,第三世界的發展能不同時對西方啟蒙的內容與精神發出質疑、提出挑戰嗎?我們能夠不去質疑那些被意識型態化的公民社會與革命話語嗎?孝信先生想要改造社會、解放知識的熱情,並沒有蒙蔽了科學的冷眼;相反地,恰恰是他冷靜而深刻的科學之眼,不斷提醒我們要從各種教條中解放出來──不論是左翼、右翼,還是科學主義的。對孝信先生來說,重要的是保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而不是一頭熱、一窩蜂的主義狂熱。這也是他提煉自保釣運動的深刻反思。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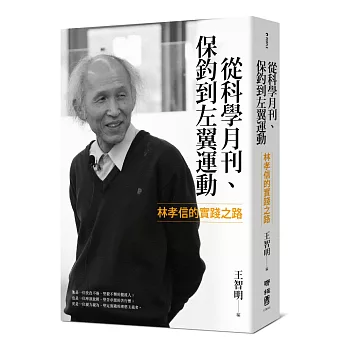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