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從八斗子出發的見證者—關於王拓留下的三本小說
1
我第一次認識王拓這個名字,不是因為小說,而是因為「鄉土文學論戰」這個讓浪漫時期的我心神激動的名詞。對我來說,那固然是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是浪漫主義的時代。因為唯有極度浪漫之人,才會在那樣的氣氛下,仍能不顧一切為自己的理念發聲。
事實上,1977年在《仙人掌》雜誌「鄉土與現實」的專題裡,和蔣勳、唐文標、尉天驄、陳映真、銀正雄、朱西甯一起發表文章,探討「何謂鄉土?」之前,王拓已在《文季》雜誌發表了諸如〈廟〉、〈旱夏〉、〈炸〉等「現實主義」小說。因此,他以〈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為題並不讓人意外,因為《文季》的出現,挑戰的正是當時當道的「現代主義」。
後來被歸類為「鄉土文學作家」的王拓,當時是不滿「鄉土文學」這個用詞的,因為他認為這詞常讓人誤以為是「只描寫鄉村的文學」。他說:「鄉土文學……就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裡的願望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我認為應該稱之為『現實主義的文學』而不是『鄉土文學。』」在這樣的定義下,這類的寫作者強調的是根植於「台灣現實經驗」的作品,場域則不分城市、鄉村,是一種以「寫實技巧」,表達「在地經驗」的主張,並不真的深入涉及政治、國族的意識型態。
這可以從王拓在這篇長文中第一段很長的「前言」看出來。他用數千字先談了1970年代台灣社會的樣貌,裡頭陳述當時文學家必然會提及的「中華」情懷,並對帝國主義(包括「日帝」)大為撻伐。關於前者,我們當然無法判斷,當時是因為時勢之故,或是作者的真心;而關於後者,可以知道當時王拓深為左派理念吸引。這段「前言」如今讀來很有象徵意味,因為可見在當時宣揚「現實主義文學」(或鄉土文學),後來被構陷為「工農兵文學」,概念上類似於中共同路人的這批作家,正如宋澤萊在一場演講裡提到的:「當時所有參加論戰的人,不管贊成或反對鄉土文學的人都是持著中國意識,包括『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這種意識」。只是結果帶有左派色彩的年輕作家,最後仍不見容於政府。
其次,不可忽視的是,王拓在文中對自己「文學」的懇切自白:「在我不算很長的業餘的寫作生活中,我所寫的一切文字,包括小說、報導和評論,都是對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的人這種堅定不移的愛心和信心出發的。」這又是帶著某種浪漫情懷的表述了。
2
讀王拓的早期作品《金水嬸》(1976,與《夏潮》創刊同一年),可以看出他的「現實主義」宣言的實踐。《金水嬸》以王拓母親做為故事藍本,敘事筆觸質樸無華,是清晰順暢的寫實筆法。就像以澄透銳利的鏡頭近拍的照片,自有一種素淨透明的動人魅力。
在出版兩本短篇小說之後,王拓歷經從政、牢獄之災(在獄中寫了兩本長篇小說以及一本兒童文學)、平反,成為民進黨的中堅份子,退休之後再次動筆。當我受黃武雄先生與王拓兒子王醒之先生的咐託,閱讀他的三本遺稿時,心情竟和當年讀《金水嬸》時很接近。這三部作品代表了王拓多年來的文學堅持,很像是他對現實主義的宣言:「反映現實生活中的人的感情和人性反應」,再加上他一貫的浪漫情懷。只是這次王拓寫的不是他的母親、漁村人民、底層勞工、受資本家壓迫的人們或是醫界黑暗面,而是幾番從文壇、政壇裡「死去活來」的自己。
這三部作品裡面以王拓自身為藍本的主角,年紀最輕的是《阿宏的童年》,時間跨度應在1950——1960年之間;三十萬字的《吶喊》是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到高雄橋頭事件;《呼喚》則是1979至1989年間,從美麗島事件到台灣解嚴,以及天安門事件為止。
根據王醒之先生給我的信件裡的說法,《阿宏的童年》創作時間較早,後兩冊則是在王拓從文建會主委卸任後所寫,修訂完成的時間是去世前的兩個月。也就是說,這三本書是「順著生命之流」而寫的,雖然其間的人名體系都不相同,卻可以清楚辨析出王拓本人的角色及周遭人物。可以說,從文學步入政治,再從政壇退役的王拓,早就有意圖以這近五十萬字描述自己五十年的生命史。據說如果身體沒有出狀況,他是希望能再接續寫下去的。
這三本小說中,在前兩部王拓的代言人都叫「阿宏」(雖然姓有更動),最後一部則變成「林正堂」。小說裡有些人物使用真名(比方說比較無關情節推動的人物如藝術家劉國松),有些人物則依託另一個名字(如陳映真在《吶喊》裡是石用真)。不過,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台灣文學或政治史知識的讀者,辨識出小說裡人物與真實人物的身分並不困難,因為王拓並沒有用過多的文學筆法掩飾。或者,我認為王拓是刻意不掩飾的。
所有的文學研究者都知道,小說絕對不能等於作者自身(王拓本人也在《吶喊》的序裡說明)。作者隱身在文字之後,他取、捨了什麼材料,多半讀者並不知道。就算研究者把文本拿來跟作者生平比對,在虛構文學概念的掩護之下,作者往往能「全身而退」。但研究者也都知道,小說確能看出部分作者的意識型態、意圖與理想。這似近似遠的關係,就是文本與作者之間的秘密引力。
在文學領域裡,王拓與《夏潮》、《文學季刊》成員關係很深,甚而參與其中;在政治領域,王拓曾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文建會主委;在這兩者交錯的時空,王拓因著文學,也因著政治入獄。這些都意味著,王拓不僅僅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人。因此,他留下的這三部「現實主義」作品,也很接近於那個時代的「目擊者」。
3
王拓一生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正是他在《文季》、《夏潮》、「人間副刊」發表小說、訪談、隨筆,同時也主持《健康世界》的時候。這一時期的王拓與「黨外」人士接觸密切,但還沒有想要涉足政治,他對文學的熱情則是一個八斗子漁村的孩子,從身邊的人、事、物以及周遭「說故事」的長輩得來的。
在《阿宏的童年》這本小說裡,主人公阿宏是個有才情卻叛逆的漁村孩子,成長過程中有兩個故事打動了他,讓性格做了改變。其一是母親金水嬸說的「魚娃娃」的故事,二是他在學校裡的外省人老師黃錦川說的「一根蔥」的故事。這兩個故事他日後都在書裡頭讀到,發現它們分別來自日本和印度童話。講述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故事的來歷,這讓阿宏大為感動,文字竟有如此的力量,讓不識字與識字的人,都從其中得益。
而在老師的贈書裡,阿宏又與中國作家謝婉瑩(冰心)相遇,這些文學教養的形成,王拓顯然暗示著未來的阿宏,終究會是一個從文學出發的政治家。
《阿宏的童年》是很典型的70年代台灣寫實主義的寫法:小說先寫環境(八斗子漁村),再帶出次要人物,接著再讓主要人物登場。小說的開展是從主要人物的成長,間以人物、事件推動時間。其間至少揉合了幾個元素:一是私密的記憶,二是八斗子的地方發展、民間人物,以及鄉野傳奇。最後是時代的變遷以及主人翁自身的意識型態與認同的變化。
雖然是質樸,屬於在某個時代的寫實筆法(台語文也是那時代的寫作方式,因此並不準確),但一些細微之處仍打動人心。那個青春期敏感的阿宏,畢竟是一代年輕孩子的縮影。特別是金水嬸說的「魚娃娃」故事裡的啟示,成了貫穿這三部小說,最具文學性的隱喻:
知道這個世界有時快樂有時痛苦,即使如此,還是願意被生下來,那麼,你才會來到這個世界。
4
王拓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因為無法見到親人,也像自己的母親一樣,對著獄外的兒子講起了故事,寫成《咕咕精與小老頭》。離世後,他的兒子王醒之則寫了《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與基隆畫家王傑合作,將當年的家書化成一本在時間之中的回信。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兩個時空的對話。王拓的一生,本就像是一部一部作品結構起來的,似虛構又無比真實的世界。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鄉土文學論戰。我後來在閱讀這段歷史時有一種感受,因為中文的特質,加上過去作家論戰不太定義自己使用的詞義,因此很多時候「戰」沒有太多「論」的成分,甚至感情成分多一些。就像當時刊登在《仙人掌》的這11篇文章,彼此並沒有真正聚焦。
回過頭看,當時學者、作家在使用「鄉土文學」時,可能涉及三種西方文學的概念,分別是「Nativist Literature」、「Regional Literature」以及「Realism」。前者是在內容上強調「本土性」,其次是在材料上以「區域的」、「地方的」人、事、物寫作,而後者是一種後來廣泛演化的藝術概念。
學者陳建忠曾經據《文學辭典》,引述鄉土小說(Regional Novel)應該至少具有幾個特點:「它以某一地理區域為故事空間,特別關注社會習俗、民間傳說、鄉土語言,或者是自然風土等方面。因為這些地區性的人物或行為一旦置於其他環境就會有不協調之感,所以也有人因這類文學的特殊性質,而稱秉持這種寫作理念具有「鄉土主義」(Regionalism)。」
若查閱相關英文論述,可以發現前兩個詞在發展之初確實特別指涉非都市的在地經驗與風景。但後來,這種在地精神隨著資訊的流動、人的移動更為頻繁,甚至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地方性」有可能存在跨國(現今的國家定義,未必和地理、人類族群的分布完全一致)的現象,以至於詮釋上益發複雜了。
當年這些文化菁英彼此之間的論戰,背後有表態的恐懼、不表態的恐懼;有自身文化教養的盲點,也有感情衝動的盲目。那盲目是國族的信仰、文化觀的信仰,再加上威權之勢,恐怖壓身的結果。
王拓這三部小說裡的主人公,從愚騃的童稚時光,漸漸變成思考「我所說的台灣人就是現在住在台灣生死與共的這些人」、「台灣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裡頭的人物「不想涉入政治」,卻因為對社會、文學帶有責任感,而被迫涉入政治。終究從浪漫的少年,熱血的青年,變成懷疑論者,入世者,進而建立了自身在悲愴與恐怖的世界裡賴以維生的信仰。這三部小說裡,王拓以類自傳的方式寫進來的諸多風流人物,或許也多少看得出他們生命軌跡的變遷。
我在想,這三部小說說不定反而因此誠實地反映出了一個人的生命選擇,是在時時變動、刻刻移轉的狀況下逐漸成形的,裡頭充滿了艱困、無奈、懷疑以及不確定。而不是像一些政客所出的傳記(按理說那應該是「非虛構」作品),總是宣稱自己:「無私」、「無愧」、「無懼」。這種宣稱才是真正的虛構吧?
而這或許也就是為什麼有人認為小說有時比非虛構文學還要真實的一種可能性。
如果以評論者的立場,我必須說,王拓在這三部小說裡的「技法」不再是此刻我們觀看的重點,也很難讓年輕作家追隨了。但這批作品放在台灣文學史上卻有一種特殊的重要地位:它們是時代的證詞,一批獨特的證詞,一個浪漫時代的證詞。是一個作家與政治家的成長之路,也是台灣意識的成長之路。
那句:「什麼日本人,中國人。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是八斗子人!」是歷經了各種挫敗、強暴、威權與傷害後的自覺,王拓一生志業真正的「現實主義」。
這讓我想再一次,重述一遍王拓當年首篇論戰之文裡,所說的那一段話:「我所寫的一切文字……都是對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的人這種堅定不移的愛心和信心出發的。」
這趟旅程並沒有隨著王拓先生的離世而到了終點,而是從這三本遺留下來的小說開始。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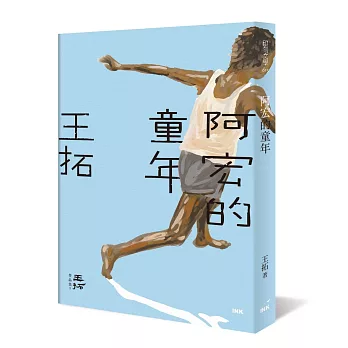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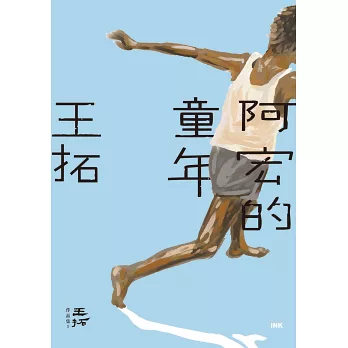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