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隻貓在路上
那年在內地,有天夜裡,國子監胡同,小區有燈點亮一棟老公寓天台上瘦長的房子,一個朋友和她的貓以及一些將裝入紙箱的家當正熱烈對話,那是北漂多年後,幾千公里的南遷。上海的黃埔江、浪漫的洋樓,似乎遠遠地,乘了安靜的夜色,拐了好幾條巷弄,伴著梧桐光影打起誘人的招呼,一聲又一聲。
人,是唸北大的姑娘,喝過洋墨水,一個身材不高,面色白皙,打扮低調,說的話、笑起來總覺得有點南方,水水甜甜的韻味。
貓,年輕、頑皮、受寵的橘色虎斑,肥肥胖胖,深養在家裡,見了人,多些沒見過世面的害羞和警戒。
紙箱四處,搬家是件辛苦活,人與貓幾千公里的開車路途更是困頓,不過這樣的遷徙,讓我想到一種態度:自在、隨心,風塵裡的天開地闊。
這,應該是街貓浪浪的故事。
有時有人問:你養貓嗎?
不養。我總是無情地回答。
不養,因為不忍。
學生養貓,經常聽他聊起貓,談起貓的頑皮、貼心和溫暖,眉眼間好像總有隻貓在跳舞。看來很美,卻又有一些疑問存在我的心裡:四條腿的動物活在兩條腿的世界,真的是種幸福嗎?
我在朋友的工作室,城市的咖啡館看見貓,看見貓咪們多半窩在桌下、沙發上、窗台上,牠們的肢體優雅,表情溫和,少了風吹日曬,多了飽暖,是公主,是王子,被照顧得妥妥貼貼,然而不經意地,我總會看見牠們靜坐,守著一道光。面對窗外,看著熱鬧、人來人往的車街,要不就是碧綠的樹和藍天,牠們在想什麼呢?
淡水堤岸有家很小的咖啡館,一樓吧台,二樓座位,牆刷了黃、白、藍有些希臘,我有時會去喝一杯,是看落日的好地方。
店老闆收養了幾隻街貓,沒有華麗的窩,只是紙箱墊了布毯,外加旁邊一盞老式綠色鑲金的檯燈和幾本書。貓餓了就回來吃,累了回來睡,想散步,女兒牆縱身一跳,飛簷走壁去了,一切瀟灑隨心。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出入在我家的動物,那些雞、鴨、鵝、狗、貓,現在回想起來,鴨冠仍然鮮紅,雞尾巴是道彩虹,鵝還是聒噪地追著人跑,那隻高大的狼犬嘴上依舊叼著輕竹籃,跟我媽上街去買菜,而貓呢,寬廣的草地上有些小花和蟋蟀,天很藍,映著光,牠跳躍其中的身影是金的。
除了狗,有時會用鏈子把牠拴在門邊,其他小傢伙,多半時候都是放養,牠們的世界好大,好大。
沿著山路走,順著水岸行,為了接近貓,瞭解貓,我經常背了相機,搭一兩個小時的車出門。天有時晴,有時陰,有時雨,有時起了霧。經過的山徑、小溪、破屋、巷弄、碼頭、城市裡的車街,雲影流動,風捲著浪潮而來,我陸續遇見了許多街貓,牠們以黑,以白,以黃,以灰,以玳瑁,以三花,以不同的斑紋,或蹲或臥或行或走,各種姿態和顏色相迎,纏繞腳邊的,常是可以回味很久的親人叫聲。
有天我走在九份的輕便路,那是山城常見曲折小路,卻不像基山街、豎崎路那樣的熱鬧喧騰。
我走進一家陶藝小店,因為店的一角有隻灰色虎斑。
女主人正低頭做著作品的最後修飾,我打了招呼,四處欣賞,卻發覺身邊有隻貓,輕聲而溫柔地叫著。
是剛剛那隻,我低身摸摸牠的頭,學牠喵了兩聲,訝異牠不怕生。
有客人來時牠都會這樣,黏著人叫,好像在替我招待,然後又回到牠的位置。女主人笑笑地說。
哈。那真好玩。是街貓嗎?我問。
半家貓。放養狀態。
我和女主人又聊了兩句,看了架上隨心捏出的瓶瓶罐罐,然後走出那家店。
天有些陰,店裡的燈亮著,昏黃而溫暖,回頭看那貓,果然是老地方的優雅姿態,真是有禮貌的傢伙。
是誰說「狗有義,貓無情」呢?說這話的人一定沒有養過貓,不知道貓瞳孔收縮與放大的意義;不知道尾巴豎起與彎曲的意義;不知道細緻的眉毛、鬍子向前向後所代表的意義;更沒聽說人、貓一起上街購物,黃昏時一起長堤散步的故事。
貓,形聲字,右邊是貓的叫聲,左邊是貓行走的樣子。部首「豸」也是野獸的象徵,肉食哺乳類。中國早在西周就有相關文字記錄,詩經把牠和熊寫在一起,沒有太多史料,當初也沒相機,不然留存下來的影像,說不定貓指的是大貓,是獅子、老虎、豹(一笑)。
家貓難拍,街貓更難,難在有野性、有戒心,難在難以溝通,不聽指令。拍平面不像拍影片,不透過誘引,也能經過剪接,達到部分想完成的效果。多半時候我拍貓,只能尋找一個環境,在對的時空,儘快地找到對的角度按下快門。這個「對」字,是機緣,是素養,是對貓的看法,是個人心中想像的世界。
有時貓是貓,我是我;有時我是貓,貓是我。
這本書不是教你如何拍照,也不是如何照顧寵物,裡面的貓也未必很萌,如果說有什麼想望,應該是期待在新詩、書法、攝影,甚至是繪畫,在美學、文學的表現下,引導大家接近街貓,欣賞街貓。
生活很美,街貓很美,到處都很迷人,就看你,怎麼閱讀。
寫於二○一二年五月十二日,於台北
不羈的靈魂
天有些陰,雲壓了帽簷貼著山頭而行。水岸安靜,偶而樹梢傳來幾句鳥語,大概也是一種無爭閒情。
這是家書店,臨著河岸,一樓通往二樓的樓梯壁面曾經泊了一艘小船、幾隻白鷺,現在則整個翻轉,貼了時事。門口的落地玻璃小門更多了「請脫鞋。接地氣」一張小紙條,低低地,不見身段地傳遞店主無限情話。
推門而入,眼前一排書櫃,相較過去,書少很多,排列卻相當清爽。七年前,或者四、五年前,我有一本書在這寄賣,有時天晴我來,看它和夏目漱石的貓玩在一塊;有時,畢卡索般地立體堆疊,我那本關於貓的書常常窩了一隻貓。
貓與書與文人與畫家,與男與女,總有一分鮮明的浪漫相逢。
這幾年常念經,心經,二百六十字,可說是大般若大智慧經要。裡頭寫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說是貓的行為顯相,似乎也相差不遠。
有時荒地裡看貓靜坐,優雅如一座山,如一帖法度充滿的楷書,看牠目光卻是見了遠處又落在近裡。又有時看牠陽光裡,圍牆上伸展懶腰,總覺是一捺一撇流雲行書,動態中透露了自我定性。溪水溫柔,來與去,楷行草書寫的愜意隨心,這應該就是與貓共處,讓人歡喜的主因。
我站在書櫃前,翻閱一本封面有很多眼睛的「酒徒」,想像劉以鬯失眠的夜色,是否曾經和我書寫的詩句,一隻黑貓的雙眼對映。那會是初一還是十五呢?
這裡,現在還有貓嗎?
某些充滿陽光的日子,一個纖細的女詩人在這所餵養的街貓,其中一隻虎斑,想起來叫金莎。
有。隱於櫃台的店員,應老闆要求,用一種可愛、不熟悉的台灣話回我。
那些貓肚子餓的時候就會出現。牠們是街貓。很怕人。吃完就跑了。
也許,他的語音讓我想笑;也許,知道這裡依然有街貓出沒感到歡喜,那多少意謂著環境議題以外的人間多情。這幾年路過河岸,總會想起那些圍牆、屋頂、草叢、花間,縱橫天地的街貓。我記得,有一兩年,我有貓的視野和氣味,經常在巷弄、河岸、山城低伏。
我離開書店,輕輕帶上那道玻璃門,離開記憶中細緻、少言的女詩人和她魁武高大的先生,走進兩個金爐分守左右的廣場。天光是神奇的色溫帶,黃藍兼併,路邊店家已然點燈,廣場好像還有許多我用大筆書寫的水痕,和一隻橘貓,從七年前的黃昏穿越人群。
時光漫漫,總是悠悠。深秋的河岸,欒樹一路火紅,像要到了天邊,卻又曲折轉了彎,停駐碼頭。
碼頭不大,有堤。堤,瘦長,春夏秋冬,多有人在上面或站或坐。遠遠看去,逆光的剪影靜默有如一場場人生大戲。風裡相擁,薄霧裡分手,怎麼看都很精彩。我記得碼頭邊的咖啡館,簷下七彩燈光照著,一隻名叫空空的貓,背對曾經空空的長堤。天地開闊,樹下、草叢,三月的苦楝花年年開著,紫色的空氣散佈很多巷道、空屋,貓的眼睛只是澄澈如一方碧綠琉璃⋯⋯
七年前,我書寫了很多貓的文字。七年後,我再次梳理那些舊日在路邊和貓接觸的情感,順著貓徑去了淡水,感受眾貓的不拘,屋頂上與天相近的安然,重新整編這本和貓相關的影像詩集。巷弄清寂,明月高掛,諸神之前自當磨墨,將萬種祈願一筆一劃,縱橫紙上雪地。這書內容依然有山有水,有淡水河岸,也有九分、金瓜石山城的淡然,甚至城市巷弄群貓夜話。
感謝青田街的隱者,書房總編和主編的溫暖,素昧平生,如此厚愛,為我出版了關於貓的影像詩集,謹此由衷致謝。
寫於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台北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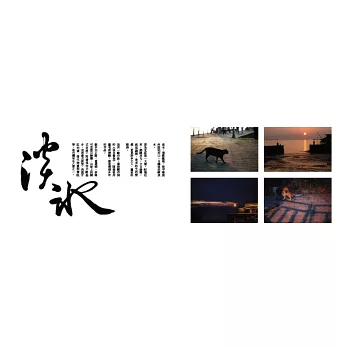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