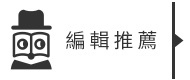推薦序
她的背後,是一個時代的景深
李桐豪(作家)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跨年倒數最後幾個小時,我在公司附近的咖啡館見著了佩津。
在新加坡讀MBA的她回來過新曆年,問她新的一年即將來到,可許了什麼新願望?「我不許願,今年發生的事情,讓我對跨年非常恐懼。去年,媽媽得了癌症,跨年的時候,朋友一樣要我許願,說哀傷的一切都會過去的,結果一跨年就來一個更大條的……我已經不會對未來有過分的期待,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有什麼會發生。」
佩津口中講的更大條,是指去年一月一日,罹癌的母親在家燒炭自殺,「我回家一發現第一件事是在我們的朋友群組講這件事,我丟訊息說,幹,我媽好像燒炭。他們就問還有沒有呼吸?趕快送醫院!我說,硬掉了。」
她說,那時候,警察男友還沒變成前男友,面對這種事,心裡已經有一個SOP,身邊有人陪著,通報、葬禮、拋棄繼承、除戶……後事很快就處理好了。時值農曆年前後,她在母親住處整理遺物,發現一疊發票,有一張發票是她去旗津散心買的波士頓派,消費金額一百五十塊,一對獎,中兩百元,兩相扣抵,賺五十元,她擠出笑容說,這應該是母親給她的過年紅包。
這件事同樣寫在佩津的《卸殼》,該書行文基調,一如坐在我面前的她訴說往事的口氣,淡淡的,冷冷的,情感上自我壓抑、自我克制,甚至有點自嘲,娓娓道來一個家庭的成住壞空。書中交代,小學校園作防空演習,小一、小二的女生,認識的字不多,以為「防空警報」該寫成「皇宮警報」,因為童年的記憶跟在皇宮也沒什麼兩樣:她在國賓飯店喝下午茶,穿著品味無懈可擊的母親調教著她的餐桌禮儀,嘴巴含著食物時不要講話、舀湯的順序是由外而內……她像個公主一樣被嬌生慣養著,印象中,家中堆滿禮盒,母親時不時要她拿一盒腰果去學校送老師,或者給同學吃,如此才不失禮數。
母親在娘家家族企業當會計,後來不顧家人反對,和心愛的男人結婚,生下了她。婚後,父親嗜賭,欠下千萬賭債,母親和父親離婚,父親離家,母親一個人開旅行社,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但後來又幫親人作保被倒債,房子被拍賣,一無所有的母親,流浪在大賣場當清潔工,佩津大學寒暑假最怕回高雄,寧可一個人待在宿舍,怕不知下來又是什麼奇怪的狀態,「那時候最讓我感到煩心是家裡房子沒有了,我媽跟我借存摺,我拒絕,她很受傷。對我來講,跟我們家裡互動充滿壓力。」
二○一二年,在台中工地打零工的父親意外身亡,年僅四十八歲。二○一九年母喪,年僅五十五歲。眼看自己就要滿三十歲了,所謂三十而立,就是一個人佇立在人生的十字街頭,不知何去何從,「一直以來,父母的狀況會讓我很害怕被拖累,我知道接下來我不會再有潛在的風險了,其實有種鬆一口氣的感覺,但同時也告訴自己,從此之後,妳再也沒有人可以怪罪了。這種事情你很難跟同輩的人講。聽他們抱怨爸媽時的心情是很奇怪的,因為你不能跟他們說,至少你們還有父母可以抱怨啊。」
無父無母,無牽無掛,自由某種程度跟孤單同義,去年春天,她一個人來到新加坡念商學院,明明生命中最沉重的負擔卸下了,但心裡總是空蕩蕩的?她在課餘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寫下來,一周規定自己寫一篇,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靠這樣的方式度過時間,「以往是不大讓身邊的人知道家裡的事,怕他們知道會很有壓力、會嫌棄,但後來想想也許有人會碰到跟我一樣的事,畢竟這是我們這個年紀很容易遇到的事情,家中長輩身體有恙,大家的人生都被迫慢下來的,內心的焦慮很多的……」家醜外揚,寫成文字,集結成冊,無非是如果你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那麼有類似際遇的你也許不會這麼孤單,也許會覺得安慰一點點。
佩津和我在壹周刊曾經共事,同樣負責人物採訪,寫眾生百姓的「坦白講」、寫苦勞大眾的「後來怎麼了」,她學生時期關注社運、學運,做這樣一份工作極有熱忱,她很執著,認真,對人有同理心,某個六百字小人物故事採訪,她打了三萬字的逐字稿。如今角色互換,採訪者變成受訪者,她坦白得驚心動魄,某些段落讀來,不免要在心中深吸一口氣:「這個你也寫出來?太苦了吧。」她善待他人,但對自己比誰都殘忍,把自己身上一層皮都扒下來,但她並不抒情,也不訴諸同情,出版市場從來不缺家族書寫,但孤女追憶高雄媽媽、台中爸爸的家變往事,她借助社運和學運學來理論,試圖去回應母親下半生對生命的那一句叩問:「我一生沒做壞事,為何這樣?」《卸殼》是做工的人,做工的女人,和她女兒的《俗女養成記》,母女的生命故事背後是一個時代的景深,何以力爭上流的人,最後還是向下漂流,還是翻不了身?
那個跨年的會晤結束前,我感慨因為整本書寫得疏離而冷靜,更不敢去想像那個情感的核爆現場有多慘烈和驚心動魄,努力不讓一滴眼淚不掉下來,比公司樓下停車,挪開一輛機車需要更大的力氣,但佩津依舊是淡淡地說:「這是一種保護自己的策略吧,我很習慣把情感都壓抑住。」
「人到後來都會變得很麻木的,不去急於去節哀,哀傷不用節制,哀傷是很珍貴的禮物,哀傷不是感冒,不是拿來治癒的,哀傷來臨時,你要好好感受哀傷的來龍去脈,想哭就哭,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在哀傷的情緒,就花多少時間。」當下我想這麼說,但我沒說出口,只是說聲「新年快樂」就互道再見,但在這邊我說了,祝福這本書,也祝福佩津。
自序
坦白講
二○一二年的五月,我正在聲援死刑犯鄭性澤的記者會中,電話響起,我躲到廁所去,接起電話,電話那一頭的人是警察,他告訴我,我十年來未曾見過的父親剛剛過世了,因為一場工安意外。
二○一九年,一月初始,推開家門,我找到了母親,她躺在地板上,周邊散佈著她的診斷證明書、藥物。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煙燻味,我碰觸她,冰冷而僵硬。我知道,她已經離開了。
從那一刻起,我是一個人了。
四十八歲、五十五歲,父親與母親的生命就停在這樣的歲數,而我的年紀從二字頭來到三字頭。
從大學畢業後,我換過幾份工作,最後以寫字維生,透過一只錄音筆竊取他人的人生。
很多時候,我並不知道怎麼跟人介紹自己寫什麼字,總半開玩笑地說:都是些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因為名人與成功總是那樣遙遠,但只有失敗與悲傷,是我們彼此共有,也終會遭逢。這些受訪者的故事尚未走遠,而這一次,輪到我寫自己了,由我來寫出自己的坦白講。